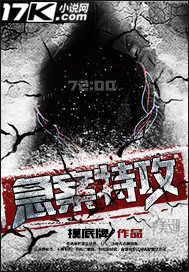若不是武建王默默无闻的替军屯王管理着军营,没人知道自由散漫惯了的匈奴大军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自从雁门关回来之后,军屯王便将自己关进了大帐,任何人也不见。但凡有人打搅,卫兵便会给一句话,让武建王处理即可。
武建王是匈奴中实力最弱的一个王,多年来他的部落就是被别人盯上的肥肉。说起来,这一任武建王是三年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大王,他的前几任既他的阿爹和哥哥全都死在战场,不是匈奴人和汉人的战场便是匈奴人和匈奴人的战场。
然而,武建王还是那个武建王,无论匈奴人辜负他们家族多少次,武建王依旧履行着先祖向天狼神发下的誓言,始终支持那个坐在单于位置上的人,不管那个人拿到单于之位是否光彩,是否合法。
栾大被关在铁笼子里,这是武建王特意要求的。和栾大有过不少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武建王就已经感觉到了眼前这个看上去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汉人绝不是他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样子。因为此人有一双和他年龄及其不相称的眼睛,那双眼睛深邃至极,估计没人能看到最深处。
手里提着一条烤的金黄的羊腿,武建王再一次来到栾大的铁笼旁,将手里的羊腿塞进栾大的笼子,微微一笑:“先生是不是饿了?吃一点吧,再过些日子可就没有这么美味的羊腿吃了。”
栾大接过羊腿,狠狠的撕下一口,面带嘲弄之色:“你们准备撤军?你就这么自信能撤走?”
武建王点点头:“自不自信都要撤退了,春天马上来临,饿了一个冬天的牲畜该贴膘了,若不能及时让牲畜吃到鲜嫩的青草,那么这一年我们匈奴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这就好比你们汉人重地误了农时一样。”
“苏任不会放过你们的!”栾大一边吃,嘴里一边发出含混的声音。
武建王一笑:“我们匈奴人和你们汉人不一样,我们没有割舍不下的东西,说走收了帐篷爬上马背就可以走,只要进了草原谁也找不到我们。”
这根羊腿很瘦,上面没有多少肉。栾大很快就吃完了,正在寻找合适的石头准备敲开骨头吸食里面的骨髓,这是栾大最喜欢的事情:“你们太小看汉人的皇帝了,他三路大军围攻匈奴便是早已经摆下天罗地网,即便你们逃回草原也不会安稳,倒不如……”
“先生不用再挑唆,还是想想自己为好!”武建王起身离开了铁牢,背后传来栾大的怒号:“你们会后悔的!后悔没在这里和汉人死拼,后悔没听我的话!你们一定会后悔!”
望着大帐里一片乱糟糟的屁股蛋子,苏任的火气就控制不住。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全被张华之给破坏了。一顿军棍下去,几乎让整个雁门守军瘫痪,别说尾追匈奴人就算是正常的操演,没有个三五日都不能进行。
“全都是你干的好事!”
张华之老神在在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吭。苏任没有权利杀了或者抓起张华之,甚至没有权利限制张华之的所作所为,因为张华之是皇帝派来的军司马。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张华之和苏任完全是两条线,甚至张华之比苏任更得皇帝信任。
张华之不说话,苏任的怒气就好像打在了棉花上,这让苏任更加生气。可张华之依旧那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样子:“将军对在下有什么不满,可上书陛下,若陛下觉得在下有罪,自然有廷尉府的人处置,但是将军纵容大军在雁门关饮酒,此事我已经禀报,并且对我做出的惩罚负全部责任,在下对此事依旧认为是将军辜负陛下圣恩,而非在下。”
“滚!”
“司马有权参与军议,此乃军法所写,在下绝不会因为将军喜怒而做出对我大汉和陛下不妥之事。”
张华之的话说的很平静,可听在其他人耳朵里就是那么刺耳。苏任看着张华之:“你真要和我对着干了?”
“错!将军错了,在下是将军的军司马,绝没有顶撞将军的意思,可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在下还是要说的,希望将军明白。”
“那好,今夜子时,给你三十名死士,由你率领突袭匈奴大营。”苏任稍微一顿:“你是我的司马,本将军对你有统领之权,此事不是和你商议,乃是命令,你可明白?”
张华之起身抱拳:“在下明白,末将领命!”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大帐。
都知道苏任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别说三十人,就是三百人、三千人也不能说突袭匈奴大营能够活着回来,苏任这是要张华之死,但是张华之接受了,这就让大家更好奇。
韩庆看着张华之出了大帐:“先生!”
苏任一摆手:“我就是想让他死!好了,他的死活老子不放在心上,下面咱们说说如何将匈奴大军留在这里,你们还能打仗吗?”
“能!”众人一声吼,扶着受伤的屁股,挣扎着纷纷站起来。
匈奴人和汉人的大战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为了应付汉人三路大军,伊稚斜孤注一掷几乎将除过王帐军之外的所有军队全都派了出去,希望能够各个击破。但是,事情似乎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东面的苏任龟缩雁门关和他派去的大军相持不下,西面的李广也将浑邪王、日诸王的残部牢牢的吸引在金城玉门关一带,更让人气氛的是,派去阻挠中路卫青的人丝毫没有起到阻挠作用,反而被卫青打的落花流水,已经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最最让伊稚斜头疼的还有一只队伍,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破坏力却让伊稚斜刮目相看。
霍去病浑身是血,黑色的战马也被染成了棕色。站在河里,一盆一盆的往身上浇水,混合着血的河水流下来,在霍去病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区域。黑马打了一个响鼻,是在告诉霍去病,别只顾着自己,它身上被血糊住也非常不舒服。
赵破虏将一盆子冰凉的河水浇在霍去病的黑马头上,黑马兴奋的晃动的大脑袋,长长的鬃毛甩的飘逸潇洒:“校尉,咱们已经深入匈奴八百里,连续作战数月,军卒都有些疲惫,是不是……”
霍去病看了赵破虏一眼:“你怕了?”
赵破虏一笑:“跟着校尉走这一场,我赵破虏只觉得痛快,从来没有害怕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担心的?咱们一人三骑,既没有辎重也没有俘虏,将军给我们的命令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又不是没有碰见过匈奴人的阻击,那一次不是全身而退,还有淳于先生的灵丹妙药在身,即便受伤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这次准备去狼居胥山看看,你不想去?”
“狼居胥?那,那可是匈奴王庭!”
“看看而已,又不是和伊稚斜拼命,要不你回去送信吧?出来这么久将军一定很担心。”
赵破虏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赌气狠狠的刷洗黑马。黑马吃疼,不断的抖动身子。霍去病摇头笑道:“别拿我的马出气,有本事在战场上多杀几个匈奴!”
“哼!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就算是我也不回去!”扔下手里的东西,赵破虏气呼呼的走了。
轻抚黑马的大脑袋,霍去病道:“这小子不错,我非常喜欢,你喜欢他吗?”黑马嘶鸣一声,霍去病哈哈大笑。
伊稚斜病了,而且病的很突然,在没有预兆的时候突然就病倒了。躺在羊皮堆里,脑袋上覆着冰凉的麻布,李少君坐在伊稚斜身侧,一只手搭在伊稚斜的手腕上。帐前跪了一地的人,包括伊稚斜的十八个阏氏和七个孩子以及他手下最忠心的军卒和奴仆。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等李少君最后的宣判。
过了好久,李少君将伊稚斜的手重新放回羊皮堆里:“单于只是急火攻心,并没有什么大碍,在下去给单于配两副药,吃了也就好了,这几日单于需要静养,千万不可劳累过度。”
众人长长舒了口气。李少君在匈奴这么多年,出了神鬼莫测的预言之外,诊病也是他独到的法门,甚至在那些贫贱的牧民心中李少君的地位正在超越原本高高在上的祭祀。
大阏氏再三感谢李少君,派人送李少君回去。擦了擦眼泪坐到伊稚斜身旁:“单于,这一次可把我们吓坏了!”
伊稚斜在大阏氏的帮助下努力做起来,挥手让其他人下去:“哎!我还是轻敌了!一个苏任就让我非常头疼,军报上说他在雁门关用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打的军屯王心灰意冷,我们的大军全都被吓破了胆子,谁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霍去病,竟然带着数百人就敢深入我匈奴腹地,几次围追堵截都不能成功,反而我们的损失更大,已经有近百个小部落被这小子屠灭,此子比苏任更残忍!”
“那?”大阏氏一停,紧接着道:“单于无需多虑,我匈奴全都是战士,汉人只是逞一时的凶狠,只要单于身体康复率领勇士,定能将汉人全部击溃!”
伊稚斜勉强的笑了笑:“但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