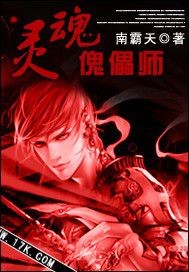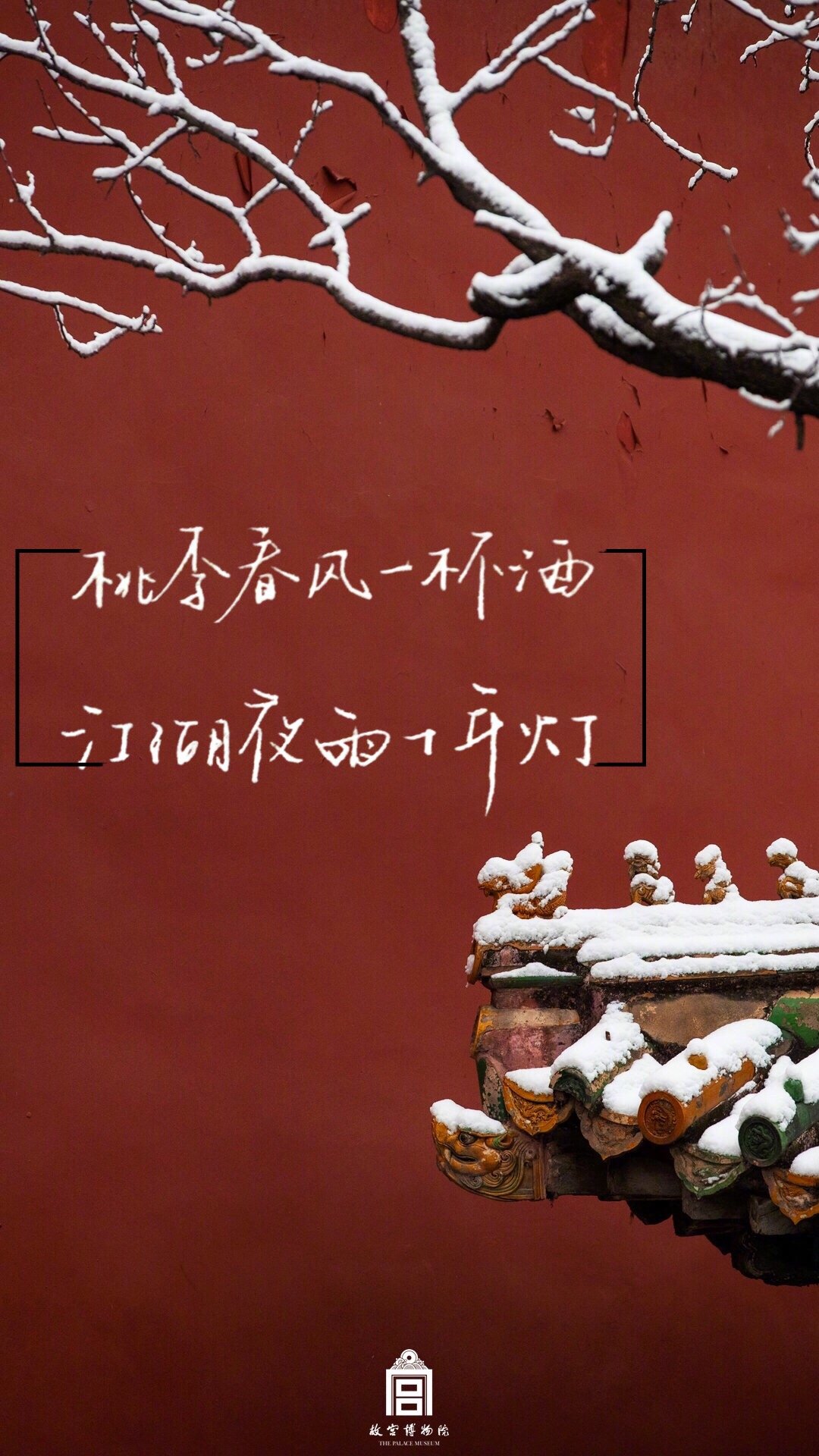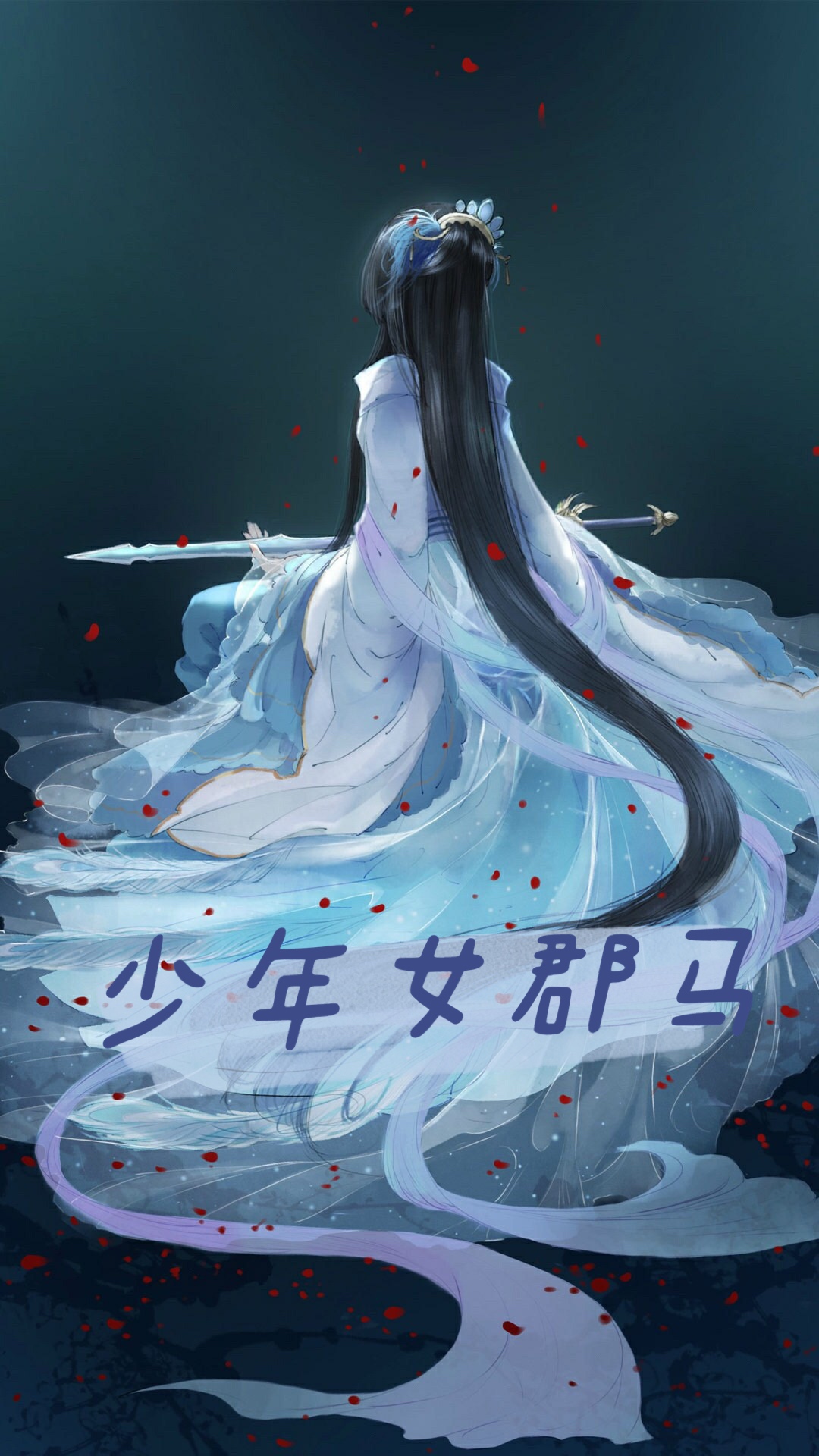有这样一座城市。她座落在风光旖旎的海滨,有银色的沙滩和澄澈透明的海。古老的教堂和广场上,阳光在尖塔顶端闪耀。依稀能看到洁白的海鸥在湛蓝天空飞翔。威尼斯,她被人称为亚德里亚海的女王。
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威尼斯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罪恶之城。潜伏在暗影里的势力掌握着这座城市。几乎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赃物都流向这里,又从这里流出去。一条狭窄的老街,一间古旧的杂货店,暗地里经手的财富数量甚至可能超过一些小小的公国。
提到罪恶之城,可能让人本能地联想起凶杀,抢劫等等犯罪的事情。但是,其实威尼斯是个治安相当出色的城市。不要说抢劫,连街头扒窃的小偷都很少能见到。因为黑暗中的意志不允许这种下三滥的敛财方式。尽管这里流通的每一块金币上可能都沾着鲜血,但是绝少出现脱离秩序的暴力。如果有人不识相,那么他会得到一个巧妙而善意的警告。警告无效的情况下,通常这个人会跟一块沉重的石头混着装进麻袋里沉到海底。
不过最近威尼斯的气氛有点奇怪。远在罗马的教皇陛下不知道为什么,派出他精锐的圣殿骑士团进入这座城市。出入威尼斯都要受到盘查。当地教区的主教亲自守在城门,对重点怀疑的人使用真言鉴定。盗窃安茹伯爵名画的罪犯被抓住了。假冒炼金术士诈骗了伊丽萨白女王一百磅黄金的骗子也落网了。然而盘查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
一匹马懒散地朝城门走过来。而它的主人也似乎不怎么着急,让它随着性子慢慢遛达。今天进城的人不多,守门的兵缩着脖子直犯困。
“你好,我是格勒诺布尔教区、沙特勒斯修道院的玛丽安修女。我到威尼斯来看望圣吉利欧圣母教堂的马法尔神父。”
骑在马上的年轻女子温和地轻声跟几个城门兵打着招呼。她有一双清蓝的眼眸,很好看。城门兵麻木地瞟了修女一眼,似乎在估算她身上应该有多少钱。
“入城费一个……不,五个金币,实在没钱,用马折价也行。”
面对城门兵摊开的手,修女勉强压抑着怒气说:“我记得上个月进威尼斯的时候,只要十个铜子。”
“现在什么时候,全城都在盘查。知道那边门楼里坐着谁?百人队长米索罗阁下!聪明的赶快掏钱,不然关到牢里,苦头有得你吃。”
排在修女身后等待查验的人纷纷对她报以同情的目光:谁让你骑匹好马呢。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大家都温顺地等待着,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刚被勒索过的人也转回来看热闹了,有人甚至幸灾乐祸地笑。这种倒霉事总是很容易变成他人眼里取乐的资本。善良的人们习惯了忘记屈辱,并且热衷于从他人的不幸里寻找安慰。
城门兵嚣张的勒索引来一声怪笑。虽然声音不大,但显得很刺耳。修女回头瞥了一眼:城门根的黑影里靠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酒气和苍蝇盘绕着他,路过的人都捏着鼻子躲开。
一个城门兵不耐烦地伸手去抓栗色马的缰绳。修女终于发怒了,她扬起手里柔韧的骨制马鞭,斜着一鞭抽在这个冒失的卫兵手上。卫兵嚎叫着倒退,几个城门兵一阵慌乱,长矛撞在一起。玛丽安修女把胸前的白金十字架摘下来扔给他,说:“把这个给米索罗看,让他过来给我道歉!”
百人队长米索罗很快赶过来,毕恭毕敬地把十字架双手还给玛丽安。他低着头,谦恭地赔礼:“这位夫人,请您原谅我那些冒失的部下。他们认不得圣徒十字徽章,不知道您是一位贵族。”
卫兵们惶恐地扔下了长矛,跪在泥地里向玛丽安求饶。
“算了,” 玛丽安做手势让他们起来,“其实你们也很苦,我知道。你们都很讨厌那些手里有权的贵族吧?可为什么只要有了权力,哪怕是一丁点,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用它侮辱伤害勒索那些和你们一样苦的人呢?”
城门兵惊恐地埋着头。他们畏惧圣徒十字徽章代表的权势,他们后悔自己不长眼,但他们其实不明白玛丽安话里的意思。被权力伤害过的人如果抓到一点权力,往往会迫不及待地用来伤害别人。一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权力会失去,二是自己受过的苦能够让别人也尝尝,这种感觉很爽。
玛丽安朝那些卫兵摆摆手,叹口气。她知道自己的话其实等于白说,可是也只能如此。
没什么热闹看了,人们纷纷散开。玛丽安纵马赶上城墙边正想离开的流浪汉,用马鞭轻点一下他肩颈处灰色的渡鸦刺青。
“你是渡鸦旅团的人?”
流浪汉慢慢抬起头,蓬乱的头发下面,有着咬肌结实的腮帮。一道很旧的刀疤从嘴角豁开去,让他的笑容看起来有点阴冷。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尊贵的夫人。”
当啷一声,玛丽安掏出一个金币扔在他脚边。流浪汉笨手笨脚地用五个指头去撮。黄澄澄的小精灵顽皮地从他指头缝里溜走了好几次。他的手很抖,不知道是因为酒喝多了,还是见到钱太激动。
玛丽安皱了皱眉毛,一鞭子抽在他肩膀上。灰色渡鸦的翅膀上浮出一道暗红鞭痕。
“下次装酒鬼的时候,记得手不要抖得那么难看。”
她从马鞍上弯下腰,把手放在流浪汉头顶上。路过的人都以为这个好心的贵族修女正在为他做一个简单的赐福祷告,只有流浪汉自己才能听见玛丽安压得极低的威胁。
“这一路上你们都在跟踪我,你们这些阴魂不散的乌鸦,”她冰冷地说,“要不是法利斯主教在附近,你会象你那些同伴一样,变成冰棍或者火把!”
威胁过后,玛丽安露出亲切的笑容。按照赐福祷告的标准仪式,她把手掌在流浪汉头顶旋了一圈:“愿主保佑你,迷途的人。”
流浪汉惶恐地跪倒,谦卑地把脸凑过去吻玛丽安的深黄色鹿皮靴。当修女的马走远之后,他扔下铺在石板上的肮脏座席和席子上的杂物,遁入附近阴暗的小巷。他走进一间小屋,脚步很快,七拐八弯地上到二楼。一个身形庞大的汉子一动不动地坐在窗边,手边一杯喝掉大半的粗质烈酒。
“首领,长老吩咐要找的那位女士,今天进了城。”
“知道了,”大汉对前来禀报的手下挥挥手,“这事你跟商会那边也说一下,去吧。”
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消失后,大汉再度把手伸向烈酒。金黄的液体流过喉头的时候,如同火烧的感觉流遍了他全身。“如果真十字架在那女人手里,”大汉喃喃地自言自语,“那么毕维斯的死,她也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