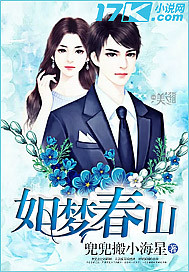司潇凝视着这只玉镯,与欧阳静腕上的那只,如同一母同胞的双生子,无论是款式,色泽,纹理,丝毫不差。她还没忘记,那个叫漪儿的丫头给自己这玉镯的时候,说这东西……是捡来的。
在湖边,司潇找到了漪儿,“漪儿,上次你说这玉镯是你拣来的,这么好的东西,你在哪儿捡的?”
“喏,就是上次我打扫水阁那边‘容月堂’的时候,在床上枕头边捡的。”
“床上……枕头边……”司潇喃喃念着。突然,她双眼直直的盯着前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回到闺房,司潇仍默默想着什么。佩弦从小丫头的手里端过一碗银耳羹,道:“小姐,喝口银耳羹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佩弦,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你看你,年纪和我差不多。这双手,哪像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
“小姐的心可真好,不过我们这些下人,哪个不是这样,整年的把手泡在水里洗这洗那的,哪能和小姐您的手比呢。”
司潇轻轻握着佩弦的手,那粗糙的皮肤和突出的指关节让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努力的回想着,慢慢的,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一丝奇诡的笑容。
有些萦绕在她心头的疑惑,因着这一双手,已经有了答案。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钱府终于如司潇所料的,不再是平静的一池碧水了。然而什么时候自己才可以施展计谋,却仍是个未知。直到半个月之后……
那个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辰。只有无处不在的黑暗,笼罩着整个钱园。
富叔佝偻着背,向夫人回报着府中的大小事务,不时地咳嗽着。夫人见状,关切地问道:“富叔,你近来这身体可是不爽利啊。自己多小心些,年岁大了,可不比从前年轻气盛的时候啊。”
“多谢夫人关心,我这身体也就这样了,都十几年了。”
“那要没别的事,你就先回去吧,路上小心那。”夫人轻拍其背,道。最后那句“路上小心”还特意加重了语气。
园中一片寂静,只有风吹动树叶的沙拉声。
富叔没有回他的卧房,而是经了条不为人知的小路绕到了湖边西侧,在湖边的一处凉亭停下,小心翼翼的环顾四周,见周围无人,便蹲下身去,用手轻轻拂去地上的尘土,露出一块斑斑驳驳的青石板来,他又从袖子里摸出一支女子发簪,对着板上一个极小的洞孔,插了进去。
只听“咔嗒”一声,似是有什么机关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