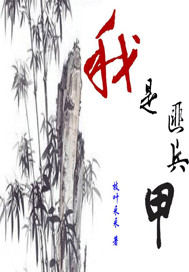接连几天,文天祥的心情都有些沉闷。刘子俊和陈龙复离去前脸上的失望他看在眼里,但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做才能让二人不失望。
百丈岭整军以来,周围的人都形成了习惯,有什么疑难事情找文天祥,凭借传说中的“天书”和文大人能力,对一切都有答案。而此刻,偏偏文天祥自己与周围的人一样迷茫,一样困惑。
文天祥当然不知道,此刻困扰着他的问题,在另一个时空居然困惑了几代人。文忠和文忠的后辈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困惑下去。并且,这些人的见识和智力都不比他这个大宋状元差。他只想凭借自己将这些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让新的华夏从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在相对完善的框架上。让我华夏不再坠入兴衰交替的轮回,这是文天祥在承接了文忠记忆的同时,承接的一份责任。
他当然找不到准确答案。确定的说,文忠记忆中的答案,也是支离破碎的,很多地方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文忠要求民主。而对自己所在的党派和所坚持的理想,他又要求绝对服从。
这一点,文天祥做不到。他羡慕文忠记忆中那种抓把黄豆也可以进行的,简单而朴实的选举。但却无法相信文忠理想中的世界大同。他认定那种让底层百姓掌握选举权,以下制上的官员选拔方式,却不得不面对很多令人失望的现实。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让他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但不继续坚持下去,他又看不出凭借新式武器强大起来的大宋,与原来那个有什么不同。
如果官员的任免权力依然掌握在他的上司手中,与百姓无关的话。那么,军队越强大,也许官员压榨起百姓来越肆无忌惮。因为任何时候,军队都掌握在朝廷手中。就如现在的大元,强大到世界上无可匹敌,但生活在其统治下的百姓却是世界上最困苦,最无保障的。
纷乱的念头困扰着他,再次超越了他的承受能力。以至于对自身实力认识比较清醒的他,都忘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此刻考虑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为时尚早,大宋能不能在北元的打击下生存下去,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对时局乐观者大有人在,特别是邹洬挥军攻克广州后,军心民心大振。很多人纷纷到丞相府献策,建议文天祥再组一军,誓师北伐,将已经被破虏军梳理过一次的两浙拿回来,光复大宋旧都杭州。还有人建议文天祥传檄天下,号召天下豪杰起兵勤王,趁这个机会发动对北元的最后一战。在胜利氛围的笼罩下,一些承担保卫福建任务的破虏军将领也动心起来,接连上表大都督府,请求集中力量与达春决战。就连偏安到流求的行朝,也派陆秀夫专程赶了回来,与文天祥商议将皇宫迁回福建的事。
尽管理智中,一个声音不停地提醒着文天祥,北元不会这么容易被击垮。但眼前的局势和民心却让他感到胜利也许并不遥远。此刻,科学院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耗时尽一年的火铳研制工作终于完成,林恩老汉带着第一批定型的五百杆火铳,正顺着闽江向福州赶。
“老文啊,你最近可愈发瘦喽!”一见面,林恩老汉就笑呵呵地问候。年余不见,老人的精神越发健旺,一张黑脸不知道是在路上被太阳晒的,还是因为兴奋,带着浓烈的潮红色。
“还好,还好,我本来就是这种体格,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子。不像您老人家,七十几岁了还能轮得动大锤,和古时的老黄忠差不多。怎么样,路上倦不!”文天祥丝毫不以林恩对称他“老文”为忤,一家人般笑着答应。
“你们几个,也不说给丞相大人弄点吃的补补身子。难道做人的亲随,就只管防范刺客么!”跟文天祥寒暄完了,林恩老汉回过头来,对着完颜靖远等人倚老卖老。
‘这关我们什么事情!丞相饭量小,我们又不能硬塞饭到他嘴里’完颜靖远郁闷地想,看看文天祥仙风道骨地瘦弱样子,心里随即涌起几分内疚。裂了裂嘴巴,借着帮亲兵抬军械箱子为由跑远了。
“该给丞相大人添个人暖被子了,身边都是男人,难免照顾不好!”林恩老汉看着完颜靖远开溜,自言自语般说道。自从百丈岭见到文天祥那天起,他就没把文天祥当作丞相来看待。而这种亲切的态度,也让文天祥觉得很舒服。与他交谈时如和自家人谈话一样轻松随意。于是,在丞相府的属员当中,林恩老汉成了最特殊的一个,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提,别人不敢干预的事情,他敢插手。
当然,林恩老汉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分寸。自己理解不了,无权限干涉的国事,他从来不乱参与。
“那个,那个,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文天祥持续多日的烦躁心情,被林恩老汉几句亲切的问候涤荡了个干干净净。不知不觉间红了脸,迫不及待地将话题向其他地方岔。
他的妻子儿女均在赣南会战中被李恒掳走。妻子和儿子死于押解途中,两个女儿被忽必烈没入皇宫当女奴,从此生死不知。破虏军在福建站稳脚跟后,不断有亲信幕僚和好友想给他再娶一房妻子,均被他以国事繁忙为理由拒绝了。
内心深处,文天祥忘不了妻子的身影。同时,因为接受了文忠的记忆,这个时代别人眼中的贤良淑德,品行和美貌俱备的女人,已经很难再入他的眼。三年来,唯一让他动心过一次的,就是那几句“长干行”。可当时吟唱着此曲的人,偏偏又是他无法娶的那一个。两人的身份、名声和地位,注定了他们只能彼此以欣赏的目光相对,而不可逾越雷池一步。
“以后再说,你不过四十多岁,以后的日子很长呢,难道就孤零零的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不成。再说了,你被照顾得好一点,也能多活几年。把跟我老汉讲过那些好事儿啊,挨个给实现了!”林恩老汉如文天祥的长辈般,带着嗔怪的口吻说道。顺手自随从身边取过一个长条木盒子,递到了文天祥手里。“拿着,这枝是老汉我亲手打造的火铳,试过几十次了,绝对不会炸膛!”
文天祥接过木盒,轻轻打开。一杆六尺多长的火铳,和一把鲨鱼皮鞘匕首静静地躺在红绸上。用绿钒油(浓硫酸,古人用煅烧绿钒(硫酸亚铁)的方法获得)侵蚀过的铳筒和匕首柄被太阳一照,散发出淡淡的蓝光。
有股冷冰冰凉嗖嗖的感觉从脑门直冲而下,一瞬间,文天祥感觉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慢慢模糊的目光里,文忠当年在黄崖洞中渡过的岁月,一一浮现在眼前。
眼前这杆火铳与文忠等人在黄崖洞中制造的“七九”“、八一”式步枪,在技术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包含在制造者内心深处对国家与民族复兴的期待,跨越七百余年,却无丝毫不同。
以文忠的家世和背景,他应该投靠当时的中央政府才对,是什么驱使他站在了自己家族的对立面?甚至想把自己的家产与周围人分享?这绝对不谨谨是“车马轻裘,与朋友共”的侠义思想作怪,而是他当时为了国家而不得不这样选择。
那一刻,文天祥再次分不清哪一世是庄周,哪一世是蝴蝶。如果能知道文忠为什么如此选择,也许他就能参透数日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矛盾。但偏偏那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相距过于遥远,文忠的影子犹如隔着一团迷雾,无论如何凑近,都无法看得清晰。
见文天祥的脸色一刻不停地变幻,林忠老汉楞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状态下的文丞相,仔细看了看盒子里的火铳,突然醒悟到了什么,抱歉地拱了拱手,解释道:“丞相勿怪,这个火铳,的确和最初那个设计有很大差别,长了许多,引火孔也改到了侧面!”
说着,林忠老汉从盒子中将火铳取了出来,亲自给文天祥示范其用法与改进的原因。“这个,引火孔放在侧面,是为了防雨。您也知道,咱南方雨水多,容易耽误事儿。上次张弘范就是趁着雨天,火炮不易击发的时候,打了大伙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将火孔放到侧面,再于上面遮个铁片,雨水就淋不到了”
文天祥的思绪被从庄周晓梦中拉了回来,随着林恩老汉的介绍,回到火铳侧面的孤行防雨盖上。此时,他才注意到这杆火铳与萧资设想中那杆差别甚大,联动击发的打火锤和炮子点都不见了,代之的是一个侧面的燧石轮和一个药线孔。
“火绳枪”一个名字脱口而出。虽然文天祥自己对此也懵懵懂懂,但这个词汇,显然在文忠记忆里占据着很特殊的地位。
“火绳枪,这个名字贴切!”林恩老汉对文天祥的眼光佩服得五体投地。利落地从木盒边角处翻出一个黑色布袋,自里边拿出寸余长的药捻来,塞进引火孔里,一边示范,一边说道:
“纸炮子儿太小,容易掉出来。引火孔开在侧面,就不能用炮子儿了。大伙想了好些日子,才想到了用药捻子的办法。这东西制造起来简单,引火也方便。切成一寸长的火绳,装填起来比炮子儿还快些。燧轮制造,也比打火锤简单,还不用弹簧回拉!”
说着,老汉取出纸包火药,铅子儿,按部就班地塞进内膛,合拢外膛,将火铳递回文天祥手里。
文天祥接过火铳,自手掌间传回的熟悉的感觉让他心情愈发激荡。平端,瞄准,对着院落中一棵老树伸展于半空中的枯梢扣动了扳机。
燧轮回转,擦出淡蓝色的火花。药绳被引燃,火苗瞬间钻进火铳里。
“乒!”清脆的枪声在丞相府内回荡,半空中的树梢应声而落。
文天祥取药,装弹,添火绳,一枪又一枪打下去,足足打了二十余枪,直到盒子内的火绳用完了,方才罢手。正在丞相府内各部门工作的官吏都被枪声惊了出来,站在各自的屋檐下,看着文天祥拿着仙术般的神兵指哪打哪,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
“有如此利器,还怕蒙古人不退!”刹那间,文天祥的内心又被自信充得满满的,把火铳交回林恩老汉手里,大声问道:“老丈,这东西射程多远,威力与破虏弓比到底如何?”
可能是被硝烟熏得太厉害,林恩老汉咳嗽了几声,强压着身体的不适答道:“按丞相教导的标尺,大概八百米。不过,打到那个距离,基本上就是瞎猫抓个死耗子,纯靠蒙了。真正有准头,有力气的距离,是二百五十米以内,比钢弩远,也比钢弩狠。一百米内,能打透柳叶甲和罗圈甲。就是装填麻烦些,比钢弩还慢。”
“比钢弩还慢!”参谋长曾寰惊诧地问道。刚才文天祥演示火铳用法,大伙光顾着惊叹火铳的威力和文天祥用起火铳浑然天成的熟练度。却没注意到火铳从装填到发射,整个过程比弓箭慢得多。回头想想,以文天祥所表现的熟练程度,每发射一颗弹丸,敌军可射三箭,如果对方是个熟练射手的话,可能射出四到五箭不止。这样,即使装备了火绳枪,军队在平原与蒙古军相遇,面对蒙古人的漫天箭雨依然没有优势。
“比钢弩省材料!火铳造起来虽然慢,但弹丸用不值钱的铅籽儿就行,造起来简单,小学徒一天也能造个几百颗。钢弩太费材料,咱邵武的铁矿,这两年炼了钢,大部分都造了弩箭,要求手艺又高,不是熟手干不了,为了保密,还不能把活转包给别的作坊干!”林恩横了曾寰一眼,摇头晃脑的解释。
火绳枪的诞生,凝聚着科学院所有人的心血。为了制造不易炸膛的枪管,先后就有四个工匠被炸瞎了眼睛,毁了相貌。有人看到最后成品还乱挑毛病,这种行为让林恩老汉心里非常不乐意。
从文天祥手里拿回火绳枪,顺势从皮鞘中取出匕首,轻盈地一捋,咯嚓一声,将匕首装在了枪管上。众目睽睽下摆了几个花式,林恩老汉说道:“装备了火枪,就不需要再配刀。鞑子靠近了,把匕首装在枪头上,就是杆现成的花枪,直接挑翻了他。他跑远了,我卸下刀,借着用铅籽儿追,看他跑得快,还是我的弹丸飞得快!”
不知是因为生气还是劳累,老汉的脚步有些虚浮,喘了口气,杵着火枪试图站稳,却一不小心跌坐到了地上。
“老丈!”文天祥见状,赶紧伸手去扶。林恩老汉笑着推开他的手,讪讪道:“人上了年纪,这腿脚就是不灵光了。”接连努力几次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却觉得腿越来越软,仿佛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
林恩老汉大惊,用尽全身力气向起站,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手一张,直直地栽了下去。
文天祥赶紧去抱老汉起来,隔着单衣,发觉林恩老汉的身体如火炭般烫。再看老汉的额头,嘴角,都有淡淡的青黑色透了出来。
“快去请大夫!”曾寰冲着楞在一边的亲兵喊道。林恩老汉虽然为人不拘俗礼,也爱管些年青人的闲事,但在破虏军中的人缘一直不错。很多低级将领都是他的弟子和晚辈,如果林恩老汉因为自己的一语无知冒犯而病倒了,那样,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不算别人,科学院院长萧资第一个会冲到福州来找人拼命。
“宪章,不关你的事,他大概是路上中了暑吧,应该会很快好起来!”文天祥见曾寰着急,低声安慰道。抬眼看看围拢在自己身侧,与与林恩一同送火铳来的随从,却发现,很多人脸上都带着潮红之色。
一股不祥的预感快速涌上文天祥心头。
被李兴从两浙掠回来的金大夫提着药箱子匆匆赶来。抱起林恩的头放在腿上看了看,又翻了翻老汉的眼皮,突然伸手将文天祥推到了一旁。
“怎么回事?”文天祥被推得一楞,不顾追究金大夫的无礼,低声问。
“赶快回去,把衣服用热水烫了,用白酒漱口!”金大夫抬起头,对着所有人说道。指指林恩老汉,接着命令:“跟他一起超过两天的所有人都不许离开,文大人,赶快给属下找个院子。要人手,只要学过医,不怕死的,统统都要!”
“怎么?”丞相府所有人都发觉试态不妙,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瘟疫,春瘟!不想染上的,赶快去换衣服,漱口。五天内别出这个院子,别跟他人往来!”金大夫声嘶力竭地喊道,却忘记了病情最严重的林老汉,此时正躺在自己的腿上。
蒙古人的致命一击悄然来临。四月初,随着前线频频传回的捷报,连城、宁化、清流陆续传来大批百姓和士兵病倒的消息。其中与达春作战的陈吊眼部损失最大,四个标人马几乎有一半士兵染病,不得不放弃了对上杭的攻势,撤到漳州的龙岩去修整。
随即,永安、沙县、剑浦陆续出现了大批病人,甚至连许夫人的兴宋军也有人被传染。 紧接着,福州、漳州街头上都发现了病人,很多人头一天到工厂上工还好好的,第二天就再也爬不起来。要好的工友前去探望,却跟着染病。
沿着槿江、九龙江和闽江,瘟疫以不可控制的速度继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