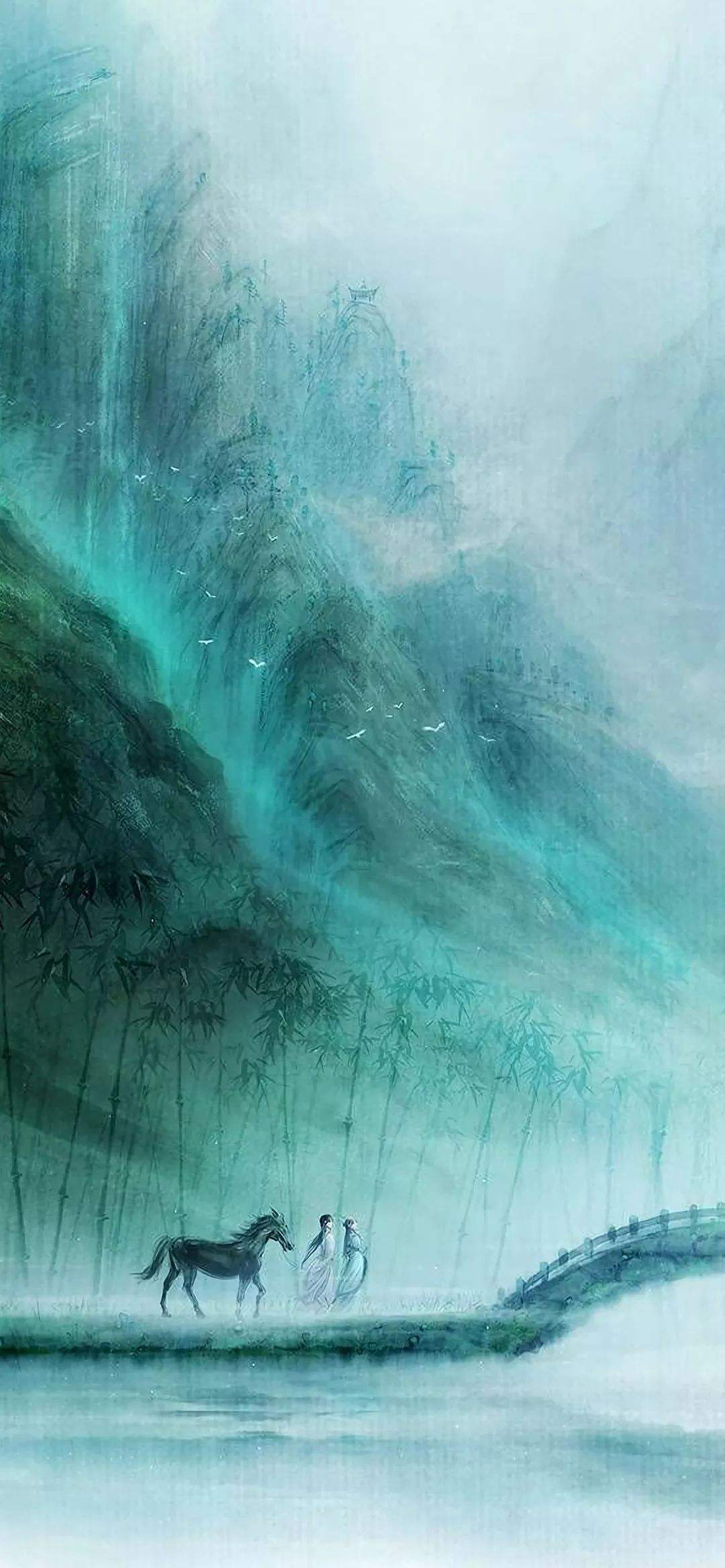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魔法师。。。。。。”一桌桌站起来的顾客们直勾勾地望着我手掌上的两团火苗,他们没有想到身份显赫的魔法师会跑到都市酒馆里闹事。
“魔法师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角落传出一声不平的喝叫,我垫脚眺望,那是位看起来挺富裕的公子哥,他旁边就是被我一瓶子破相的嘴贱小人。
我一步步走向他,周边的群众们个个义愤填膺,但恐于我手上的火焰,没人站出来阻拦我。“你刚才说什么,我欺负人?”我散掉火元素,手掌撑在桌面,歪着脑袋看他。
“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把我朋友伤了,还不算欺负人吗?!”公子哥满脸大无畏的样子,他挺直了胸脯喊道。
你那朋友嘴贱到一定份上了,还不叫理由?抬起手来冲手心吐点口水,飞起一嘴巴扇得公子哥头壳磕碰墙面,“啪——嘣!”两声脆响回荡在酒馆之中。“我就没理由了,你能怎地?”伸手按住他的侧脸蛋,手掌不停扭动,按得对方皱在一起的嘴唇发出“咯咯”悲鸣。
光大姐抓起脚下胖子头发,眨眼功夫亚麻色板寸褪成银色,毫无光泽。再瞧胖子的脸蛋,犹如脱水猪肉,皱皱巴巴的脸皮已经贴不住肉,随意耷拉着,看上去很恐怖。“我给你们七秒钟的时间,滚!”
这次光大姐的话十分管用,见过她大变干尸的顾客们逃地比猴子都快,果然还没到时间,屋子里只剩下我,光大姐,木乃伊脸的胖子和两位挨过打的公子哥。
“以后记着点,我要打你的时候你要主动把脸探过来,别等我迈步近身。”松开手掌,我揣了两位公子哥几脚,轰他们滚离酒馆。光大姐将胖子的脸和头发恢复如常,一脚蹬在他屁股上。胖子踉踉跄跄出了房门。
“老板,点菜!”光大姐随便找张桌子坐下,她冲空中挥挥手,狠狠地拍在桌板上。
酒馆老板战战兢兢地跑到桌边,“吃,吃什么?”
“我要喝酒。”光大姐沉默一会儿,她看看我,手指敲打桌面。“你陪我喝!”
我坐在她对面,大白天喝酒,影响不太好吧。不过对于我们刚才的举动来说,再糟糕点也未尝不可。“喝就喝呗,我没意见。”
没过多久我便着实后悔同意陪酒了,光大姐的酒量是我目前碰见相识的朋友里最强悍地,我用杯子她用瓶子,楞把我灌得迷迷糊糊,人家反倒小脸微红,口齿伶俐。
“我说,大。。。。。。大姐。”我的舌头有些转不过弯,“你今天到,到底看见啥了,难受,难受成那样?”
“别多问,陪我喝就是了。”光大姐眯着眼睛,她又帮我满上一杯,径自对碰,新上的酒瓶喝得一干二净。
不说,嘿嘿,不说我有办法让你说。我也是被她灌得心中狂野起来,一口干掉杯中甜酒,偷偷从怀里掏出先前专家妹妹给我的自白剂,上次用过之后还剩下半瓶。“老板,没酒了,上酒!”假装拿酒的样子,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接过老板的两瓶新酒,往其中一瓶里倒了大部分药剂。
一边晃荡瓶子,我一边回到座位,将下药的那瓶摆在光大姐跟前,我用另外一瓶给自己的杯子斟满,“来,干!”说完碰杯,仰头灌进喉咙。看着大姐喝完瓶子里的酒,我心中暗笑,这下你想不说都难了。
接着喝过三五杯后,大姐终于显露疲惫之色,她用手掌托着脑袋,摇摇欲坠。“我,我好像不太对劲。”微弱的话语传进我耳中,我打个酒嗝,嘿嘿一笑,“喝,喝多了呗,走,咱们上楼歇会。”
桌上留下几枚金币,现在正是我兴奋之时,酒气冲头,自然多给了赏钱。拉拉扯扯回到二层房间,我拍拍脑门清醒清醒,斜眼观瞧光大姐的漂亮大眼,如今已然通红一片。
“光大姐,大姐?”我搀扶她坐在床上,双手扶住纤瘦的肩头,防止她直接倒下睡去。
“。。。。。。唔?”光大姐的头耷拉着,她想打起精神回应,可抖了几下终究没能抬起。
“你——你在大街上,看,看见啥鬼东西了,吓成那样?”有酒壮胆,我也不去小心翼翼地测试状态,劈头就问。
“什么鬼东西呀,那是我爸。。。。。。”光大姐的声音很沉,尤其是爸字,几乎吞进了肚子里。
“啊?”我打个激灵,事情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你,你爸?你爸怎么在这儿?”好奇心涌了上来。
“我本来就是卡纳克人。。。。。。我爸是个乞丐,自然就跟城里要饭了。”光大姐摇摇脑袋,她似乎不太想说,可是药物的效果迫使她说了出来。
光大姐的父亲是个乞丐?我更加没有头绪。“那你。。。。。为,为什么不跟他相认呢?”
“我——”她抓抓头发,抗拒意识更加强烈,“我不敢,心中害怕的要命。”犹如文字般的话音飘出,我要不是注意力集中在了她身上,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害怕?跟爹见面有啥可怕的?我越来越好奇了。“你在害怕,害怕什么?”伸伸舌头,我希望可以让它灵活一点。
光大姐闭上了眼睛,她的表情很痛苦,双手企图捂住脸庞。“我怕我会伤害他。。。。。。”泪光从眼角滑落,大姐的鼻头浮起红色。
我看得出她的内心正在挣扎,伤害自己的父亲这种事不是随便就能说出口的,更何况她沙哑的嗓音带着哭腔,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要不,你讲讲你的身世?”脚步蹒跚来到桌前,我到了杯清水,一边喝一边聆听光大姐的故事。
大姐睁开眼睛,她蒙着红雾的双眼凝视我许久,才幽幽地开口道来:“我,是一名弃婴。爸爸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城外捡到襁褓中的我,由于被两只颜色各异的眼睛吸引,才把我带回去收养。
爸爸原本也有自己的工作,他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但因为好赌,每月的工钱往往扔进了狐朋狗友的口袋中。而我,则是靠妓 女的奶水长大。爸爸所居住的贫民区中,风尘女子不在少数,而有些没注意怀上孩子的女人们,便成了我的奶娘。”
“哦。。。。。。”我掏掏耳朵,没听错吧?平时见她趾高气扬的样子,虽然听格罗佛说她是团长买回来的,可从来没想到大姐还有这么惨的身世。
“我在八岁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那些女人的住处和接客房,看着不同地叔叔们来来往往,心中曾想过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也要和她们一样生活。那时的我天天盼着长大,盼望自己也能和她们似的挣钱养活自己,挣钱给爸爸花。”
光大姐的声音波澜不惊,但我还是打个哆嗦,这小女孩的梦想着实令人难受,不得不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不经人事的孩子们。
“后来,爸爸有个月赌得身无分文,他偷了裁缝铺的收入,被店主开除了。没有经济来源,爸爸走投无路,妓 女们也不再给我提供住处,我们流落街头,过上街头要饭的日子。以前,那些女人们时常夸我的嗓子好,唱歌也好听,教了我不少歌曲,我和爸爸要饭的时候为了吸引路人,便常常献歌。
这个方式的效果很不错,时常及一顿饱一顿的我们也逐渐吃穿不愁。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虽然经常露宿街头,可总能和爸爸待在一起,不像以前一个月只有几天见得着他。”
光大姐嘴角微微上扬,她很少笑得如此甜美。我叹口气,不管怎么说,要饭总比跟着烟花女子混强一些,她当初那个目标总算能转变了。
“后来,够吃够喝了,爸爸拿多余的钱又去赌博,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全都打了水漂,城里的过往行人们也听腻了我的歌,钱越给越少。最终,爸爸决定离开那里,我们开始旅行。
这次旅行整整度过四年光阴,我们几乎走遍了卡纳克的每一寸土地。但是无论挣钱多与否,爸爸仍旧输得干干净净。那时我已经十二岁,心中对爸爸的赌瘾很是不满,每次看着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隔夜不见,别提多失落了。”
光大姐的语气像个小女孩,她回忆起当初的感受,眉头紧皱。“我们的旅途达到了最终站:贝鲁坎特。当时我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在这里停留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而且他晚上总会消失一会儿,留下孤零零的我躲在巷子深处避风。
也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没有赌博,我们乞讨得来的钱快能装满两个口袋,看着那么多钱我感觉自己合不住嘴了。然而,一天我睡觉起夜的时候忽然发觉爸爸不在身边,两个装钱的口袋也消失不见。我明白爸爸又去赌了,顿时大哭起来,靠着墙根整整哭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