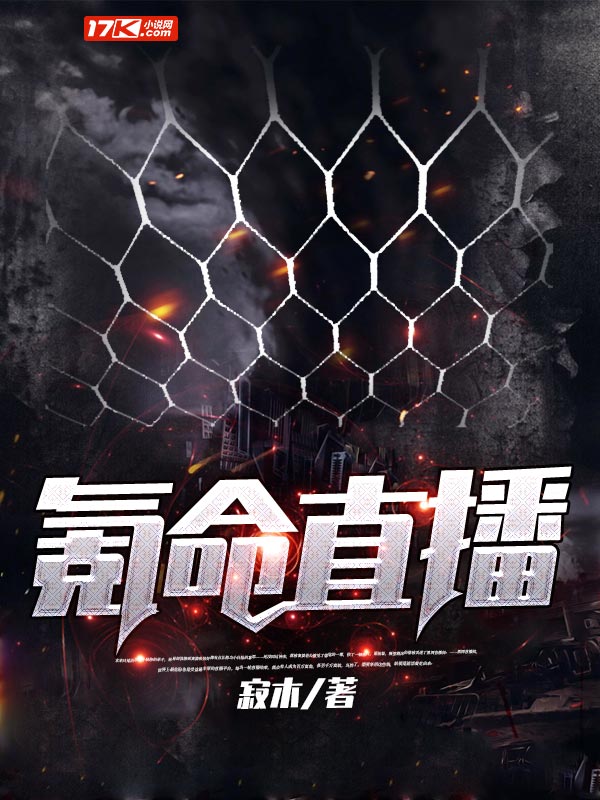陈红说她已经在这儿等了我很长时间了,但不是为了要采访我。实际上,校园十大风云人物这个专栏原来是老何想出来要做的,也就是为了在学校里搞点典型模范之类的宣传。现在陈红已经找了其他学生做这个报道了,无外乎就是什么校园歌星啥的,并不打算拿这个事烦我。
“哦,那陈大记者来是——?”
“没有事就不可以来么?”陈红反问,她的语气很有些无力。我总觉得自打我昏迷住院之后,我身边许多人都变得有气无力的。
“当然可以来,欢迎参观本公司。”我大度地做出了欢迎的姿势说。
“周序哥哥,你现在,我是说有时候,有没有感到一种想呕吐的感觉。”陈红盯着面前的茶杯忽然这样问。
“咦,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奇怪地看着陈红。她的脸上现出一丝红晕,但还是坚持着又说了一遍:“周序哥哥,你一定觉得我不可理喻是不是?可是,这真的很重要,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时会突然出现想呕吐的感觉。”
我说:“有这样的感觉又能说明什么呢?”
“那么说来,真的有。”陈红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已经憔悴不堪。我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便轻柔地对她说:“陈红,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能不能全部告诉我?”
陈红不说话了,低头盯着那杯茶,看碧绿的茶叶在水面上轻轻荡漾着,就象盯着微观世界中的一叶扁舟。
我干脆坐到她身旁,叹息着说:“那天在医院里,丽娜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们在谈论什么?这些为什么都不告诉我?知道吗?丽娜现在就象换了一个人,老是坐在那儿发呆,搞得我也精神恍惚,这样下去,恐怕我真的要死了。”
“不要,不要提那个字!”
陈红紧张地象刺猬似地缩了缩身体,难以形容的恐惧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她的脸上。
“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呀,就算我真的得了绝症,也不必这样遮掩嘛。”我毫不在乎地大声说着。这种躲闪和掩饰已经让我厌倦了。
“不,不是因为那个。不仅仅是因为-----”陈红呑呑吐吐地说着。
“那是因为什么?”我笑了,说:“你是不是想说,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比如说------”
我正想举例说明,但一时找不到好的例证,绝症?开玩笑,真的是绝症?
我在想词的时候,陈红毫不迟疑地将手掌捂到我的嘴唇上,这是她第二次做这个动作了。我飞快地抓住了她洁白柔软的手,那上面还有一股温暖的香味。
“说吧,陈红,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呢?”
我注视着陈红的眼睛。
“你这样不觉得很累,很痛苦吗?你在受着折磨,而且是自我折磨,对不对?”
我接着又说。
我相信,我的话已经触及到陈红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陈红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手在微微颤抖,却没有想抽离我的手掌。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似地说:“有件事我一直,一直想不明白,我也觉得太荒唐了,可是却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每天都在想,想得发疯。可是又不能对别人说,不能对丽娜姐说,不能对同学说,不能对郑站长说,更加不可以对你说。我都快憋死了,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
说着说着陈红的眼眶就红了,她把脸埋进了手掌中,瘦弱的双肩在轻微地抖动着,象是在发泄着心中的苦闷。
我轻轻地在她肩膀上用力按了一下,然后将她搂在怀中,用力地搂抱了一下,不超过两秒钟。
“说吧。再荒唐的事我都碰到过。”我柔和地说着,我想这是事实,再荒唐的事,我的确碰到过不少了。
陈红仰起头来,脸上满是泪水,一副梨花带雨的娇柔模样,对我说:“周序哥哥,我有个请求,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不要见怪。”
我笑着说:“有什么请求呀,我怎么会怪你呢?又不是叫我去杀人放火。”
陈红破涕为笑道:“那肯定不是的啦。”
“你说吧。”
“我——”陈红拖长了声音,一脸认真地说,“我想看看你的后腰可以吗?”
我愣住了:“什么后腰?”
“就是你这儿。”陈红指了指我的腰部,羞羞答答地说,“只看一下,好吗?”
听到她这么说,我倒也有点害羞起来。面对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我总不能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就脱衣服吧。陈红跟我总不会做那种事的,但这算什么?所以我犹豫了,这算什么请求?
陈红看我的脸色就知道我想歪了,她急忙说:“我只看一下,绝对不会碰你的。”
我笑着说:“你要碰我也行,我也碰回来就是了。”
陈红涨红着脸说:“你又要胡说八道了。快点嘛。”
这一声娇滴滴的“快点嘛”,差点让我流鼻血。不过既然人家小美女都这么说了,我也只好把衣服撩了起来,说:“快点看哦,要是被别人看到咱们这个姿势,你周序哥哥的一世英名就完蛋了。”
陈红咬咬牙,心一横就俯下身去,拉起我的衣服朝我后腰上看。
我傻乎乎地撩着衣服等了很久,只觉得后背上都凉飕飕的,陈红却象泥塑一般停在那儿不动了,一只手始终保持着撩起我衣服的姿势,就那么僵在半空中。
她看到什么了?
我转过头叫了她一声,开玩笑地说:“哎陈红,看好了没有,这可是你大哥的隐私部位哟,你包姐姐也没看得那么仔细呢。”
陈红“啊”了一声,手一抖把衣服放下来了,脸色更惨白了。
我疑惑地问:“你到底看什么呀?”
陈红自言自语地说:“太,太奇怪了,真是这样。”
“什么真是这样?”
陈红脸朝向我,脸上因为激动而显得通红。
“哥哥。”
“什么?”
“你真是我哥哥。”
“什么意思?”
“你真的是我的哥哥。”陈红象是在梦呓一般地反复地说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