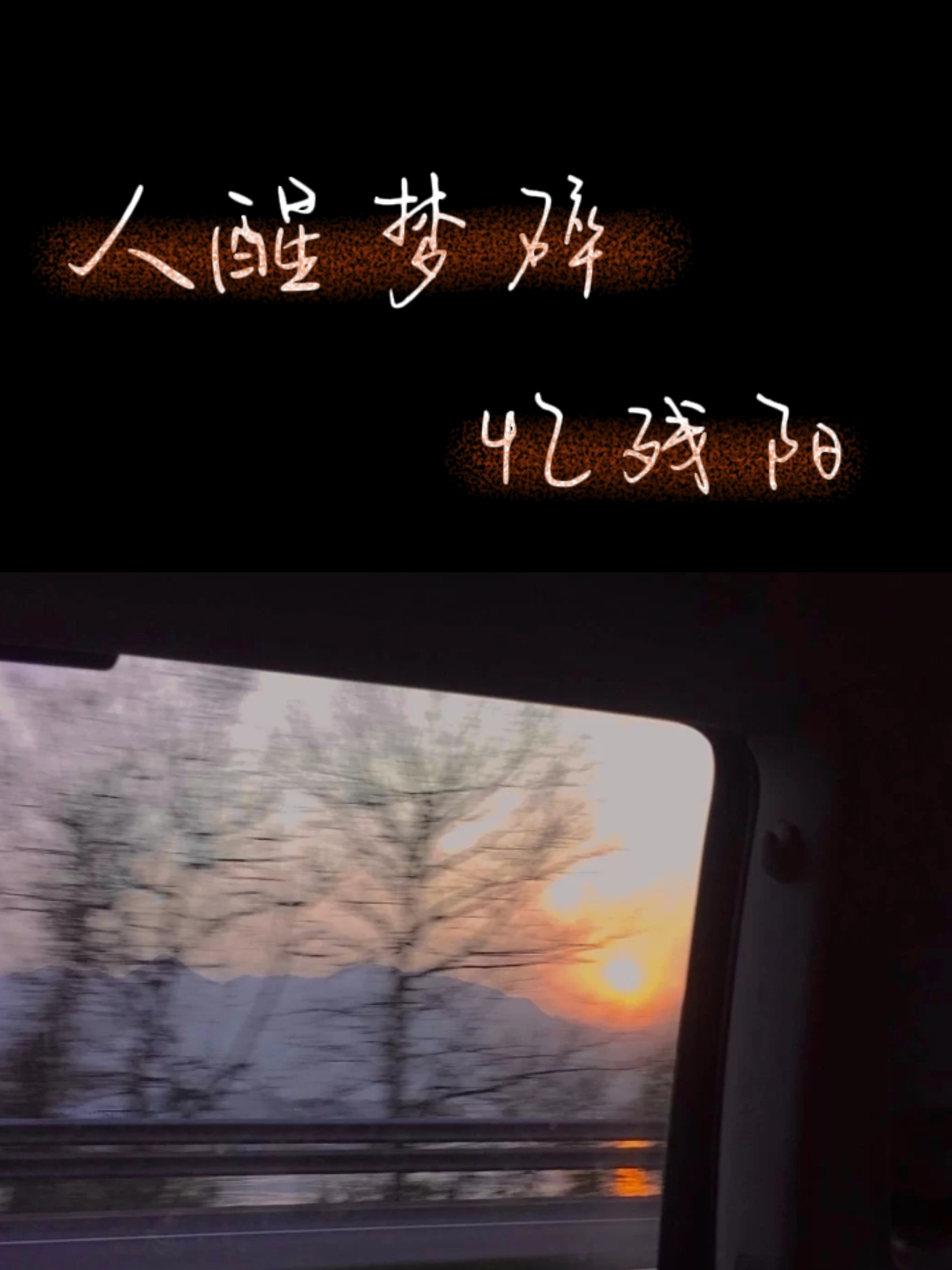所有人一走,故里瞬间从床上弹起。头上繁重的头饰,差点没让她闪了脖子。
故里使劲扒拉了一下头上的头饰,但无果,并不是她能轻易取下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戴上去的。
现在整个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才开始打量起自己所处的环境。
一间古色古香的老式厢房,雕花木窗上贴着几个醒目的双喜字。红色帐幔挂了满屋,不像结婚,倒有些诡异。
故里想到对方说的那个素未谋面的人,顿时一股恶寒从心底升起。
故里四处打量了一下,整个厢房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一眼望去,满眼的红。
这时,一个梳妆台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方葵形铜镜,映衬出一抹娇俏的身影。镜子里的人影,脸上画着浅淡的妆,衬的那张有些婴儿肥的脸,看起来更加俏皮。
但此时故里并没有心思看自己那张脸,吸引她注意力的,是镜子旁边,用红布遮住的一个东西。
那东西有些高,足有她的小手臂那么长,不过看起来不大。
故里心中疑惑,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用红布来遮住的?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她缓缓走近那个东西。
故里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她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那个东西,不是寻常之物。
再联想到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快要破土而出。
故里伸手,指尖触碰到红布时,又骤然缩了回去。
虽然心里已经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东西,但她还是忍不住自己好奇心,想掀开看看,验证自己的猜想。
像是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故里双眼一闭,手一伸,倏地一下掀开了那张红布。
“卧槽!”一声惊呼,故里猛的向后退了几步,差点被宽大的裙摆绊倒。
待她稳住心神,这才仔细的看向那东西。
果然和她猜想的一样。
一块牌位,不知道用什么木料制成的,通体泛黑,上面只有两个字,却让人看着有些渗人。
长安。
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却让故里突然有种不适感。
她缓缓走近,站在那块牌位前,鬼使神差的将它拿了起来。
顿时,故里只觉一股暖意沁入心间,让她没来由的觉得鼻间有些泛酸。
故里拧眉,奇怪自己突如其来的异样。
不过很快,那种异样的情绪就从心间消散开来,就像从未出现过。
故里收起自己的疑惑,仔细端详着手里的牌位。
她翻来覆去看了个遍,并没有发现其他特别之处。
除了“长安”两个字,上面再无其他。
故里记得,刚刚那位叫隋淮的老人家,似乎提过,和她成亲的,是一个叫长安的老祖。
看着手里的牌位,故里知道,她应该就是和她手里的家伙结了个婚。
“你这家伙,人都死了,怎么就不知道安分点呢。人啊,阴阳之隔,天人永别,总归是不一样的。即使我嫁给了你,你摸不着,碰不着,有什么用?在说了,你的后代们这些行为是犯法的,若是我有机会逃出去,肯定会报警,端了你们这个老窝。”
说到最后,故里语气变得有些恶狠狠,不过配上她软糯的声音,怎么听都不像在威胁人。
而且,还是个什么都算不上的牌位。
故里将牌位原封不动的重新放回梳妆台上,又用红布将它盖住,然后走回了那张大床。
她现在最重要的事,就要要逃出去,也不知道爸妈有没有发现她不见了。
若是她睡了一觉,那也就是说这已经是第二天,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她明天就必须返回学校去。
虽然她家离青城大学不远,但为了实现自由,从大一开始,她就选择了住校。
而她消失了一夜,爸妈肯定也发现了她不见的事实,肯定会报警。
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了解现在这个地方,让门外那些人对自己卸下防备。
故里瞟了眼梳妆台上那被红布遮住的牌位,眼眸一转,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我的夫君啊!你死的好惨!”
隋淮刚走到故里的房门口,就听到里边传来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喊声。
刚才怕打扰到老祖,他特意将门外的人都遣走,可谁想却出了事。
脸色顿时一变,也顾不上尊卑之分,猛的将门推开。
他的突然闯入,让床边的人哭声有那么两秒的停顿,等看清来人,又继续哭了起来。
“我的夫君啊,你死的好惨啊!”
故里藏在广袖里的一只手,使劲的掐着自己的大腿,腿上一阵生疼,真让她挤了几滴眼泪出来。
隋淮有些紧张的看着哭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故里,眼中闪过惊慌。
“老,老祖,可是出了什么事?”他四处打量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地方有异常。
除了,老祖怀里多了一样东西。
这时其他隋家人也听到了动静,纷纷往故里的院子赶来。
“家主...”所有隋家人都站在门口,没有家主的命令,他们谁都不能踏进老祖的屋子。
隋淮抬眼,给领头的隋清比了个手势,示意他将人全部带下去。
隋清恭敬的领命,又带着乌泱泱的一群人快速离开的主院。
隋淮又将视线转向故里,眉眼间担忧之色尽显。
“老祖,可是晚辈哪里有做的不妥之处?”隋淮战战兢兢的问道,说完就准备跪下去。
故里见状,猛的往前几步,伸出一只手将他拉住。
“老人家,您可别再跪了,我怕折寿。”此时故里哪还顾得上哭,只觉得脑瓜子疼。
动不动的就跪,什么毛病?
被故里用了尊称,隋淮更加诚惶诚恐。
“老祖,使不得使不得。”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直接就跪了下去,还重重的磕了个响头。
故里:......
她不是为了让他们来看看她哭的有多伤心的吗,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那个...”故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隋淮见她语气停顿,眼中带着疑惑,顿时了然:“老祖,晚辈隋淮,叫我小淮就可。”
故里嘴角直抽,但也随了他的意。
“小淮啊,是这样的。昨天虽然是我和长安的新婚之夜,但我许多事情都有些记不清了,我现在想出去走走,不知道方不方便啊?”
隋淮闻言,瞟了眼她怀里抱着的牌位,顿时又低下了头,好似故里抱着的是洪水猛兽一般。
“老祖,恭请!”
故里神情一诧,没想到对方这么容易就答应了,那她刚才在那儿鬼哭狼嚎的起了个什么用?
“那,那麻烦小淮带路了。”故里扶了扶头上沉重的头饰,昂首挺胸的站着。
隋淮微弯着腰,恭敬的应了一声是。
因为他低着头,所以并没有发现故里眼中一闪而逝的得逞与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