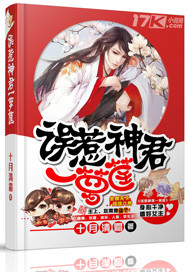“可不是,高董还是有远见的。”张娟补充了林妍的分析。
“老大他们这次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他也不说清,真让人着急。”明凡也不无担心地。
“还好是他在,要不员工得出事。”高一涵一说,几个人都点头称是。
“一涵,以后你怕是要拽着点他,老这样拼,早晚不得担心死人呀?”
“林妍姐,你就不要乌鸦嘴了,以后还能由着他,我高一涵就不姓高。公司不论谁出了事,我都不好交代。”这是高一涵的心里话,作为企业的法人她无疑是第一责任人,想象发生的这一切姑娘后背一直在发凉。一个为人们提供快乐、幸福、开心的项目,在它的背后经营者们需要如此的付出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但凡这其中出现一点不测,后续的影响不容人多项,没有哪项事业的成就能够轻松得来。
“好嘛,高大小姐你有担当,我们有你这个老板幸福啦!”这算是林妍说着冷幽默来缓和严肃的气氛。其实大家的心理谁不是揣着后怕和忧虑呢?
……
整整两天后,哑巴被安全地转运到了林场的医务室,安排了留院治疗,张自强几个轮流照顾病人。杨晨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他本来还想在地窨子里坚守,被林场的领导勒令一起回来了。时间已经是春节的大年初七的下午。
首先采取行动的是周松,两个男人之间的熊抱,大难之后的喜悦和兴奋。
高一涵和明凡,连张娟都兴高采烈地上去给杨晨最温暖最长久的拥抱,抱得他几乎都要摔倒,大家真的太高兴了,一次意外的险情终于还算完美地过去了。
林妍站在最后,楚楚动人地抽泣着,始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尔后她跑回自己的房间去消化复杂情绪去了。
这时的杨晨头发胡子更长了,多日来不洗澡、不打理,加上泥雪里的浸泡,寒风的洗礼,地窨子里烟火的烘焙,就像一个粗鄙不堪的老农,比之要饭的也没好到哪去。
这边他洗澡、换衣,收拾形骸,整理心情。那边高一涵招呼所有人,包饺子、做菜、打酒,几个姑娘还很有仪式感地都换了衣服,打扮了新妆,她们要在今天补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周松敲开了楼下小卖部的门,把老板所有的鞭炮和烟花都拿下,喜气洋洋地在楼下空地上排开,就等开饭。
不久张自强、二勇、小黄等几个人来到楼下的空地里,雪停了,风歇了,天晴了,漫天的星斗都亮了,人们的心情在鞭炮的炸响声中、在烟火迸发出的彩色烈焰里都张开了笑颜,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体验恬静的美丽。
所有人围坐于宿舍客厅里,斟满酒等着杨晨,全是殷切的眼神。
感慨万千的他用力地稳定着自己的情绪,不想慷慨悲歌,也不愿热情洋溢,他只是希望平静地对待过去几天的动地和惊天。生活里这样的事情对于寻常老百姓而言并不少见,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让现下成为歌功颂德的场景。
“今天,我们和高董一起可以过年了,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快乐,健康!”普通的毫无新意的祝福,人们听到的全是风轻云淡,预想中的情绪在他平静的脸庞上和话语里丝毫没有呈现。
看着所有人的沉默,杨晨又补充了一句,叫醒了迷茫的高一涵。“来吧,高董,您发话,我们走一个,开开心心过大年!”
这一桌人都酝酿着情绪调动着神经等着他满含激情的话语后一起高歌庆祝,没想到杨晨轻描淡写地把前几天的惊心动魄都掠过,直接把话语权交给了高一涵。
“老大,你是不是还没走出来,是不是现在还想着后怕呀?”高一涵不解地问他。
张自强他们终于知道了老板对上司的称呼是什么,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敬意。不过,一起经历的险情的他们才能彼此心意相通,杨晨不刻意地诉苦,其实是对所有经历者最大的尊重,生死考验后人们的心灵交流层面早已经不再是对苦难的纠结,生命不需要悲歌,它自行已然升华成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赖。
“没有,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就不要在纠结了。除了哑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也算把他们完整地交回给了公司。其实,我还是有些沉重的,没出大事是万幸。之后,我会检讨我的工作失误的,高董。”杨晨冷静得让人敬佩,甚至是叫人生畏,他是在以一种真正的责任感在面对发生的一切。只有热爱,热爱事业、热爱身边的团队和人,才会有的责任。
一群人陷入深思,的确在坝上创业太不容易,这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教训,作为一名成熟的职业人,一个项目的领头者,杨晨确实高兴不起来。他哪有资格沾沾自喜呢?他心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沉重地呀在那儿,只有把它搬走,才能抒怀。
“好的,老大,我们不说这些了。我来说个开场白吧。”高一涵放过了他。
“今天是我们迟到的大年夜,好酒不嫌晚。刚才老大说了他的祝福,我也祝福各位: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完事如意!我们就干吧!”
大家举杯同庆,相互致意,喝下了充满暖意的烈酒,杨晨在高一涵面前真心诚意地夸赞和表扬了一同值班的4个员工,一一把他们遇险时的表现向大家讲述、叙说,唯独没有提及自己,他在有意淡化这件事。
正月十五,到收假的日子,高一涵必须要回北京、回集团主持自己的日常工作了。
坝上的气候条件还是不适合经营,高一涵采纳了杨晨的意见放弃了对会所的值守,让张自强等人留守在了宿舍区,等哑巴出院。并要求他们也回家休整等待公司通知。
她看望了即将康复的哑巴,慰问了他的家属,她带着这几位高管先回到了承德。
高一涵、张娟和杨晨住进了紫御酒店,林妍他们各自回承德的宿舍休整。
下午时分,天光微亮,北风淅淅,阳光照在人身上一点暖意都没有。杨晨习惯性地来到武烈河边。河床上白花花冻结了的冰面,看不到水流的踪影,几只鸦雀在冰面上站立不动,期望日光温暖羽毛。他出神地看着它们,对岸河堤上缩着脖颈走过的人们拖着的长长身影掠过冰面,惊得小鸟一炸毛又懒懒地恢复原样。
“老大,你也在这?”高一涵清脆的声音。
“您也来了?”杨晨浅浅一笑,并没有过于惊喜的神情。“在屋里闷得心慌,出来透气。”
“一样。”还是很浅,看着武烈河的冰面。
“这次很惊险。”心有余悸,高一涵的浅叹。
“还行,都过去了。”他们又以最简短的方式开始交流,彼此都知道修饰语言不是对方要的交流方式。
“你有心事?”高一涵看出了他的情绪,悠悠地询问。
“您也有。”彼此心照不宣,都明白心里的沉重。
高一涵也远望对岸的人流。“嗯,感觉你有内容的样子。”
叹了一口气,肯定了她的猜测。“复杂的内容。”
“讲讲?”俏脸回转,专注地看着他。
“不冷吗?”杨晨看似不经意的问道,似乎想要把话题拉开。
“冷静,有利于接收信息。”她还是坚持要听,她需要知道他的心想。
杨晨详细地把坝上那几天自己看到、听到、想到的内容合盘告诉了高一涵。
“我有点热血上涌!”没有评论和分析,只是说出了情绪的变化,并没有说她很愤怒,但是这比愤怒还要严重。
“不出我所料,这些搁谁身上都不能冷静面对。”杨晨读懂了她。
接下来,两个人面无表情地开始彼此分析,在不需要试探和顾忌心里的波动,力争还原当下最根本的情绪。
“你想怎么办?”
“没想好。”
“有担忧?”
“林妍。”不是疑问,是肯定,两个人的担忧很一致。
“是,林妍姐恐应付不来。”
“您的想法?”
“我也没想好,担忧你。”
“?”偏头看看她严肃认真的双眼。
“担忧你下手的时候有顾虑。”
“有。”
“我爸?”
“不仅仅。怕出来的东西太多、太复杂,收拾不了。”
“凭你,我想可以。”
“凭我,可能真不行。”
“信心呢?”
“不是信心,是逃避。”
“你会逃避?”
“会。”
“哪有?”
“比如推荐林妍做总经理,就是一次逃避。”
“这个我可没想到。”
“这些终究是老板自己要面对的事。”
“我爸,也逃避了。”
“他会逃避?”
“事实如此。”
“这个,我也没想到。”
“要不,怎么是我来主持集团呢?”
“他的企业,他说了算?”
“不,有的事他说了不算。”
“比如?”
“比如交情和恩惠。”
“确实很难取舍。”
“但是,现在必须有所取舍。”
“怎么取舍?”
“老大,项目其实是你的,在某种层面。”
“你懂?”
“我懂。你也明白。从救出你们那天开始,你只字不提自己,我就懂了。”
“嗯。”
高一涵娓娓说出了她对于杨晨思虑的分析和理解。
“项目但凡有所闪失,你在这里存在的必要性都会消失,你都要离开。而且,如果你把英文斗趴下了,其他股东对你会很忌惮的。”
“没错。”
“所以,你逃避。想有更好的办法?” 高一涵本质上很懂得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