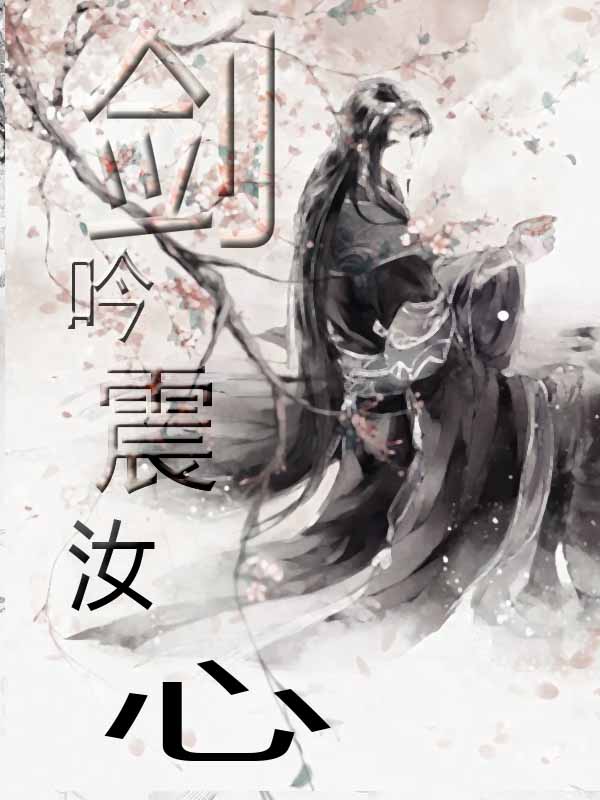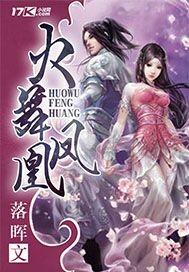公元一五九六年,明朝末年,旱灾各处频发,气候严寒,百姓苦不堪言。
可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严峻的初秋,婴儿的啼哭声出现在一户农家,也使这严峻的天气,有了那么的一丝丝人情味儿。
“是男孩儿、男孩儿呀!” 接生的阿婆笑着说道。
孩子母亲躺在接生床上早已疲惫不堪,衣衫也早已被汗水打湿,刚刚的这场硬仗已经快要把她的精力耗尽了。 可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也忘记了疲惫,轻声道:“是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阿婆走到女人身边,用襁褓把男婴盖好放在女人枕边,随机扭头去开门,对着门外那看起来不过年二十五六的汉子笑着说到:“还在这里愣着做甚,还不快进去看看你的妻儿,母子平安,母子平安呀!”
站在门外的男人听后喜出望外,随即朝着屋里奔去,也顾不得对阿婆道谢。女人看到男人进来后,轻轻唤了一声,男人却微笑着低声说道:“这一次,你受累了,谢谢娘子。” 女人听后摇摇头,只是笑了笑:“不打紧,让夫君操心了,” 然后又轻轻拍了拍襁褓里的婴孩,问道:“叫孩子什么好呢,夫君觉得叫什么好呢?” 男人听后说到:“是呀,叫什么好呢...都怪我,只想着科考功名,却到现在孩子的名字还没起好……”男人沉思片刻说到,“娘子觉得‘狄’字如何?试问老仙寿,铜狄几摩挲。” 女子只是轻轻笑了笑:“夫君觉得好,那就是好的,”然后低下头,看了看男婴,“希望等我们小狄长大了,可以快快乐乐的……”
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十年时光转瞬即逝。
男人却始终没有考出功名。白天帮忙上山砍柴,夜晚挑灯夜读却也从未放弃,只因十年前的他曾立誓,考取功名,衣锦还乡,报效国家。
女人也从未埋怨过自己的丈夫,因为她相信他一定会科举中的,更何况丈夫的所有举动,小狄也会看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狄也慢慢长大,跟着男人上山砍柴去城里卖柴,晚上有时也会学着男人,看着那些对他来说苦涩难懂的话。却总看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倒头大睡。男人也只是笑笑,随后便熄了蜡烛,把孩子抱到床上盖好被子,自己却会坐在床边好一阵子。
“入朝为官,可能我确实是没有机会了吧。”男人看了看小狄,又看了看窗外的月色,低头沉思。
“这样也好,能陪在妻儿身边,看着小狄慢慢长大,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瞧瞧孩子这手臂壮实的……最近陪我上山砍柴真的辛苦了……”男人微微笑了笑,“最近要再去城里面,看看谁家里需要些干柴,家里的粮食不太够了…”随后,便也宽衣睡下了。
公元一六零六年,由于旱灾严重,食物有限,遂衰败的蒙古突袭并深入辽东地区,烧杀掳掠,一时间民不聊生。
小狄和往常一样,跟随父亲上山砍柴后将柴禾卖到城里,路边遇到了小时候吃过的糖葫芦摊。便央求父亲:“爹爹,小狄想吃...”
男人闻声后回过头,弯下了腰,笑了笑说道:“我们家小狄想吃糖葫芦啦?那只可以吃一根哦,剩下的钱要带回去给你母亲的。”一边说着,一边从袖袋里掏出两文钱来。小狄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说道:“谢谢爹爹!”说着接过男人手里的铜板,蹦蹦跳跳地去跟摊主买了一根糖葫芦。
“最近那蒙古人不安分,趁咱们戍边漏洞,不停骚扰周边的村子,好多村子的人 都被杀了呢…”“是呀…真是可恶…”小摊旁边的茶铺传来的对话不小心被小狄的父亲听到,这让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给,爹爹先吃!”正在男子沉思时,小狄跑了回来,两只手举着糖葫芦,男人看到后只是揉了揉自己孩子的小脑袋,温柔的说道:“小狄吃吧,爹爹不爱吃这个呢。”说着拉起了小狄的一只手,“咱们快回家去吧,今天柴禾卖了不少钱呢,你母亲一定很高兴。”“嗯!”小狄一边吃着一边高兴的点头,仿佛这个世界此时此刻都不如手中的这只糖葫芦以及身边陪伴着自己的父亲。
父子二人回村的路上有说有笑。小狄有时候走累了,男子也不着急,只是让儿子坐下休息,而他却不知疲惫地讲着一些小故事缓解着一路上的辛劳。就这么的,父子二人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子口。
“哇,爹爹我们果然在太阳落山前回来啦!”小狄高兴道。
“是呀,爹怎么会骗你呢。饿坏了吧,走,咱们呀,赶紧回家让你娘煮你最爱吃的面条。”说着,便拉起小狄的手,大步朝着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