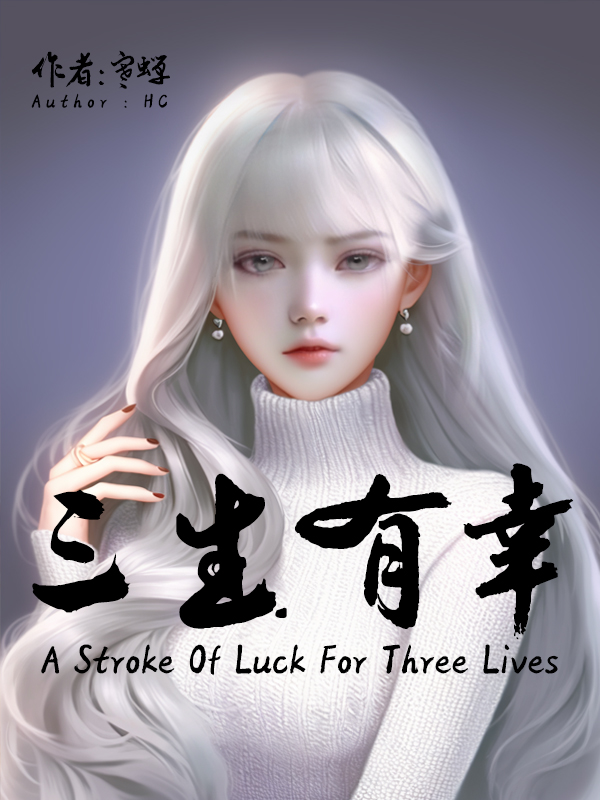“公主,侯爷在门外,说是有些话要跟公主讲。特令奴婢前来问您,此刻是否方便?”一名侍女快步走进房内,屈身行礼。
“请侯爷进房内详谈?”婉絮脱口而出,她了解的文卿做事向来谨慎,此时冒然打搅,定有要事找她商议。她甚至都不用思考,就已猜出对方的来意。
“诺!”那名侍女退出门外,将文卿请了进来。
“公主,萧某不请自来,扰了公主清净,还望公主海涵。”文卿对她彬彬有礼说道。
“侯爷,不必自谦,请坐。”婉絮方才已从榻上起身,见他走近语气谦和说道。
冬雪走上前去,将他带到房内茶案旁…
“公主无需拘礼,坐下说话即可。”文卿走到茶案旁跪坐在地上圆形的蒲团之上。
“侯爷,有话请讲!”婉絮由冬雪的搀扶之下才勉强在他对面的蒲团上跪着,只得硬撑着腰杆将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倒在膝盖之上。
“洨侯遇刺一案,凶手也查出……”文卿把那日黑衣人多交代的事,统统都跟她复述了一遍。
“如此说来,这一切都是王后跟吕产串通好,致我于死地!”婉絮虽也曾料想到王后会参与此中,但令她始料未及的事:她跟吕产居然合谋,一人为夺皇位,一人为了要她死。
“王后跟吕产一早便谋计暗害公主,幸而公主厚德多福,几次都从鬼门关绕了回来。”
“没想到王后为了让我死,尽已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是啊!她甚至允诺吕产以皇位换取公主的性命,看来…你们的这位王后与公主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恨呐!”
“即便她是南越的王后,匈奴的公主这两种身份加之,也难免她犯下此等滔天罪行!”
“太后已将洨侯府里上下全部拿下一一审问,只待人赃俱获,公主蒙受不白之冤不日便可洗脱嫌疑。”
“若真查找出证物,太后若是追究起来…南越岂不备受牵连。”
“是她王后干涉他国朝政,此事若只是她一人所为,太后则不会难为你的父王,更加不会究责于南越百姓。”
“婉絮听得传闻:你们大汉的太后可不似侯爷口中这般菩萨心肠,太后若想要谁死,随便加上个罪名即可…”
“侯爷,您请品茶。”站在她身后半天不曾说话
冬雪,听得她话中映射之意,赶忙接过侍女手中端来的茶水,放到文卿面前的茶案之上。
“公主,请用茶!“冬雪接着将一杯茶水放到婉絮这边。
“公主刚入长安城不久,怎知传闻是真是假…妄议太后…可是死罪!尤其在这宫中,小心隔墙有耳!”文卿端起案上的茶盏,放在鼻尖闻了闻茶香,轻抿一小口。
冬雪听了文卿的话后,顾不得身体上的伤痛,快步走到门外查看一番,有没有人在此偷听她们间的对话……
“侯爷是在教诲婉絮谨言,婉絮心领侯爷的善意提醒。”
“公主言重了,文卿岂敢教诲公主,只怕是公主心直口快,一个不小心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被有心之人听了去,有意传入太后耳中…公主岂不是惹来杀身之祸!”
“在你们大汉就连说错几句话都是死罪,看来…传闻中的太后并没有说错。”
“公主对太后心存敌意,是跟近来几日的遭遇有关,说两句怨言,发泄一下心中小情绪也罢!只是,出了这道门切莫再提及…”
“听闻侯爷素来冷面无霜,今日如此在意我的死活,婉絮在异国得侯爷照拂,真是感动于心!原来,侯爷也是心善之人。”
“公主说对了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至于照拂乃文卿份内该做之事。父亲还在府中卧床不起,普天之下,唯有公主一人能够医治。倘若,公主出了差池…父亲岂不…”文卿淡定说道。
“侯爷这般袒露真言,还真是心胸敞亮!婉絮多谢侯爷提醒,日后便不再言语论及她人,免得让侯爷忧心…”婉絮心里明白他这张气死人不偿命的嘴,一如从前令人生厌!
“文卿也听得传闻,公主乃聪明绝顶之人,定然知晓谨言慎行才能在宫中生存下去…”文卿再次将案上的茶盏端起,接着道:“茶凉了还可再续,人没了…”说话间放下手中的茶盏。
这时,冬雪走了进来对着婉絮摇了摇头,示意她外面有无人在此盗听她们之间谈话。
“你在门外候着…” 婉絮对她微微点了下头,小声说道。
“诺!”冬雪后退两步,转身走到门外…
“侯爷请放心,婉絮不会这么早让自己死的,也会尽毕生所学医治相国的病。”
“如此甚好!文卿现在此感谢公主仁心。”文卿起身,微微屈身,向她行礼。
“侯爷言过,婉絮在狱中幸得侯爷送药,伤痛才得以医治,否则伤到了根本,后果便就不好了…这么说来,婉絮还要感谢侯爷救伤之情!”
“文卿就用着这救伤之情,劳烦公主能为父亲续命,即便是数日也可。”
“侯爷莫急,待案情水落石出,婉絮自然就能回府。”
“唉…想我大汉泱泱大国,宫中太医,坊间名医无数,竟没有一人能够治得陛下跟父亲的病。如今,唯有公主能够让他二人醒来。”文卿一声叹息,重新跪坐到蒲团之上。
“侯爷不必恭维婉絮的医术,能不能够醒来,且要看他们的造化。”婉絮作为一名医者,第一回对此二人病情深感无奈。
“公主,侯爷太后身边的张总管来了。”这时冬雪走进来传话。
二人听罢,闭语,起身。
“侯爷,公主!太后请您二位过去。”张总管走进,屈身微笑道。
“张总管可知太后命我等前去,所为何事?”文卿在他身前小声问道,说话间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冬雪搀扶着婉絮,小步跟在他们身后。
“老奴只知是萧将军回宫,太后便命老奴请二位进宫。老奴先是去了廷尉后又去了您府上,都回是您二位被陛下请进了宫,老奴只好找到了这里。至于,这其余之事…老奴一概不知。”张总管低着头,边走边说道。
……
椒房殿,正殿之中,吕后端坐在她的凤椅之上。
侍女:蓁蓁,在她身侧站着。
“太后,末将等人在洨侯府中搜出竹简,绢帛等均为洨侯里通南越王后的罪证!”萧延在殿内站着,指着一旁随从手中举着的证物,大声说道。
“呈上,哀家倒要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是如何有着谋逆、篡位之心!”吕后气愤说道。
那名随从,听得太后之令,即刻走上前去,将手中证物双手呈上。
蓁蓁走上前去,伸手接过,呈到太后面前的奏案之上。
“他果真里通外国,意图篡位!”吕后阅见竹简上的书面内容,气得将手中的一卷竹简用力地朝前甩出…怒声喝道。
“太后!请息怒!”那甩出的竹简不偏不倚砸到了刚从外面走进的张总管额头之上,额头瞬间被砸破了皮,一道菱形伤口处有少许血液流出。他见到太后正在气头上,哪里还敢顾及疼痛,随手接过竹简,满脸堆笑道。
“你也不知道躲一下,下去敷些药吧。”吕后看着这位跟着他多年以来出生入死的老太监,动了点恻隐之心。
“太后,公主跟侯爷请到了。”张总管微笑道,说完尊太后命,小步退出门外,去处理伤口。
“微臣…”
“臣女…”
“叩见太后!”文卿跟婉絮走上前来跪地,叩首行礼。
“都起来吧…文卿,你来瞧瞧…吕产犯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吕后气的满脸涨红,身体微微颤抖。说话间,她转过头去,朝着身侧的蓁蓁使了个眼色。
蓁蓁走上前,将案上的竹简拿起,送到文卿面前。
文卿听闻,起身上前,接过蓁蓁手中的竹简,低下头览阅。
“小公主,你过来。”吕后对着婉絮轻声道。
“诺!”婉絮缓缓起身,走前两步。
“此次案件你们南越的王后参与其中,之前在你房内搜出的信鸽可是你用来给她传送信件之用?”吕后不紧不慢小声质问她。
“臣女饲养信鸽只是贪图口腹之欲,用此来打牙祭,并没用它给他人传送过信件。臣女跟王后多年不睦,南越王宫上下,人人皆知,请太后明察!”婉絮跪倒在地,低下头去,面对太后的质问,她没有惧怕,据理力争说道。
“太后,公主是被冤枉的!您别忘了,洨侯与南越王后合谋要杀的人原本就是公主,这个世上没有人会伙同他人合谋自己杀自己。”文卿览阅完竹简,将手中的竹简放回蓁蓁手中,大声分析道。
蓁蓁接过,将竹简重新放回太后面前的案上。
“如此说来,公主确实清白之人,是哀家冤了你。那又何故将那只鸟隐藏地那么深?”吕后还是有所疑虑,问她道。
“太后,许是公主居住的院落之前常年无人居住,流通气少,以致屋内阴暗潮湿。墙面掉落了一块,露出了缝隙,鸟儿自己钻进去出不来了也并无可能。”未等婉絮开口,文卿抢先说道。
婉絮跪在地上,头微微抬起看向文卿,文卿对她轻轻点了下头。此刻,她尽然再次对他心生感动之情。
“赵婉絮不能有这种情愫,他可是你仇人之子,你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他之所以会在太后面前帮你洗脱嫌疑,完全是为了不让你死,好回去给他父亲医病。”她下心中默念着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