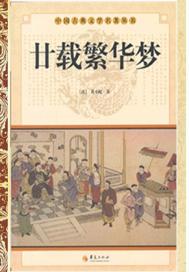‘抱月斋’在幽州城也算是知名的场所,在建筑风格普遍还比较古朴的时代,门口牌匾大大的金粉漆字,已是雕梁画栋,极尽奢华,酒楼有三层高,一二层接待普通人,三层则只对文人士子开放。
当婢女小荷一脸自豪,给对面小厮说出自己公子举子身份时,小厮的脸上,果然露出了满眼的羡慕之色,刘申不禁苦笑的摇了摇头。
不过,也难怪小厮如此了,时代是有特性的,如今的时代,身份等级对应着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和贱籍的划分,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早已经是根深蒂固。
满是牵挂,尚在求生的百姓,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话的,大家对身份看的很重。
虽然唐代比之后世来讲,还没有太过重农抑商,不过哪怕商人再有钱,他的社会地位也不如大地主,而那些坐拥良田万顷的地主,又不如朝堂里的官家,如此一级一级的划分。
刘申这个书生加举子的身份,在普通人眼中可就大大的不得了了,这还是在城内,如果在城外县镇里,这个举子的身份,就堪比那些县令主薄之类了,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有些读书人,哪怕到七老八十,胡子都白了,还未必能考得上这个举子。
什么是举子?可以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便是举子,举子分为两种,一种是都府长安里的高官子弟,一种便是其他州县的顶尖学子,由于地广又交通不便,所以唐时大部分的官员都是在首都产生,这也就有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区分。
中央官学也叫‘六学’,大抵是看家事招生,其中国子学,便是唐朝的最高学府,堪比北大或清华这种名校,而其他的学府,像什么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比之稍差,还有两所更像是专科学校,在这里学习的书生,身份便是举子,也叫做“生徒”。
地方官学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学习的,无论身份是百姓的儿子,还是官员的子侄,不过也有门槛,首先要上过私塾,能够读书识字,而后经过层层选拔,各种县级、州级的考试之后,冲出重围,才能拿到举子的身份,这类地方官学出身的举子,也叫做“乡贡”。
而其中的难度,自然不言而喻,取得了身份,就有对应身份的好处,大唐对于各个阶级的人,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像普通百姓,想要离开家乡,走亲访友,都需要当地官府开具的路引,只有过关盖章了,才能通行,不然就只能一亩三分地的在村里或城里待着。
而书生的身份就完全不需要这些,他们有权利佩戴宝剑,出门游历之时,沿途的官吏也不能阻拦,哪怕在公堂之上,举子都不必行跪拜礼,还得被青天大老爷赐座,更不用上来就挨几十大板。
这样的人,在普通人眼中,自然就是极有身份的了。
当然,乱世之下,人人皆是蝼蚁,刀斧加身,谁也不比谁高级。
刘申举子的身份虽然不可小视,但唐末还是首重武力,也许在普通百姓眼中身份高贵,但在那些以拳头说话的将军,以刀枪言语的绿林人士眼中,他也只不过是个弟弟而已。
之所以来抱月斋,是因为刘申接受了现今的身份,时间能够磨平一切,所以,刘申也尝试着开始接触社会了,说是‘社会’,大抵还是因为要把自己从个体之中,摆脱出去而已。
古人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是伦理及人际关系,大背景使然,很难做到现代社会的洒脱,当然,现代社会受到五千年历史的影响,做事也很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
个人在古代生活很难,因为交通关系,每个人活动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被五伦所影响着,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这些关系是交互的,每天都会发生。
人出生后与父母的关系形成,娶妻生子后就有了丈夫或妻子的身份,之后自己又成了父母,慢慢成为家族,这些人在一个大的国家内生活,就有君臣关系,与周边邻居或同事接触,同样有了朋友关系。
去判断一个人,首先就会从这几方面入手,比如刘申,刘申是谁?
这个名字说明不了什么,唯有从五伦入手,不是君就是臣,不是父就是子,不是兄就是弟,不是夫就是妻,不是朋就是友,除此之外,就没其他东西了,突然把五伦全部扔掉,这个人就是个体,但他该怎么生活呢?
西方有耶稣,他是个狼人,说过一些狠话,如若不憎恨父母,不憎恨兄弟姐妹,就不是我的门徒,而后耶稣用宗教的方式,把这些抛妻弃子的人,聚集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团体,他们抛弃了家族,成为团体中的个人,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答案是教友,是同一个宗教,同一个教派的朋友,他们没有五伦的交互,唯一的共同点,便是信仰上帝,服从同一套教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一旦团体瓦解崩塌,不再把信仰当成生命的意义,不再把团体的利益当成个人的利益,宗教的解体和衰弱,自然就会去寻找另一种原则来代替,近代社会,就是契约原则,理性的契约,这也是西方人重视契约精神的关键,都是一步步的历史性运动推动而来的。
儒学若是抛开统治层面的部分,其内在还是古人们归纳的一些人生感悟和道理,哲学的知识,许多东西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退一步讲,如今的儒学也并没有像宋明时代一般,过渡的本末倒置。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皱逢大变,从现代穿越到古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接受一切的,尤其他前世,并不是什么无父无母,无妻无子的孤家寡人、天煞孤星。
抛开亲人不说,古代与现代相比,也实在没什么可值得夸耀的,三妻四妾的男女关系,在现代同样遍地都是,所以,最近两个月来,掩藏在笑脸之下的刘申,是无边无际的孤寂,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思考着儒学,思考着生命,反正不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吗?所以这两月来,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去思考这些哲学的东西。
而无论是时间太短,还是因为终究经历太少,或者本身他就不是这块料,想了很长时间,终于还是也想不明白,自己如今为什么而活,只得将念头归结到,蝼蚁尚且偷生吧,自杀毕竟是一件很疼的事。
如此之后,思绪也就稍微通达了一些,开始逐渐适应了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父母和七七八八的家人。
凡事都需要讲究规矩,既然如今已经是‘刘申’,那就做好这个刘申,对于之前上过几次门来看望的朋友,也该时常的相交一番,对于古代的那些活动,也该时常的参与一下。
事实上,幽州城也的确是大府之城,地处北方,人口多少不知道,但少说要有十万之众,别看这人口比现代社会的四线城市还不如,但在唐末却也着实不少了。
安史之乱,黄巢之乱,自从百年前起,大唐的各个州府道郡,就在不停造反,灰败之色已重,天地将倾之势已不可逆,群雄割据之下,人口更是稀少。
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
战争破坏是惨烈的,唐末之后便是五代,堪比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
十万之众的幽州城,绝对是北方数一数二的大城了,公认的北方繁华之地,甚至比不远的军事要塞卢龙城还富庶,不说奢靡成风,也能算得上丰衣足食、富贵繁华了,这从公告板上说的各地惨状,而幽州城内却大部分人都有衣穿食吃,就能看的出来。
城内的各种青楼画舫成群,酒肆宴饮成风,蹴鞠的、打叶子牌的、冶游的、经商的络绎不绝,节庆之日,城内更可说是不夜之天,每日里都有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相传,也许,这便就是王朝更替的表现,各地起兵造反的原因,差距太大了,南辕北撤之中,满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味道。
所以刘申其实还是生在了好人家,好地点,如果扔到中原,一抬眼就是钢刀加身,敢不一起从军打仗,直接剁了当军粮,也许他就不会矫揉做作、无病**的思考什么生命的意义了,乱世之下,要么生,要么死,哪来的那么多想法。
酒楼三层是个整体的大包厢,楼上装饰典雅,而偌大的空间内,人却并不太多,大厅中央一条长长的案几,案几上摆放着毛笔、砚台、纸张等物。
一个身穿宽松白衣大袍的男子,正执笔泼墨,挥毫有神,旁边素衣绿裙的美貌女子红袖添香,为其研墨,几名同样身着华服的年轻书生,站在一旁微笑注视。
书香之气立显。
这时,“蹬蹬蹬”脚步声起,刘申带着婢女小荷到了楼上,其中一人见此,立刻微笑着迎了上去,拱手一揖,说道:“文遥兄,终于出山啦,殊为不易啊,伤势如今大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