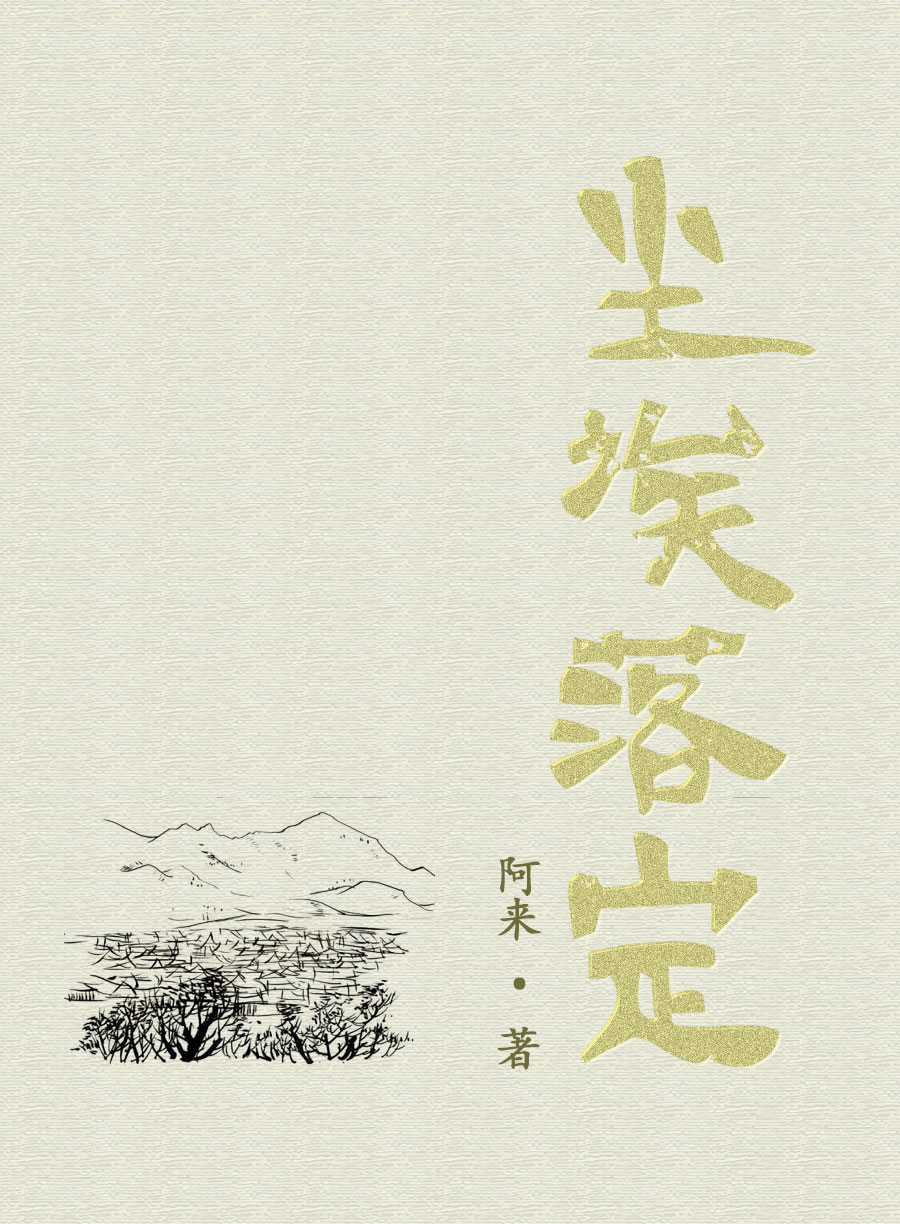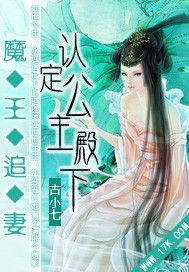史怀山看到启平、启家都睡着了,他起来从里到外都穿戴整齐、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胡须,把帽子弄的端端正正,觉得没有什么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了,他将那包砒霜拿出来倒在茶杯里,加上凉开水摇晃几下,仰头一饮而尽,回到床上躺下。
史启平和史启家早晨起来,看到爷爷还睡在床上,启家说:“今天爷爷怎么起得这么晚?”启平说:“昨晚喝酒了,别打扰他。”他们俩轻轻地穿好衣服出去了。
宋雨苑让起治把小米粥和七、八个煮鸡蛋送给昕儿后,她端着一碗粥和两个煮鸡蛋来到了史怀山的屋里,把饭放到桌子上,来到床前轻声叫到:“爹爹、起来吃饭了。”她连着叫了几次见史怀山一动不动,看到他戴着帽子睡在哪儿、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快步来到厨房对史镇石说:“爹爹怎么戴着帽子睡觉?我叫了几次他都没动静。”史镇石撂下筷子同妻子一起来到史怀山的屋子里,他看着史怀山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头上还戴着帽子,他走到床前,手在爹爹鼻前停了片刻、没有一丝气息,他用手摸了摸爹爹的手、觉得冰凉冰凉的,他放声大声哭了起来。宋雨苑呆呆的站在那里,说:“爹爹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呀!”史镇石说:“不是,看爹爹的样子好像是事先有了准备,不然怎么会戴着帽子呢?”孩子们听到动静都跑了过来,知道爷爷已经去世,都跪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史启治来到魏昕面前哭着告诉她:“爷爷去世了。”魏昕把孩子放到摇车里,要跟起治去看爷爷、起治对她说:“不行、生孩子没满月是不可以去的,不吉利!”魏昕说:“怎么回事?”起治道:“谁都没搞明白、等弄明白了我会告诉你的,你呆在屋里、不许去!”说完他哭着回到爷爷的房间。
李增学吃过早饭正往局里走着,来到史镇石门口,听到一片哭声从他家里传出,便来到史镇石家,当他来到哭喊着的人们面前、见到是史怀山去世了,对史镇石问道:“怎么回事?”说完跪下给史怀山磕了三个响头、嘴里说:“爹爹一路走好。”然后站起来对史镇石说:“爹爹什么时候去的?”史镇石说:“今天早晨发现的,大炮、你看看这个!在抽屉里发现的。”李增学拿起那份绝命书看了看,热泪流下、多年来自己与镇石情投意合、老人对自己痛爱有加、在老人的见证下、自己与镇石结拜为异性兄弟,自己常来史家、干爹身体一向康泰,看着手中的白纸黑字、内心道:“干爹这是舍其命而保全家也,高明!”他对史镇石说:“石弟弟、节哀,当下紧要之事是安规定去注销户籍、取得爹爹的死亡证明,我去货物处安排几个装卸工人,再派台车去宁城把爹爹的寿材拉来、明天不等天大亮就把老人發送出去,按爹爹的要求不大操大办,你意如何?”史镇石道:“一切按您的意思办,我这就去派出所。”李增学对史镇石说:“咱俩抓紧分头去办,对了、这个我拿着、放我办公室去,会有用的。”说完把史怀山的绝笔放到自己的兜里出去了。史镇石与宋雨苑商量的结果是:宁城的亲人一个都不告诉,只让启平去石河把他的姑姑和姑父找来。
汽车在缓缓的行驶着,穿着孝服的史镇石、吴青林、史启治、史启平、站在汽车车厢里史怀山灵柩旁、史启家坐在驾驶室里不时在向车外抛撒着纸钱,天快亮了、路上是被秋风刮满的金黄色的糖槭树树叶和史启家抛撒的纸钱混合在一起、在飞舞着,看不清那片是树叶、那片是纸钱、它们金黄黄地铺满了整个道路;当汽车驶离市区时,路旁的草是枯黄的、山色在朝阳的辉映下层林尽染,有暗黄色、金黄色、暗红色、鲜红色和苍绿色;汽车终于停在墓地,那些早已经到达墓地并在史杨氏墓室左边挖好墓穴的装卸工们将史怀山的棺木安放下去,随着史镇石第一锹土落入墓穴,哭声响起来!久久地响起来!那些装卸工们在窃窃私语: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棺材、这人一定不是一般人;听说是史处长的父亲,八十一了;这寿材最少有三、四十年了,那图案、那油漆漆得多好!、、、、、、
史慧娴从兜里掏出十张纸币对史镇石说:“这是二十块钱、十块给阿爸买烧纸,十块给昕儿下奶,我和你姐夫就回去了。”史镇石道:“姐、这钱就不用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史慧娴说:“这钱你一定要拿着、这是有讲究的!”说完拉过弟弟的手把钱放到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