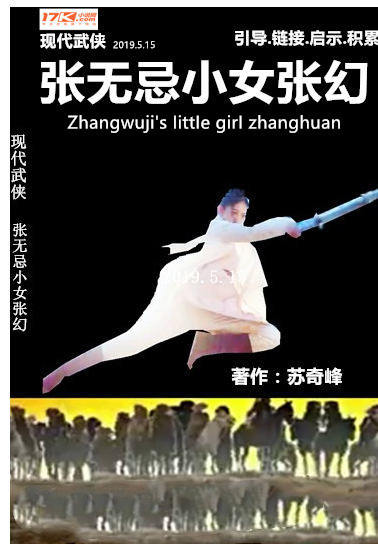我,木小春。从小到大,总是伴随着痛苦与喜悦。
出生时,恰逢政策少生优生,作为第二胎,怀孕的母亲天天躲藏官兵,周围几个省市都算是溜了一遍。
出生后,官兵人口普查,抓到了我家。他们砸了她们家祖传的一对儿青花瓷,那对儿青花瓷也就几百年的小年纪啊。祖上姥姥爷是这老地方的一名官人呢。
除了老旧发霉的床,还有发霉晒晒的几个大木箱子,其他都被带走了。 一同留下的,还有厅堂中几米长的大连柜子,通体实木上了紫色的漆。
可惜了那些带走的家具,全是父亲亲手做的。后来父亲再也没有做过木工,变成了平民打工仔。
要是有钱的人家,就尽数发了款,没钱的,便撬了家具衣物拖走,若是无钱无家具,才会叹气离去。
本就生养难得了,还要在生活上给民众再加一把火。等了我木小春二十来岁后,却是又来个生二胎三胎的操作来?当初建议只生一个的那位官员,早就生了好些孩子了。我小春才不会将我的孩子变为官员孩子的踏脚石,或者是说打工工具人。
从小就这被罚一事,就受了相亲不少指指点点。是的,我痛恨这样的,可惜要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我是施暴者嘛?不,我是受害者。
幼儿园开始,被嘲笑皮肤黑。大班作业被换,跟老师说,却只给一本破破烂烂的作业本。——那不是我的,我怒气冲冲地擦掉所有笔迹。于是,再也没有好好写字过。我不愿我认真的结果,只是换来个我捡别人的烂。那时那个“老师"还说,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名字呢?认真的么?那么小,除了aoe什么的,我会写字?
后来啊,一年级是留了一级的,因为爱玩。总算到了二年级,性子也成了沉闷的状态。
我拿了一块钱先给"老师"店员,买了五毛钱的水,后来想想大热天还是换成冰棍吧。结果用水换了冰棍,"老师"店员不给找钱,反说我偷东西,就告诉旁边我的亲戚,我大声告诉亲戚,我没有偷东西。可是没人信我,亲戚也指责,你是不是没给钱?我帮你给了。
回家后,到处是说我偷东西的传言。内心更深地封闭了一次。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呢?如果不相信我,我的澄清又有什么用?我不如不跟别人说话。
三年级,那些孩子们欺负班级一个胖胖的小孩,姓名加上外貌的肥胖。我看见他挣扎了,他说不喜欢这样子被叫。
也忘了什么时候的我,突然拦住了那群人,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欺负他了?不要那么叫他了?他不喜欢啊,为什么一直要让别人难过呢?
后来,我才发现,这种事情都是学校霸凌。
四年级,同桌一直同行的同村小伙伴,她听了她朋友的话,说:小春,你哭一个。
我莫名其妙,没有哭。
"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做朋友了。"她一脸认真又笑着说。我突然哭了,她笑指着我,对着朋友说:"你们看,我说她会哭出来吧?"
于是,我平生就没有再交过朋友,不喜欢开玩笑,也不喜欢被人伤害。
三年级订学校牛奶,丢了一个月的钱,没有喝牛奶,只能对老师说:我们家这个月不订了。四年级某天丢失了一百块,要知道,那个时候一百块已经很值钱了。父母有很少陪伴,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泡面,也是在那里吃了久了,才堪堪给赊账一次。
五年级,用粪勺舀河水浇菜,听一阵的声音,把大河里一条蛇给舀了上来。它卷着一个黑色的大青蛙,不是有癞子的蟾蜍。就叫了同村的孩子把蛇弄走,结果他们把蛇打死了,想取胆,可是胆都破了。
后来那只黑色的大青蛙就钻入我家的田地里,再也没看过。路与菜地中间那条小河里,曾经有一条黑色像蚯蚓的生物抬头看了我一眼,也不知道是不是盲蛇。为什么看我这个方向呢?
菜地附近的大草垛也出现过黄鼠狼,只不过窜的很快,比大橘猫还快,就一刹那的事情。喜欢那只大黑狗,喜欢那只三花狸猫。
看过大猫咪教小猫咪爬柿子树,给猫咪接生过。后来啊,我不在的那几年,猫咪死了。小学忘记几年级,大黑狗被偷走。
那只大黑狗曾经有一个孩子,结果前两天锅房被母亲打扫,没有稻草什么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冻死的小狗勾,还有大狗的呜咽声。我很喜欢她的乖,还有聪明,只不过没想到她早早离开。
初一成绩很好,初二下滑,初三成绩很稳定,只不过没去这个省里最好的学校。只去了父母建议的地方。
忘记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女孩被骗了去男宿舍,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喝酒烫头打架,花父亲的钱,大手大脚的。我惧怕那种气息,又顶着那份被霸凌的压力,才堪堪忍到毕业。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了,很多事情已经不记得,或者有事很难受,创伤很大,我的脑海会自动消除那些一段段不应该启齿的沉痛。
后来的事情,也不必再提了。我的回忆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