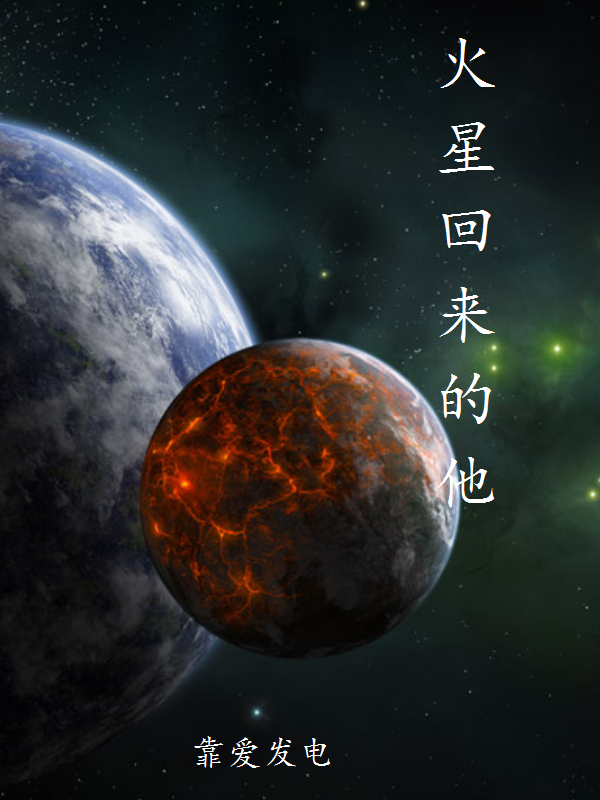当冬日的暖阳升起,照亮了大地万物,一切一如既往昨夜的那场大战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朝晖中两个人影缓缓走向陈留东门。
在离东门还有一里的地方,韩浩和曹真早已等候在此。看到人影向这边走来急忙下马迎接。
“先生,我与子丹恭候多时了。”
走来的两人赫然是去管亥营偷袭的萧一和典韦。曹真也跟着韩浩上前,“恭喜典将军,以两百骑兵杀散两万黄巾贼寇。”
典韦少有的谦虚了一下,“典某不敢居功,乃逸山奇谋,将士用命之功。”不过相对于典韦,萧一的脸色却不好了点,“子丹,我跟你说过多次,黄巾也是大汉子民。我且问你,敌军尸首可有好生掩埋?”
“这个……”
看到曹真回答不上,萧一的脸色越来越阴沉。韩浩急忙岔开话题,“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还望先生一解心中疑惑。”
“元嗣,有何疑惑但说无妨。”
“先生奇谋虽然当世少有,可为何那近两万黄巾却挡不住典兄区区数百骑兵?”
萧一就知道他会有此一问,“元嗣,觉得黄巾自起义时短却能席卷神州,是何缘故?”
“这个……末将还真不知道是何缘故。这群人前身多是贩夫走卒。军备也不齐整,有的甚至是拿着农具上阵,可昨日交锋韩浩发现他们的狠劲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士兵。也不知是不是那张角施了什么邪术?”
“张角的邪术只有两个字,信仰。”
“先生,信仰为何物?”
“这个嘛,信仰就是你所贯彻的,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就像武将阵亡,文臣死谏。皆是因为他们心中的信仰让他们不避生死,一往无前。”其实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当年的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干过侵略者的飞机大炮,无外乎也是信仰二字。
“照先生所说,黄巾军心怀信仰应该可以一挡十,为什么反而被典兄轻易杀退?”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信仰一物虽然强大可是一旦被击垮可就比瘟疫还要可怕。”萧一整理了一下思绪,“张角早起创立太平道,光收徒众四散传教,而张角的形象也越来越神化,黄巾众人多是被张角哄骗入教的,张角给了他们一个太平大道的画饼,而教众也把张角当成神来对待。可是当他们看到那座三日瓮城,看到子丹神来一箭时。心中自然就会想到城中有如张角一般的人,我借机说出要招幽冥鬼骑的鬼话让他们怀疑,谎言最可怕的不是内容,而是时间。我派兵扰敌并不是要拖住他们的攻城进度,而是要拖垮他们的精神。然后在他们最疲惫的时候,幽冥鬼骑出现。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就会把我和他们心目中的神张角相提并论,然后就会相信那真的是鬼神临凡。是问区区凡人有怎敢冒犯神威。”
在场的人听得似懂非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眼前这位大谈“信仰”的青年,把三万人的思想都玩弄于鼓掌间。
“先生,子丹不懂,我们既有瓮城,为何不依城固守,等黄巾粮尽而退。”曹真趁机发问。
萧一苦笑,“你以为我不想吗,一者如此行事死伤太大,二者我不曾想到那冻土铸城不能太高。所以那座瓮城只是个摆设,更甚者那瓮城一旦倒塌就会从守城工事瞬间变成攻城的阶梯。”
“不管如何,先生神机妙算。黄巾贼……军被我们烧了粮草又损兵折将,已无力再图陈留了。”
“唉,百姓所求至简,唯生存尔。”回忆昨日看到的战争的真面目,萧一有点不适,毕竟在现代这种场面可不多见。以后的世道只会更加混乱,百姓何罪呀?“子丹,你去把他们好好安葬吧。”
曹真自然知道萧一说的“他们”是谁。而萧一伤感的语气也感染了曹真,他对萧一拱手,“末将这就前往。”
曹真一人先走了,萧一三人继续前行。突然萧一对典韦道,“大哥,要不要跟小弟去洛阳看看。”
“好呀,但听贤弟安排。”
却说管亥带着一伙残兵败卒投奔了张宝营下,张宝原本要制他败军之罪。只因他正与皇甫嵩鏖战于颖川,破例留他帐前听用,以观后效。后来张宝及其兄张梁被官军所破,管亥又携败军逃往了北海。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光和六年末,天下大乱,天子降旨,改年号为中平,既是说除夕一过就是中平元年。
腊月上旬,萧一弃官,一行四人往洛阳而去。
“元嗣,你说你好好的副统领不作,跟着我干嘛?我和我大哥是回洛阳省亲的。”
“先生莫要诓我,省亲有必要辞官不作吗?再说了能跟随先生左右。区区统领之职算什么。”
萧一那个郁闷,自从自己在陈留说要走的时候韩浩就辞去了统领之位,给萧一当起了贴身侍卫。不过有一点韩浩确实没说错,萧一此行并不是省亲这么简单,黄巾之乱已起,接下来就是各地豪强崛起,宦官之乱,董卓弄权。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洛阳,萧一不是圣人但是也不想每日看到那夜陈留城外的情景。所以此次洛阳之行,萧一是下定决心要搅乱历史,推迟乱世的来临。此种做法用迷信的说法就是逆天而行,恐有灾祸。用萧一的说法就是插足权利圈,难免遭人妒恨,死无葬地。
见说不通韩浩,萧一就望向另一位“不速之客”,“子丹,你不是要去投奔你族叔吗?怎么也跟着来了?”
“先生这次你可冤枉我了,我族叔起兵讨伐黄巾去了,他捎来书信叫我到洛阳去等他。”
说来曹真一直都说起的这位族叔到底是何方人物?居然能让这小子如此听话。
“子丹,常听你提起族叔,不知他是怎样的人物?”
“说起我这个族叔可不简单。”曹真一脸的崇拜,“我族叔本姓夏侯,因其父过继于曹家所以才改姓为曹的。族叔年少之时就有权谋,多机变。记得族叔曾跟我说过,他幼时游荡无度,其叔尝怒之,言于其父。其父责备于他,他便心生一计,在见到他叔父时就诈倒在地,做中风之状。叔父看了大惊马上告诉其父,其父急忙来看,族叔却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其父问他,他回答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从此以后不管他叔父怎么说族叔的坏话,其父都不再信,你说我这位族叔有没有趣?当然这只是少年趣事。族叔他二十岁就被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族叔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就连汝南名士许劭都言我族叔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原本听曹真侃侃而谈,萧一就觉得耳熟,当听到这,萧一不禁脱口而出“曹操!”
“先生怎知我族叔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