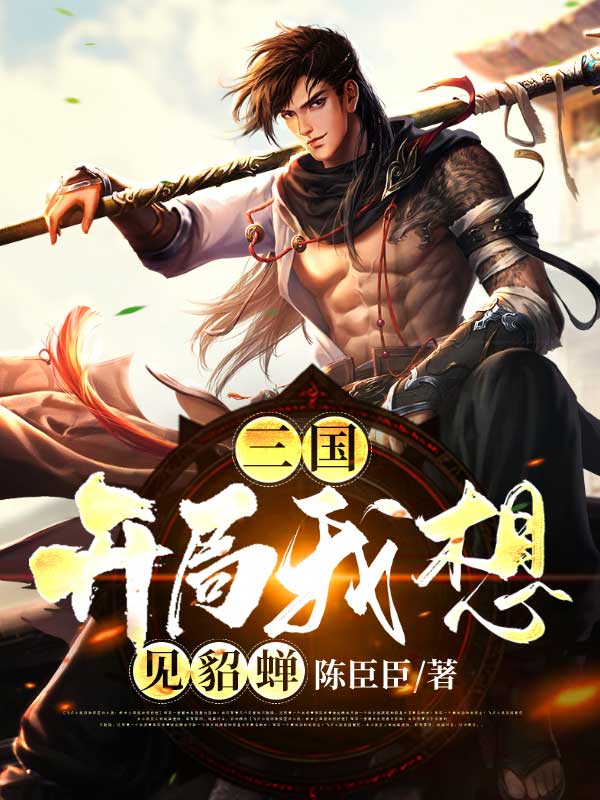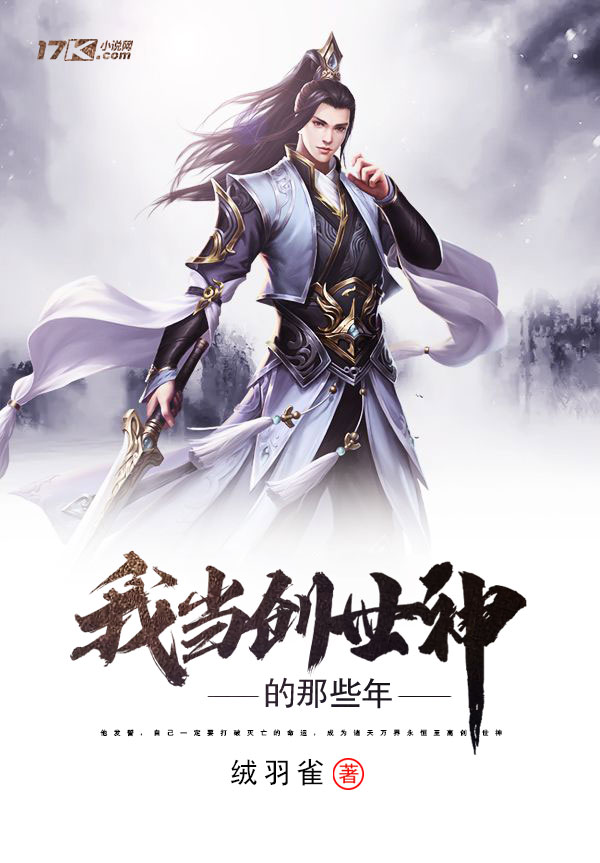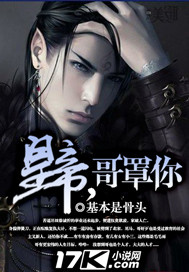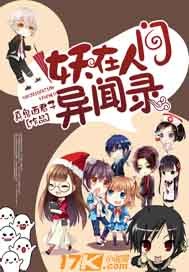烈日高悬,鹿台山山顶某处不知名的破败道观内,一位骨相清奇的墨衣少年,正在那座拴满红色绸带的古树树荫下,挥舞着手中的三尺青峰,嘴里念念有词,听着依稀像是吕祖曾与山野间偶然所作的那首剑歌绝句。阳光透过古树繁茂的枝叶化作丝丝温热的流光,覆映于寒气逼人的玉质剑身上,配上少年口中那貌似剑诀的豪迈诗句,倒是衬得这充斥着杀伐之意的剑舞平白多了些许中正平和之态。
少年不远处的宽大青石板上躺着一位“谪仙人”,仙人身着一袭修身的碧色丝质开襟衫,飘逸的长发以青玄木所制的玉色发簪束起,只留鬓角及额前些许微末的细碎发丝随着微风缓缓飘散浮动,修长挺拔的躯干不时透着一股不同于兰麝的木头香味,面容被盖在脸上的那本古籍遮掩不得而知,只能从裸露的额角看出他的皮肤很白,就像绝大部分的南宋文人一样。阳光透过树影,交错间宛若升起一层飘渺的微光。薄雾笼罩在仙人左右,为其披上了一层出尘且神秘的面纱。
偏偏就是这样一位能令世人为之疯魔的“谪仙人”,初时在少年的眼中却尤为可憎。当然这种憎恶情绪得以延伸下去的前提,便是这位仙人能就这么一直躺着,不露脸。少年不止一次见过这位仙人的容颜,可貌似每次所见的感觉均不相同。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你有幸得见他的真容时,你便再生不起任何负面情绪,就连嫉妒的念头都不会萌生。
一阵微风拂过,古籍翻卷着从仙人脸庞缓缓离去。露出了那张棱角分明的冷峻面容,雪白的肤色并没有让其呈现出丝毫病态,反倒是让俊朗的五官看起来份外鲜明,尤其是双唇,几乎像涂了胭脂般红润。相貌虽美,却不显丝毫女气;一双剑眉下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时而闪过一抹碧色更显灵动,嘴角时常漾着另人目眩的笑容。睡姿闲雅,尚余孤瘦雪霜之态,隐隐透着种不融世间的凉薄气,莫名的让人生出种不可触及的距离感。
少年对这位仙人的憎恶出奇的简单,不过是因为这位仙人太过凉薄罢了。凉薄到从昏迷中醒转后便再未开过口。
不曾与冒雨将昏迷的他背上山来的年迈老道道过谢,更不曾对悉心照料他的清瘦少年示过好。不知礼数,麻木呆板。在少年想来,这仙人啊,说到底不过空余华贵美貌的皮囊和浮于表象的虚弥气质罢了,真要说内里的人情味和礼数教养当真比不得自己这般有血有血有肉的凡胎俗体。
少年姓穆,名寒衣,老道云游时捡回来的弃婴。父母没给这孩子留下丝毫可以佐证其身份的印信或物件。所以究其是哪家哪户豪门望族老爷夫人不慎走失的掌中宝、还是乡野村妇泥腿子养不活的弃子幼童便端的是无人可知了。当然随同消失的还有少年的名姓。
穆是老道的姓,少年自然是随了老道的姓氏。至于寒衣这个名字,不过是老道捡到他的那天恰逢寒衣节罢了。并不出自于想象中那般极具美好寓意的诗赋词曲或典故传说。用老道的话来说,这就叫做缘。世间万般事,皆脱不出一个缘字。寒衣相遇是缘,定名寒衣亦是缘,命中注定,由不得凡俗之人去多做思量。
少年初时深以为意,觉得大抵便是这样了,毕竟出自自家师傅之口的,那便足以被称为是道理,道理那是需要牢牢记住并时时琢磨的。但后来随着光阴流转,几个春秋过后少年便知道老道那神神叨叨的呢喃到底有多唬人了,分明是他懒。恩,就是懒,虽然用这词形容传道授业的恩师不甚妥当,但少年属实是想不出比这更为含蓄典雅的词汇了。
可若真要论起来,老道比那每日瘫坐醉生梦死的仙人又要强上半分。少年便觉得,如此而言“懒”这个词汇,便可以摇身一变,坐稳俗世间最赞褒义词的这一王座。毕竟凡胎胜得过仙体的事,不常有,起码少年就很少听闻。如今这鲜活的案例摆在眼前,足以在道观的发展史上重重留下极具浓墨重彩的一抹笔调。
少年对那位谪仙人的憎恶并未持续太过漫长的年岁,个把月出头便忘得干净。此中虽有对仙人那袭经年不换却依旧纤尘不染的碧色开襟衫和久醉不见饮尽的青皮葫芦的喜爱、但想来更多不过是孩童心性,年少时谁能晓得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复杂情感。一时的喜乐憎怨也不过过眼烟云,埋不得心底,更别提萌生出什么执念枝芽。
少年后来总是把仙人唤作青,至于缘由吗。多是基于那年仙人的回应,说是回应吧也多少是有些牵强的。说到底不过是被少年称作仙人的男子拿起悬于腰间的环佩在少年眼前晃了晃。苍绿色的翡翠环佩上雕着一颗洋溢着荒古气息的参天老树。不知名的老树应当出自一位可被称为一代神匠的琢玉师之手。在那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环佩极高的翡翠质地承托下,老树宛若活了过来,鼎立于天地之间。
有诗赞曰:“滴露玲珑透彩光,宝器初成惊鬼神。绿翡得解弥翠色,古木百琢焕生机。”
环佩北角以云篆刻着一个“青”字。少年天真,多半是把这无意之举当成了回答,可惜的是仙人再没其它多余的琐碎动做,至于言谈更是如往昔一般无二。所以到现在少年也摸不透这“青”字到底是何含义,是仙人的名姓,还是另有所指。索性便就这般,青、青的叫着,这种并不怎么含蓄保守的称呼方式倒是显得颇具亲切,在这个极重谈吐教养的年岁,想来也只有关系极佳的相熟友人,才敢于去如此放肆的直呼这么一个不知是否属于对方的别称雅号。
翌日,许是让少年喋喋不休的自说自话给烦怕了,一向惜字如金,上山后从不开口的仙人破天荒似的问了少年一句:“想下山吗?”
正在院里劈柴的少年闻言惊愕的回过头来,一时间竟怔在原地,多少是有那么点不知所措。这倒并不是因为仙人难得的开口,而是仙人口中“下山”这个词汇对少年来说是真的没什么概念。
要说这鹿台山他也没少下过,毕竟人总是要生活的。修道也不是要修成什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邋遢还毫不知耻的山精野怪,山上现有的物品终归是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虽说观后不远处的药田旁倒是被老道划出了一大片区域,开荒后用于种一些平日里所食的蔬菜瓜果等,但用来填祭五脏府总归是不够的,充其量不过解馋罢了。更别说制衣的麻布,供给三餐的米面油粮,习符撰箓、抄写典籍的纸张,制香及修缮道观所用的原材料及工具等等。这些都需到山下的镇上采购。
每次需要采购的时候师傅总是会带上少年。一来呢修道这种事,不见见世面,经历下红尘的洗礼那绝对是不完美的,闭门造车,从不拿起,就谈不上勘破和放下。短时间来讲倒是无可厚非,但长此以往哪天不经意间经历点风风雨雨的,可能少年未经洗礼和凝练过的道心就很突兀的被污染或打碎了。二来呢,老道每次下山所采购的东西都很杂,量也很大,一个人多有不便,多个人就多个拎包打杂的,毕竟徒弟放在那也是放着,不用白不用吗。老话说得好,有事弟子服其劳。什么都自己干,那当时收徒是为个啥子?
说起这收徒呀,老道也不是没想过,他收这个徒弟是为了什么。要说是为了道观的传承吧,多多少少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的,但感觉这个因素吧,所占的份额并不显眼。要说是因为当时看到少年这弃婴动了恻隐之心,出于一种度人救难的崇高心理的话,又会感觉有些太过虚伪做作,思来想去怎么着都说不出个门道。
虽说老道最后还是找到了原因,但说出来的话多少是有些让人难以启齿,也有损自己这一代高道的伟岸形象,不得不承认,他当时收养这个孩子更多的目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有个人帮衬自己罢了,用大白话讲的话就是捡了个可培养塑造的免费劳动力。
虽然在教徒弟这方面老道没什么心得,但是在忽悠人和洗脑这块他还是很有一套的。所以一开始自家这小徒弟还真是他说什么就听什么。那时在少年心中老道的形象还是极其高大,怎么形容呢?那种感觉吧,也就和少年初识仙人时的状态一样。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感觉慢慢的就变味了。毕竟少年又不是一个傻子,哪里跌倒总要是从哪里爬起来的。任谁被同一个人以几近相同的手法坑上那么几次后,怎么也会促使诸如意识觉醒、奋起抗争之类的本能反应诞生。虽然少年从未奋起抗争过,但意识怎么着也是觉醒了的。
知晓此中因果后,少年对老道腹议斐然,心中的不忿多少是有的,可却也不曾说些或做些什么。救命之恩他无以为报,十几年的情感自做不得假,老道也就是嘴损了点,人懒了点,心吗,善的很。
言归正传,少年明显能感觉出谪仙人口中的“下山”和他所理解那个“下山”并非同一概念,所以少年挺希望谪仙人能够继续说下去的。毕竟这个话茬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开口问的话又显得自己忒没见识。
谪仙人明显没有看出少年惊愕神色下的那抹囧态,依旧温和的看向少年期待着他的答案。两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于是乎气氛就这么很自然的变得尴尬了起来,两人僵持了很久。
“怎么,没这个想法吗?你那个七年来杳无音信的师傅你就不想去见见?”仙人或是不想再把这个尴尬的氛围持续下去。
“不……想……吧……”少年这句回话明显有些颤动,语气亦不似往日那般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