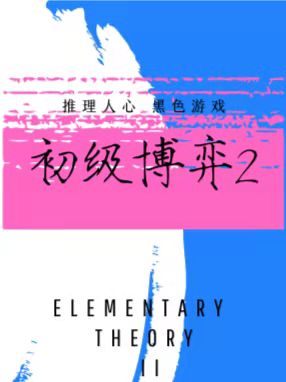时间拉回到1997年左右。
山西,黄土高原,窑洞山区,贫困农村(板桥),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母亲,家长里短,烟火,我短发 假小子,不俊,那年我应该是7岁,记忆中的样子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小,所以才无忧无虑,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烦恼所以觉得从前慢的节奏才是最美的时光。
冬天:厚棉裤,二哥,凌晨五点,学校老师生炉子,教室很呛,蜡烛,晨读,打盹,一直到七点,貌似我才真正的醒了,要回家吃早饭了,我还是个小孩子;三年级,五年级,每个同学或者说是乡亲的年纪,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即便不知道一眼就能看出来同学几岁了,并且不会错,一直以为这是我的特异功能;黑板上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用我认为很草书的字抄着董文华:春天的故事,毛阿敏:永远是朋友。还有静静的深夜,这是我能想起来的这三首歌一定是在我村学校学习的。都是拿着教鞭棍一个字一个字点出来的。结冰的河水,我含过我家路边下去那条河的冰,从没有觉得脏,能看见掰开冰窟窿下清澈的哗啦啦流着的河水,感觉生命很旺盛。跟着二哥的小伙伴玩的滑冰木头船玩,即便只有男孩我也不介意,不怕别人笑话我是女孩,介意女孩只能跟女孩玩,只能玩女孩玩的内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真的喜欢玩男生玩的内容,还是因为我的童年只能跟着二哥玩,还是我没有女生小伙伴,还是女生小伙伴都不喜欢我这样的。打我记事起我的心里就有了自卑感,标签:农村娃,不好看,性格大大咧咧。父母白手起家,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人脉。什么叫社会,唯一的烦恼就是不想学习,长成自卑的模样);雪很厚可以到我小腿那,很干净的雪,很冷的天,刺骨的寒冷,手是冻疮手,万紫千红,糖油油,是冬季必备保护手的东西,脸颊两侧红彤彤,摸着好像倒刺,不觉得苦因为我的世界里的小孩都是这样。杀猪宰羊血淋淋的场面,校长组织的去谁家谁家地里拾柴火,这个谁家谁家都是这个校长关系好的,貌似都是有钱的,去给人家顺便清理地里的杂物,反正干活的都是我们小孩子。新年:洗衣服,蒸枣味,擦玻璃,收拾柜子,除夕的一天总是我爸在写好多人家的对联,饺子,吵架。妈妈缝纫机做的新衣服,自己买的布料,橘红色的,自己纳的鞋底,灯芯绒布料的鞋面,穿着硬邦邦的,大了也穿小了也穿,冻也穿,一穿好几年,直到穿出破洞。压岁钱我妈给的好像是绿色的二块,后来变成五块,十块,二十,五十,直到上高中吧 才是一百。捡鞭炮,买零食,串门看大人打扑克。寇箱左边衣服里压着的酥糖,糖外边包着的黄纸上画着一个红色的小龙虾。水果糖晶莹剔透的。方便面贵的是六毛一袋,可以煮的有料包,酱包的那种,牌子忘了,反正不是白象的,料包那么咸,自己没事了老舔,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正月二十五,搭火把,就是用干酸枣树,连根拔起,用好几棵搭起来,点着,火势很大,家家院子里这天都是火火的样子,最后快烧完的时候也是最温度适合烤枣味的时候,那烤出来枣味,真好吃。(现在我们都用电饼档,或者烤箱直接代替)期待过年,感觉马路也是干净的,鞋底也是干净的,人们都是干净的,过了这几天就都回归到灰头土脸的日子了。
春天:柳灭灭,普通话我也不会说,(就是把柳树的柳条挑不粗不细的直溜的左右拧一下,使皮和柳干分开,那个柳皮就能抽出来,拿个小刀,削一下头头那个地方 就可以吹响了)那个声音像乐器,吹之前还要在嘴里打个响,感觉才能吹的更强更响。摘桃花,我家院子对面是一座山,名叫:簸荠疙瘩。我妈说因为长得像个簸荠,四四方方的像个梯形,又是个小山头 所以这么叫了,桃花都在这个梯形里开着,很多,面积很大的 ,一座山呢,我觉得很好看,每年都会跟着我二哥去摘,然后回来放津津乐瓶子里养着当一件家里的装饰品,还有马绒球,红色的穿起来像珊瑚,带在手上当手链。河里的冰融化了,两岸的硬邦邦的泥土也变成了稀泥,每次从河里上来的种田人都会把马路上踩的泥泥的。我的书包是斜挎的布包,妈妈做的,就跟解放军背的一样,只有一层,每次放学回家都勒出青筋,这个时候是上午十点会放学一次,回家了一般我妈不在家里,我都会翻墙,爬窗户,天窗,直接进入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类似于现在库房的窑洞,因为里面冷,干粮都在这边放着,主要是枣味(特别大的枣馒头)都干了,但是可能只有我们农村人知道这个东西是越干越香的越好吃,还有酸枣,去年秋天摘得,一大袋子,大部分都生了虫子了,但是家家都有,吃完后再去上学,如果来了卖糖葫芦的,我还没有二毛钱,就拿架子上的玉米棒子换,两个还是五个来就可以换一根糖葫芦,或者拿着啤酒瓶子都可以换,不用掏钱的,糖葫芦都快化了,也觉得不买就真的等到明年了,这个卖糖葫芦的人现在想想也可怜,我记得他都骑着二八大杠快出了我们村了,我们这些坏孩子还拿着石头扔,人家那个人停下自行车回头弱弱骂几句,灰溜溜的走了,孩子们懂什么,他们未必是想欺负那个人,只是觉得好玩罢了,但是那个中年男人却是为了家里的苦日子,是不是了回家的路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另外一个村的时候会抹眼泪:被一帮小孩赶出去……
夏天:西瓜,西红柿,黄瓜,唱戏,偷核桃,水果,香瓜,小卖部,柏油马路上摔一跤,上山采册猛(炒菜是放入一点,饭香到不行,可能只有我们这里才长这种神仙植物)每天中午午睡起来,妈妈都会让带一瓶开水,我们放的是白糖,或者橘子粉,瓶子是输液用的瓶子,和盖子,就连吸管都是用的输液管管或者圆珠笔用完油以后的空管管,现在想想真的是活的太久了,但是真的太解渴了,比现在冰镇的雪碧都好喝。每年六月十五,我们村都会请一台晋剧,供的是齐天大圣庙,男女老少都会看,人多热闹,小卖部买的东西都好吃,一毛一根的冰棍,二分一袋的聪明泉,水水酸梅粉,鸡皮,瓜子,等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那时候的最爱,没有钱哭着喊着要,不给了可以绝食,晚上十二点才散,好几个村的人步行来这里看戏,真的觉得是个节日。西瓜一买买好几个 放到床底下或者地窖里 ,吃的时候都是凉的,不吐籽,我记得我自己拿着籽种在我家房子后面,发了芽出了苗,都活了,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就不知道了,反正是突然地变平了,估计是我爸爸给铲平了。烈日炎炎,我妈喊我回家吃饭,边喊边骂:一吃饭就给老子跑!而我还在秋霞家里学着打扑克,料二子,手太小真的抓不了二副牌呀。对了,我家的猪仔,就喜欢睡在有太阳的地方,黑黑的,我会给她捉虱子,一点也不怕,我不嫌脏,靠着它的肉比沙发舒服多了!鸡窝,因为有三间窑洞,就有三个下蛋的鸡笼,村里大部分家里的钥匙都会藏在这里面,也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蛇,土颜色的,我家碗柜里钻进去过,河里我也会注意它的走位。村里人发现大一点的蛇,不会打死,直接放生,没毒,我也不会怕,现在也不会。蝎子,咬我的次数也是十来次了吧,那玩意我是真怕,没办法避免这些,只能默默忍受,所以从小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住到没有小虫子的平房里,我就满足了。
秋天:伴随着丰收的喜悦,家家背着呢绒袋收玉米,骡子拉着平车,全村人共用那么几个平车,总要把这些地里的庄稼收了。平车坐着慢,但舒服。再冷一点,就是点火堆,都是用谷子里分裂出来的碎碎的可以燃烧的东西,如果到处能闻到烟火气味,那就是最近几天都收完庄稼了,玉米也上架了,以点火堆的方式来结束秋收。那么更有意思的应该是在火堆里炒爆米花了吧,那个过**的很享受,咕咚咕咚冒泡泡就代表着要崩了,主要是真的香,比现在的市场上的都香。晚上睡觉前在烧的旺的部位埋入红薯,土豆,早上起来拿木棍搅开,别提有多好吃了!现在也奇怪,为啥那么多火堆,一晚上甚至好几天都不灭,也没有出现过火灾呢?人们也不见专门看着呀!地里拾柴火,跟着爸爸挑水,一趟一趟,也不嫌远,一年四季,如此反复。把收了的葵花杆落成一大片一大片,这样冬天就有烧的了,不会“受冻”了,没有暖气,我家也没有专门的炉子,唯一保暖的地方应该就是炕上妈妈的被窝。最痛苦莫过于树上的枣熟了,要收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捡爸爸从树上摇下来的枣,真的觉得好累,害怕砸到自己,一直抬头,脖子受不了,还不能偷懒,每年都愁……有一次,去别人家的田地里,他家的地的地势高,我乱跑到地里最最好的边缘地带,用我1.5的眼睛使劲望着所谓的大城市(县城)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构想,还是我真的看到了隐隐约约,高楼大厦在雾霾里伫立,还大声告诉忙碌的我妈,说城里真好。那时候以为,宇宙的尽头就在我们县城,没有国家概念,没有世界概念,以为长大了去了我们县城,就是完整的人生了……
我想以四季的方式可能会勾起回忆会多一点,先写冬天是因为现在就是冬天,也容易感同身受到过去,想到多少是多少,我会怕以后老一点的时候忘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所以我觉得应该找个方式来记录与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