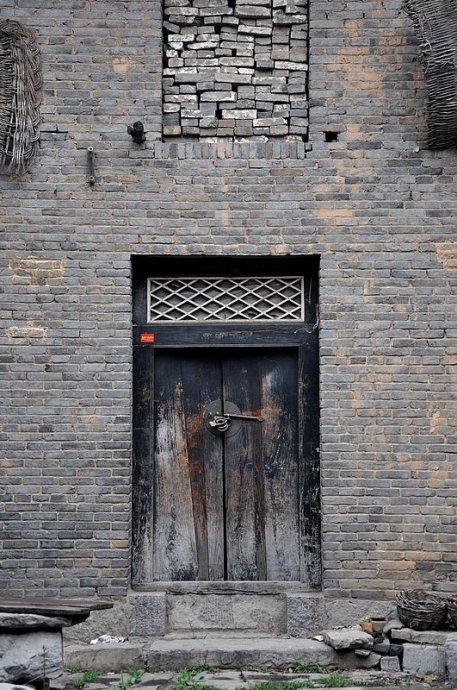“他居然敢不答应?”
胡床上的永嘉公主本该一如既往的慵懒妩媚,但是事实上她此刻的状况妩媚则有之,却与所谓之慵懒毫无关联。
她不是一只慵懒的惹人怜爱的猫儿,而是化身成一只龇开獠牙的小虎了。哪怕她龇牙发怒的样子依然很美,但下面跪着的赵管家却不敢欣赏,而是战战兢兢的跪在地上表现出了一脸的惶恐姿态。
赵管家道:“梨园令十分放肆,说若公主真喜欢洁牙行,他可以每年给公主三千贯的分红。”
永嘉公主听言勃然大怒,俏脸生寒时又咬牙切齿道:“她当本公主是乞儿了?三千贯够本公主打赏下人用吗?她若老老实实把洁牙行交出来尚好,不肯交出洁牙行,她还拿区区三千贯来羞辱我?羞辱我?”
她越说越怒,撩起裙子将案桌一脚踹翻。依兰人参熬成的汤也‘啪’的碎在了地上,冒着腾腾雾气。
下人们都吓的缩了缩脖子,晓得主子是真怒了。那赵管家立刻反应了过来,当先一脸狠劲儿的表态道:“公主放心,咱立刻叫人去对付他。”
他说的叫人,自然是叫宿卫了。
永嘉公主下嫁的是窦奉节,正是左卫将军,手中自然能调动一部分兵马。倘若永嘉公主下令,那自然可以让一班宿卫去郭府拿人。
想郭善不过一区区梨园令,哪里有手段反抗的了?而永嘉公主又很受皇上恩宠,又是皇上的妹妹,郭善断不敢反抗。假若反抗,那将他直接杖刑就是了。届时再说他背后非议公主,且淫乱公主的侍婢。皇上纵然知道他死的冤枉,也不会因为一个区区外人而降罪公主的。
这般想法只在转念间就形成,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想出这毒计,倒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用这种手段坑害过许多不听话的人了。
“杀他大可不必...我听说这厮很得我皇嫂的喜欢,我不想因为他得罪了皇嫂。先给他个教训,教他个乖。如果他还不自觉不懂事的话,到时候就算杀了他,皇嫂也无话可说。”永嘉公主不动怒了,阴沉着脸坐回。
赵管家忙不迭的点头,眉目一转后立刻领命去了。
... ...
“三千贯连一成的分红都拿不到,郭善,你欺人太甚了吧?”
朋来阁,杜荷目眦欲裂看着郭善。他一手撑着桌面,将半个身子前倾,企图用气势压倒郭善。但自始至终郭善也只是翘着二郎腿不屑的望着他,一副鄙视的样子。只听郭善不无戏谑冷笑:“三千贯能值几个钱?”
“三千贯足以我开一个不小的布庄,亦不知能活多少人命,你怎敢言少?”杜荷咬牙切齿道。
郭善不为所动,摇了摇头,讽刺说:“三千贯才够我喝多少酒?就是一顿酒钱也不够。”
杜荷听言大笑,道:“一升酒也不过二三十个钱,三千贯还不够你喝?”
郭善听言更不屑了:“你家喝酒只喝二三十钱一升的酒?你们杜府过的也够寒碜了。”
杜荷脸色一红,竟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他家确实不太富裕,当初他爹在世时李世民登基才不久。他爹当宰相不几年,也没收多少钱来。比不得长孙家那般如日中天...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家喝酒喝得也是岭南的灵溪酒、大食国、波斯进口的马郎酒和三勒浆。这些酒花费自然不小,三千贯买这些酒也不过几千升。这样算起来,三千贯的确不算多。至少在郭善眼里,三千贯确实不多。
但,杜荷手里头真没多少钱啊。他能凑出三千贯出来,完全是从他朋友那里拼凑的。府上每年也有给他钱用,但说到底也没多少零用钱。再加上他广交朋友,每日酒钱花销就不在少数,能凑出三千贯钱已经是不容易了。
“你晓得我郭善的本事,也晓得我郭善不是个缺钱的人。只拿区区三千贯,就想每年分走洁牙行十分之一的利润,我真不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郭善道:“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这三千贯给我,分十分之一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保证,这三千贯每年都将会两倍、三倍、四倍五倍的利润回报给你。可你也得想清楚,既然出了钱,那么往后洁牙行的产业的亏盈你也有了责任。洁牙行若越做越越大,你的钱将越来越多。若洁牙行有所亏损,你的钱自然也会受到亏损。”
杜荷不屑道:“这我自然知晓,不须你来跟我分说。”
郭善指了指桌上的协议,又道:“只要你摁了手印,往后每年自然有钱给你吃酒行乐。怎么样?杜二郎,这买卖做不做得?”
杜荷道:“三千贯放在我手里也总会花光,倒不如放在你手里,想来不会让我亏损。既然这样,那我还有什么疑虑?”
郭善听言笑道:“既然这般,你摁手印好了。”
杜荷不屑看着郭善道:“我杜二郎向来是说一不二,还需要摁什么手印?我谅你不敢反悔,这手印不摁也罢。”
郭善一阵无语,他知道杜荷是个很自以为是的,比房遗爱还自以为是的,但没想到这家伙自以为是到了这个地步。
郭善道:“你不怕我反悔,我可怕你反悔。这手印你必须摁,要不然往后你翻脸不认人我怎么办?”
杜荷见状,冷哼一声,锵的拔出剑来往拇指上一拉。剑刃划过,他的手瞬间血红。这家伙眉头也不皱一下,果断的在协议书上摁出一个模糊的指印来。郭善好一阵无语,等看见杜荷望向自己时,郭善才不紧不慢的从怀里拿出个匣子来。
在杜荷疑惑中,郭善打开匣子。拇指在印泥上按了按后,才在协议书上留下了红色的拇指印。
他可没杜荷那么‘英雄’,可不敢拿剑抹手指用血来当印泥用,郭善怕疼着呢。
揭起案桌上的纸,郭善吹干了手指印记,最后才小心翼翼的叠好揣入了怀里。呵呵笑了笑伸手道:“合作愉快。”
杜荷狐疑的伸出右手,被郭善右手握住。他大惊的撤回了手后,冲着郭善冷哼了一声,道:“事情已经谈妥,那我就不在此奉陪了。”
郭善道:“我家马车在下面等候,既然都是要走,干脆一起走好了。”
杜荷一犹豫,也没拒绝。他要往崇仁坊走,而郭善要去来庭坊。两个人虽然不是同一个坊里,但却同路。
郭善领着杜荷下了楼,上了马车。车夫扬鞭拍马,马车便疾驰上了道路。在春明门大街上奔驰一段路程,路过平康坊时却从斜刺里赶出几匹马来将他们的去路拦截。
为首骑马的是个青年,一身缎子,看起来也是富态人家。他身后跟着两个骑马的壮汉,膀大腰圆。而壮汉身后,则是一群泼皮。
车夫大怒,冲拦路的青年喝道:“你们干么?不知道我家老爷在车上么?”
那青年冷笑道:“是郭府的马车?”
车夫道:“那是当然。”
那青年听言冷笑,神情更是冷冽了。他猛然一抬手,冲着身后的泼皮们喊道:“兄弟们,姓郭的就在车子里。大伙儿拿着手里的家伙什儿,给我往里面狠狠的砸。”
话音一落,身后十来个泼皮立刻扬起手里的家伙。有擀面杖,还有石头片儿,瓦砾等,统统脱手朝着那马车里砸了去。
马车里的杜荷还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儿呢,一根棍子就‘砰’的打在了他的胸口处。他诶哟一声惨叫,黑着脸冲着郭善骂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郭善脸也绿了,既是愤怒又是茫然道:“到底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