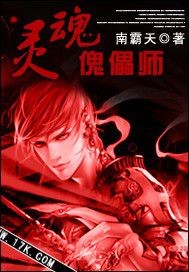92年的阿荔城最不乏的是暴力。
群架和单挑已是家常便饭般的事情,争斗的源泉也不会是什么真正的大事,有时只是因为一个摊位,一个肩膀的碰撞,或者是几句不合适的话。
如果说有人盼着流血与争斗,那么除了吃饱饭没事做的热血少年之外就只有胡寻了,因为他以此为职,阿荔城的人大多都知道他是靠这个吃饭的。
但胡寻不是土生土长的阿荔城人。
二十多年前,一个叫胡雪文的美丽女子穿着禾绿真丝旗袍拎着皮箱缓缓走近这座与她格格不入的城,住进城西的一所别院,而后开始半生岁月,直到年华逝去都没离开一步,她是胡寻的母亲。
来阿荔城的第一年她生下了胡寻,街坊邻居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只有沉默。
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一个野种。在那个年代,即使再可怜也是千夫所指。
亦有多少壮年男子蠢蠢欲动,但胡雪文只是看着软弱,实则富有智慧和傲骨,没有男人在她这讨到好处。当然早些年也是有过真心的人,并且毫不介意胡寻的存在,但胡雪文从未动摇,她就像裹着棉花的石头,拨开表层,内里坚硬无比,以为能够握在手里随意把玩,实则一遭不慎便会被砸个筋断骨折。
而胡寻,似乎自出生起,街坊邻居已经预见了这个孩子终会长成何种德行。后来不负众望的,他读完小学就有一群狐朋狗友,初一因为不守纪律而被退学,当时胡雪文打了他一顿,棒子打断了,他也不肯低头认错,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学。
休学后他常常出没在阿荔城最乱的英旗街,收过保护费,也老老实实做过小工,帮人追过债,当过混战群演。总之一路坎坎坷坷,不务正业,长到二十五岁的时候,背上已留两道疤,身边七八个小弟,裤兜里时刻有烟。
今天,胡寻被酒吧少爷裴若鸿叫来玩牌,十点半,玩了七把,站在吧台的“赌王”花哥一边擦高脚杯一边望过来。在裴若鸿让人再洗牌的时候胡寻却收起桌上的前,扬手止住,“今天算了吧。”
“什么意思?拿了钱就走?”裴若鸿把脚搭在桌上,嗤笑道。
胡寻耸耸肩,“我怕再玩下去花哥看不下去走过来替你,那我恐怕输得裤衩都不剩。”牌桌上讲究爽快,不以输赢论进退,也没有赢了就走的道理。但今天裴若鸿一把都没赢过,花哥站在那,看着毫无动容,实则关注着裴若鸿的牌况,半天就擦了一个杯子,若是胡寻再“欺负”他家少爷,那么把不准他走过来指点一二。
“那我们去外边玩几把。”裴若鸿起身,打算出去,花哥要看场子,不会跟上去的。胡寻却没有跟着站起来,反而将他扯回沙发里,“遇见什么糟心事了?”
别的他不敢说,打十点半,意志力集中很重要,平时裴若鸿也算会玩点心理战术,即使不能稳赢也能得个平手。今天却连输七把,再看花哥的眼神,估计是遇见什么头疼的事了。
“特么我办砸了件事。”裴若鸿拿出烟,抽了一根抛给胡寻,自己夹了一根,旁边的酒保马上凑近打开打火机,裴若鸿那边点燃又去胡寻那边。过了几分钟,裴若鸿吐出一串烟圈,浓黑的眉毛皱在一起,“卖汽车轮胎的柴哥柴镇凡知道吗?他有个龅牙妹妹,长得那叫一个报复社会,大家还都管她叫靓妹,因为有柴哥罩着嘛。结果前段时间有个二货当着柴哥的面喊她死龅牙,柴哥当时想动手的,可那二货也带人了,两个人就约了时间放了狠话。嘿,那二货也不是什么小混混,是武馆毅老大的亲侄子秦烁,不过毅老大什么人啊,讲道义的,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倒霉侄子主动犯的事,所以秦烁那二货从武馆拿不到人,也不敢回去和他老子讲,特么就来找我要人手,出手倒是挺大方的。可是兄弟我就因为这被害惨了!”
裴若鸿挑了挑烟头,继续说下去,“几天后程启均就来了,程启均知道吧?就是做中间人,他对我说有上家急用人,马上需要凑数,估计他上家挺肥的,他直接把钱全付了,我特么也是出门忘带脑子,看他着急,出钱爽利,什么都没问就借人给他了。结果你猜怎么找?去他娘的!程启均的上家是柴镇凡。”
“我靠!”胡寻惊讶道,“你手下的弟兄不会自相残杀吧?”
“残杀个鬼!我手下那些东西你还不知道?现在混战讲究的是人数,有实力的都自己带头去了,剩下一个个的都成了弱鸡,动个手都怕蹲牢。我带的也没好到哪去,平时拿的家伙都是棍子,还特么是木棍,更别提面对自己人,根本下不去手,特么站在那一动不动,柴哥和秦烁都懵逼了。”
想想那场面,胡寻忍不住低头笑出声,气得裴若鸿把桌子一拍,“我运气都背成这样了,你特么还笑,算什么兄弟。”
胡寻忍住笑,捻了烟头,双手搭在后面的沙发上,就这破事?他还以为是被谁追杀了,“等裴叔从陕西回来,再叫莲姨帮你吹几阵耳边风,摆平这事就一眨眼的时间。”
高悬的镂空三色玻璃灯一闪一闪,光束打在裴若鸿的脸上,照出一片桀骜面容,“算了,这事我特意让花哥帮我瞒着,别打电话告诉老头子。唉,要是早几年,这事抛给他也就算了,现在我都二十五了,还能做错事让自己老子给擦屁股?还是当着小弟的面被自己扇了个耳光,不把这事撂平我特么都没脸混下去。”
“那你打算怎么干?”胡寻问道,语气却很轻松,因为他知道裴若鸿肯定能摆平,即使他没有那个能力,即使他拒绝家里帮忙,但那又怎样?难道花哥会眼看着自家少爷泥足深陷?等事情闹大了自然还是会告诉裴叔。
“现在柴哥和秦烁让我在三天内给个说法,赔钱都不管用,他娘的,这事要被闹大了,谁还敢把事交给我办?”
烟雾缭绕,裴大少爷眉头深深的皱。
其实他的这件事对于胡寻来说不算是个事,换作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解决,柴镇凡和秦烁不见得会杀上门来,这本来就是一场乌龙,加上事情的根源也就是因为秦烁嘴贱,又不是什么图财害命的要紧事。至于面子问题嘛,只要裴叔不倒,他折的面子随时能够捡起来,也不会有人敢当面说他半个不是。
走在回家必经的公渡桥上,胡寻的蓝色条纹衬衫被灌满了风,一鼓一鼓的像是要把下摆从裤子里吹出来,他望向无际的江水,在余晖下慢慢变成一滩橙红,也不知道是要流到多远的地方去。
小时候他曾想过坐上一艘船,带着胡雪文离开阿荔城,永远离开这个破地方,从小他就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即使住一辈子也是外迁而来的异乡人。
可是他能去哪?二十多年来无论他怎么胡闹,胡雪文闭口不提那个人的事,他后来不再追问,但谁敢说他心里没有一丝渴望?人人都有父亲,可是他偏偏没有。
今天桥头的烧烤摊已经开了,有四个二十来岁的男人占了一桌,看样子已经喝了几瓶,酒嗝连连,其中一个人的公鸭嗓格外难听。
“这只能怪他自己背呗。”
旁边一个短黄毛问,“均哥,你不怕自己惹麻烦?”
“怕什么?是他自己问都不问就借人给我了,老子早就看不惯他那个鸟样,仗着自己摊上个好爹就上天了。”
程启均?胡寻脑子一转,侧着身放慢脚步。
“现在裴兆群去外地办事了,花哥管不了场外事,我看这事怎么解决。”程启均说道。
“裴若鸿身边还有一个胡寻,听说那小子从小混街...”
“啊那个野崽啊?早听说了,就是滑头了点,没什么大能耐,想踩就踩咯。”
其他几个人一起大笑,学着程启均的模样,脖子一扭,晃晃手中的酒瓶子,重复说道,“想踩就踩咯!哈哈哈!”
“不过他那个娘长得真不错,要是不是上了年纪,我还真手痒。”其中年龄最大的那人说道。
“哈哈哈,你个精虫,连大妈都不放过。”
蓝色的身影忽然一顿,胡寻垂在身侧的手攥成拳头,刘海下的眼睛皆是隐忍。他克制住自己,继续走回家,哪怕是心如刀割,他也要忍住,在这闹翻了天也就是砸了个烧烤摊,要还手,就得是狠手。
窝囊吗?他也有不窝囊的时候,十七岁那年他在桃花街帮一个妓女解围,得罪了一方老大,那人让他跪,他不跪,少年人,顶着一口宁死不屈的傲气无所畏惧。他打伤了一个人的手臂,也不算打伤,是那人的手臂被胡寻推的时候擦在木板上的钉子,划开一大道血痕,当场叫得像杀猪。
而胡寻,他背上被砍了两刀,刀刀见骨,可恨的是警察打的报告上说胡寻是先动手的,而对方是为自保而“不小心”在他背上划了两刀。为了这事,胡雪文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才把他捞出来。
那时他就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谁强谁有理,没钱有理也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