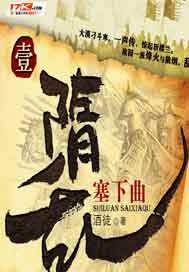小丫头拎着炭粉末一路小跑过来,气短吁吁道:“小姐,给。”
楚承安用指间沾了碳粉,在雪人的两道眉毛处一勾,退后几步看了看,频频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情。
“咦,怎么不像?”小丫头道出心中得疑惑。
承安随手捞起把雪,将手上的碳粉擦拭干净。然后揉搓成一团,朝着雪人的头掷去,面上的笑容渐深。
“不像什么?”承安朝着手哈了口气,脸蛋红嘟嘟的。
“一点也不像醉书画公子呀!”
承安扯起小丫头的羊角辫,警告道:“谁告诉我砌的是醉书画?”
“小姐,松手松手,好痛呀。”小丫头吃痛连连,吃惊道:“啊?难道真不是醉书画公子?”
小丫头一本正经看了看雪人,仔仔细细的观察。
身形不如公子飘逸,五官不如公子俊美,气质不如公子出众,这么比较起来确实不是公子,准确来说还不及公子神韵的十分之一。
不对啊,小姐干嘛放着神仙般的醉书画公子不堆,偏偏堆这么个傻大个呢?
放眼白沙洲,她就再也没见过比他更出色男子了,与小姐那更是天生一对,更是州长大人认可的准女婿、白沙洲的准姑爷。
这个雪人不是公子又是谁?看着怎么也不像州长大人啊,再说州长大人谁让年纪大了,那也是一等一的好相貌。
“小姐,你堆的难道是州长大人吗?”小丫头肥着胆问。可能小姐堆雪人不如作画,堆出来不像也是有可能的。
嗯,一定是这样的。
被她冷不丁的这么一问,承安才正视这个问题。
最开始只是好玩,随意堆个雪人,不知道怎么砌着砌着就成了钟直那个呆头呆脑的模样。特别是这两笔眉头简直是神来之笔,让这憨傻劲尽得了精髓。
“呆子。”她噘嘴轻哂道。
“小姐,你说我吗?”小丫头指着自己得鼻头道。心中暗自诽腹:难道又说错话了?
“什么?”承安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回神瞬间明白自己说了什么。
她心虚道:“这里除了我就去你,你说呢?”
“小姐,婢子愚笨,猜不出来,不如小姐明示吧。”
承安竖直扯起她的辫子,坏笑道:“还有你不知道的?”
小丫头戳着发麻的头皮,哭丧着脸道:“我想起来了,黄妈要我去厨房帮忙烧火,我得过去了。”
“去吧。”承安大发善心松了手。
小丫头看着小姐笑靥如花,心情大好。忐忑的心安稳了几分,以她的了解,小姐应该是不会秋后算账了。
楚问天与醉书画并肩走着,出了千机阁徜步到梨园就看到这一幕。
“小女生性顽劣,都是被我宠坏了。”楚问天宠溺的摇了摇头。
醉书画收回如水的目光,恭敬中带着两分笑意:“书画却觉得甚是活泼有趣。”
“梨园很大,让安儿陪你到处走走。”楚问天点了点头,对这个回答很是满意。
“楚世伯不一道去?”
“我还有些事务急需处理,就不陪你一道去了。你多走走,先熟悉下这边的地理环境。过几日得闲了带你认认门。”
醉书画心头骤跳,楚问天的言下之意他自然心领神会。
“谢世伯厚爱,书画定不辱命。”
醉书躬腰行礼,然后挺腰沉思道:“但凡有用得到书画的地方,世伯尽管开口。”
气氛有一刹的凝重,楚问天沉吟了会才道:“不足为惧,都已经解决了。”
“是否有后患?”
楚问天下意识地看了醉书画一眼。
这小子看似轻浮不羁,实则沉稳有余,分寸分明,果真后生可畏。能得逍遥子衣钵的关门弟子,又岂是无能之辈。
若将安儿交于他,他倒是安心不少。权衡之下,醉书画是最佳的人选。
“或许今日只是个开始。”楚问天手背在身后,目光看向白茫茫的天地。平静多年的白沙洲,还会一如既往的平静吗?
“世伯对背后之人可有头绪?”醉书画犹豫了一下,问道。
楚问天摇摇头,讳莫如深。“该来的总会来的,等等就知道了。”
“是!”
白沙洲的固若金汤,闲杂人等根本无法近身。不知道是谁的手这么长,伸到了白沙洲。当今天下能令楚州长忧心的必定非常人,前辈既然不说,自然是还不该他知道的时候,醉书画便退下朝梨园走去。
“嗖嗖嗖……”的破空之声由远及近,密集的雪球朝他面门袭来。
醉书画唇角一勾,露出一股淡淡地笑意。他云淡风轻的一偏头,旋即跃起,便是数个漂亮的回旋踢,生生令凌厉的雪球改道反扑。
好个醉书画,竟然来真的,也不看看在谁的地盘就敢这般嚣张,谁给的胆子。
承安骄喝一声,拔剑将雪球击个粉碎,冰渣四溅开来。
“啪啪啪……”清脆的鼓掌声响起,醉书画脸上的笑意漾开了。
承安轻哼一声,“白公子,大过年的不回逍遥谷,竟有闲情逸致来白沙洲?”
“我可记得某人说过欢迎我来白沙洲做客的,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醉书画用鞋面扫了扫地上的碎雪渣,意有所指。
“彼此彼此。”承安收回剑,抖了抖衣服上的雪花。
醉书画半点也不见生气,抬起袖子轻扫她肩头的雪花。
“你呀,还和小时候一样顽皮。”
承安缩颈,微微后倾。
醉书画刮了下她鼻头,“功夫见长许多,到不像小时候懒于练功。”
“哪里是懒,我只是没兴趣。”有兴趣的事情,她可一样也没落下。
“可不是,幸好没兴趣。不然刚刚那雪球非要了我的命去。”醉书画夸张的捂着胸口。
“那可不,我要是从小有兴趣,非要把你打成猪头,省得你去祸祸人家姑娘。”
“也好,打成猪头了。祸祸不了别人,就该你为我负责了。”醉书画将脸伸过来。
承安一手推开,“想得美。”
“唉!”醉书画苦大仇深道:“谁说我祸祸人家姑娘,你一个小姑娘都没被我祸祸,我反倒是被你祸祸了。”
承安气结,青天白日的被他信口雌黄,倒打一耙了。闻名玉烟河的白公子,还冤枉了不成。
醉书画这性子和小时候的一本正经完全不同,这是要经历了什么才能长偏的?
“我什么时候祸祸你了?”
“小时候。”
“小时候顶多是欺负你吧。”这点她承认。飞扬跋扈,蛮不讲理,特别是针对对他。
“是祸祸!”他强调。
“我怎么祸祸你了?”承安瞪大眼睛。
“你说过要我一辈子听你的话。还说过要我娶我。”
“我没有!”承安矢口否认,脸却心中心虚与无地自容而羞得通红。
“你有!”
好吧,确实有,还不止一次。而且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是打着要嫁给醉书画的幌子,去冠冕堂皇的退亲。
“那个……那个,年少不知事,稚儿戏言。”
“稚儿戏言。”她重复。
醉书画眼角微缩,拍了下她的头。“开个玩笑,你又认真了。”
承安当胸给了他一拳,“少没正形的,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玩。”
醉书画举起双手,挑眉道:“这次你说的欢迎我来你家做客不是戏言吧。”
“当然……不是!”
“那好,你陪我逛逛梨园,说说你父母的爱情故事。”
“小时候说过了。”
“我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