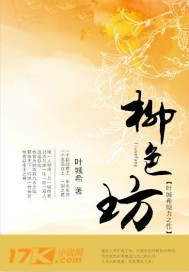八娘的表现果真与承安料想的一样,又哭又闹,嚷着说安姐姐说话不算数,骗人是小狗之类的云云。
承安因着理亏,是打不得骂不得,连句重话亦说不得,纵横这么多年头次阴沟里翻了船。
看着油盐不进的八娘,颇为头疼。不知道平时里爹爹看到刁蛮任性的她是不是也作这边感受,她现在倒是有点同情爹爹了。
嘴皮说干,好话堆了一箩筐也没用,承安只好另辟蹊径,转而对八娘委以重任。将“贵重”的一隅书苑的钥匙特别正重的交到八娘手中,并告诉她外人她一个信不过,只有交给她才能放心。
这一招果然凑效。
八娘立马噤了声,爬起来拍着自己的挺起的胸膛向她保证:“安姐姐你放心,你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保准不丢一砖一瓦。”
“好,我相信你,这里就全权交给你做主了。”承安暗暗偷笑,早知道一开始就应该使出杀手锏。
安抚好八娘承安这才动身。
今日风大,昨夜的霜还来不及化开,寒风中显得诺大的一隅书苑有些萧瑟沉寂。
承安出门系上大麾,戴上了兜帽。刚迈出大门,就看到一个小脑袋探头探脑再院门口转悠。
她一把拎住那个孩子的后襟,问道:“小鬼,这么快又有人找你送信?”
稚童头摇得像拨浪鼓,“非也非也。”
承安松开衣襟,隐隐有些失落,便不再问话。
见她要走,稚童拦住她道:“哎,我有名字的,我不叫小鬼。”
嗬!这小孩还挺较真,有点意思。
“小鬼!小鬼!小鬼!!!”她故意连唤几声,冲他扮鬼脸。
稚童不甘示弱,两手扯开嘴巴,露出漏风的牙齿,吐着舌头,回敬她:“咧咧咧。”
“真丑!”承安嫌弃道。
也许被人说了丑,稚童悻悻地放下插在口中的手指在衣摆上擦了擦。然后上下打量起承安,有了对比,确实无法反驳。
“姐姐这是要出远门?”
“嗯!”
稚童“哦”了一声,略有些失望道:“一隅书苑不营业了吗?”
“过了正月吧!”承安想了想,又道:“至少过了元宵吧!”
“年后我可以进来里面看书吗?”稚童一双眼睛油亮,问话时小心翼翼。
这小鬼挺会把握机会,懂得顺势而为。“我那儿缺个书童,每日里要打扫摆放书籍,管饭不管工钱……”
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稚童洪亮的回答:“我愿意。我还会研磨,端茶倒水。”
承安点了点头,这么说来好像是她赚到了。
“我叫张礼承。”稚童仰起稚气、皲红的脸。
“好,我记住了。”承安绕开他继续往前走,并未放在心上。
“上次让我送信的那个叔叔名叫钟直。”
风把稚童的声音送向后方,她却听得十分真切。与此同时,承安觉得心漏跳了一拍,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充盈心头,说喜不是喜,说忧不是忧,但她的嘴角是不自觉的上扬着。
她脚步顿了一会,转身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因为姐姐你答应了我来这里看书,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我理应告诉姐姐。”
这个回礼还真是……别出心裁。
“来一隅书苑看书是你求来的,你得偿心愿。而这个是你自己要告诉我的,不是我想问的。知道与不知道对我没有什么影响,那你说这来往是不是有点不对等呢?”
张礼承有点理亏,垂下了头,小声嘀咕道:“送信的叔叔说你是他很重要的人,我以为他对你也会很重要。”
很重要的人么!承安在他跟前停留了一会,重新迈开步子,走向已经泊在路边的马车。
她打了帘子,钻了进去。
“我爹呢?”
“洲长说他在船上等你。小姐,现在可以动身了吗?”
“走吧。”承安扬了下手,放下门帘。
马车缓缓使出,眼见要过了一隅书苑,她拂起窗帘,对着缩成一团黑点的张礼承喊道:“若是看到那个叔叔,就告诉他我回家了。”
张礼承好像听到了,跨着步子朝她跑来。这时马儿已经使上劲了,提速疾驰。承安看着那团黑点逐渐消失在视野,也不知道小鬼有没有听清她说的话。
行至码头,她先去向落英辞别。
落英和八娘都没亲人在旁,若是在船上过年,总觉得有点凄凉。承安便央求她过年去一隅书苑与八娘一道过,落英不但应承下来,还说她已经想好了,决定年前就搬去一隅书苑。
承安本以为落英还会要考虑很久,现在这样,再好不过,她可以放心了。
舵手用绞盘将铁锚从水里拉起来,随着开船号子喝起,扬帆起航了。
烟波浩渺,暮霭沉沉。承安立在船头,看向迎来送往的码头。
“小姐,州长叫你进去用膳。今日黄妈煮的都是小姐爱吃的,凉了就不好吃了。”
“再等会。”
黄妈顺着承安的视线看去,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没甚好看的。小姐是这在等什么呢。
“黄妈你站在这里煞风景,快进去。”承安一把将黄妈推走。
黄妈被推着踉跄前行,“别推别推,老身自己有腿,自个能走。”
顷刻,风夹着雪花洋洋洒洒的飘下。
承安抬起手心,接下一片鹅毛,看着雪花在掌心融化,暗自道:“呆子,你会来送别吗?”
“安娘,安娘。”这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再喊她。
她远眺,看见有个大傻个,沿着江岸奔跑,不时跳跃起来朝她打招呼。
“傻样!”她挪至一侧栏杆,隔水遥望。
钟直的速度奇快,想来功力见长不少,一盏茶的功夫已经缩短了不少距离。
“安娘,安娘!”钟直振臂高呼。
“你个大傻子大呆子。”她回以高声。
钟直听到了,咧开嘴,灿烂的笑容绽放在麦色的肌肤上,如同隆冬阴霾中的一缕暖阳。
看到他明朗的笑容,承安心情快活了不少。
“加速行进。”楚问天吩咐。
“爹爹,你出来干什么?”承安抱怨道。
“怎么,还不准爹爹出来了。”楚问天靠向栏杆。
“是爹爹自个说的,我可没说。”
洲长大人发话了,舵手们卯足了劲。过了一会,距离再次被拉开,越拉越大。
钟直依旧不舍不弃的更着船只一路上西,进入了江边的一排树中,隐隐看不见踪迹了。
“钟家这小子基本功底扎实,比钟询强不少。”与他预料的不同,这一点他倒是没想到。看着有点先祖遗风,似乎又是意料之中了。
“哼!”承安冷哼一声。
“宝贝女儿,爹爹哪儿得罪你了。”
“明知故问。”承安翻了个白眼。
“上哪去?”
“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