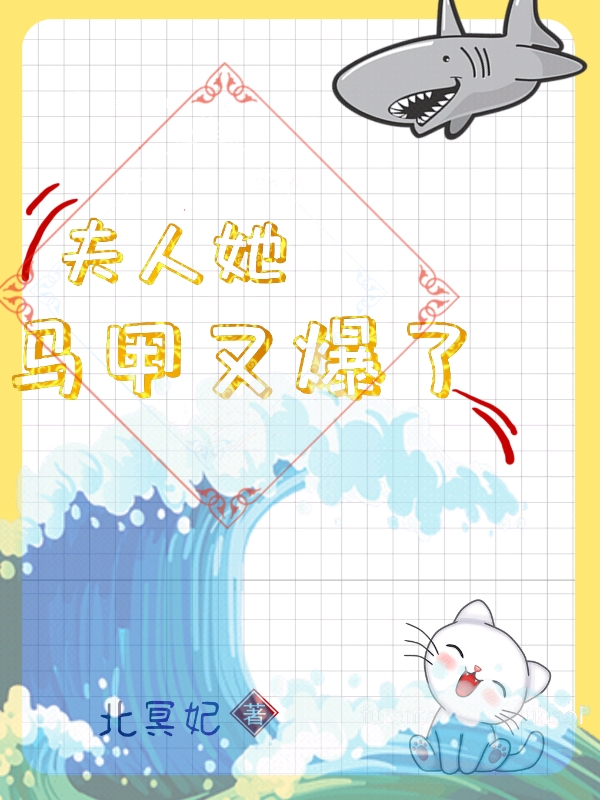钟直正愁如何回答之时,承安双手捧着脸,煞是认真的问:“呆子,你是跟着我来的吧!”
钟直被包子噎了一下,张着嘴点了点头,又拼命的摇了摇头。
“究竟是还是不是?”承安看到他那傻愣傻愣的样子,嘴上嫌弃,心中却涌着一股暖流。
“我……担心你。”钟直粗浓的眉头抬了下,迅速地看了承安一眼,然后眼帘垂下,盯着桌面解释道:“正巧络绎镖局接了入京的镖,我顺便看看你。之前应承过老伯要看着你,别让你闯祸。”
“老头儿瞎担心,你不用听他的。”承安语气有些生硬道。
“哦。”钟直诺诺的应了声。
气氛顿时清冷了些,两人干坐了一会。
过了会,承安率先开口问:“呆子,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要回河阳吗?”
钟直敛着粗眉,面色沉郁,似是想着一件很紧要的事情,下了很大决心似得。
“嗯,回河阳。”他正重的说道。
“衣锦还乡,子承父业,家里还有娇妻美妾等着,确实不错。”
钟直唇角扯动了一下,心中晦涩难言。吸了口气,半晌才道:“你呢?”
“兴许会回家吧!”承安双手交在脑后,往后仰了仰身子。
“你家在哪里?我可以去找你吗?”钟直话一出口便觉失言,补充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以后……还可以见面吗?”
“当然。”承安目光四处转了下,然后起身扯过多宝阁上放置的文房四宝,指着钟直研了墨。她铺开纸张,挥笔写上具体的地址,还就白沙洲的地理位置描画了简易的图形。
“看好了吗?”承安问。
钟直瞪着眼睛的看着,心中默默念着。
“看好了。”
承安点头,将纸张对折成纸条,点了火烛,在钟直的惊鄂中将纸烧掉了,她只道:“此处不能为外人道。”
“好,好定会烂在肚子里。”
…………
承安将白日里挑的一套靛青色衣裳与一封书信放在桌子上,系上面帘,拿起红玉宝剑与包袱推开了房门。
“钟直,再见!”她回望屋内,视线在笼罩在黑暗中的桌面停留了下,然后慢慢的阖上门。
朋友一场,她没什么可送的。她既不会做衣服也不会纳鞋子,白日里见他衣服破了,晃着晃着不知不觉晃到了裁缝店,看着这套好像适合钟直便买下了,也不知尺寸合适不合适。
她在夜色中行走,醉书画突然出现在回廊里,正迎面向她走来。
“怎么,准备不告而别吗?”他略带薄怒。
“怎么会,正准备去向你辞行。”承安面色坦荡道。
“哦,准备怎么向我告辞。”醉书画转身与她并肩走着,语气松软。
“口头告辞啊。”不然还咋告辞,这季节可没柳条可折。
“就这样?”醉书画挤了挤如画般眉眼。
“那你想如何?”承安笑道,“难不成你要为我准备饯行酒,为我送行。”
“这个可以有。”醉书画弹了下她额头,“你想去哪儿喝。”
“嗯,我想想。”突然她脑中闪过一个地名,脱口而出道:“去望江楼如何。”
醉书画面色一沉,“过了这么久还记仇呀?”
“这哪是记仇,是帮你找回场子。”
“言之有理。”
“这次我做东,你结账。”她扬了扬眉头道:“没钱就把你抵给望江楼,就你这皮囊能卖个好价钱。”
“行!只要你高兴。”
两人一拍即合来了望江楼,夜色已沉,望江楼内灯火通明,人客依旧鼎盛。
承安进来时目光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平叔,更别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樊子房了。
故地重游,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一切却又变了。
三三两两被沉下去的伤情,此刻又被搅混了,地下室中与易文清独处的一幕浮出水面,带起串串涟漪。终是要过心里的这道坎,就在这里画上终点吧,她暗暗下定决心。
他们挑了个雅间,承安照着上次的点的菜名一模一样的念出来。小二陪着诚意满满的道歉,这个时辰哪里还有正经用餐的人,都是行酒的人,饿了就点上几份宵夜下酒菜罢了。
“价钱好谈,你去问问你家掌柜的。”醉书画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
“二位客官可能不了解望江楼的规矩,过时不候,银子请收回。”小二不为所动,往回推了下银子。
醉书画看了看承安又看了看银子,淡笑道:“这地儿有那么点意思。”
“看我作甚,说说你请我吃啥吧。”承安道。
“送别怎么能少了酒。”醉书画对小二道:“两壶甘琼酒,随意上几个招牌的下酒菜吧。”
小二布巾麻溜地往肩头一甩,哈腰询问道:“好的。二位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望江楼号称京城第一酒楼,乐师没打烊吧。”
“这个有。”
不多时,小二领着一排侍女捧着餐盘鱼贯而入。一碟一碟的佳肴环了个圈的摆放在桌上,正是承安点的那些菜。
醉书画指关节扣了扣桌子,道:“有点看不懂这规矩啊。”
小二尬笑一声:“方才去后厨看到这些食材皆有,与厨师私下商量了下,都是养家糊口的人,公子懂我的意思吧。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不是。”
醉书画抿嘴无言。
“客官,这是我私下安排的,这钱……”小二拎拎指头。
“这个规矩我懂。”醉书画加了锭银子一起推了出去。
小二笑眯眯将银子收到袖子里,小声道:“还请二位客官为我保密。”
醉书画微微颔首。
这时小二双手击掌,帘后的丝竹声骤起,乐音缠绵哀怨。
“来,喝酒。”承安用嘴扒开瓶塞。
“空腹喝酒伤胃,你先垫点东西再喝。”
醉书画眉头皱起,长手去捞酒壶,却被承安一手抱壶躲开了,她伸出一根玉指呵了口气,“听!”
乐音正入主题,琴声儒雅,箫声哀怨。从前不知甘琼滋味,如今这乐响起,心怀伤情,千般滋味融入酒中入喉,方知其妙。
信天游前辈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再看醉书画他早就一声不吭的喝起来,也不知方才是谁说空腹伤胃的。
“干杯!”醉书画见她目光投来,如画般的眉目鲜活起来,举着酒壶强行与她相碰。
承安忆起上次发酒疯出丑,这次她不敢造次,只喝了几口便停下,微微醉意时再听此乐,潺潺乐音直入心底,描绘着她的心情。
好熟悉的感觉,有哪里不对,她一定是漏了什么东西了。
醉书画见她神情不对,问道:“你怎么了。”
帘幕中有人不小心碰到了蜡烛,黑了一下。里面有男声道了句:“毛手毛脚。”
顷刻蜡烛被重新点燃,丝竹之声再必响起。
承安拎着酒壶,一步步走至帘前,一把掀开门帘。
乐声顿停,抚琴的女子似是受了惊吓,怯怯的起身绕过琴,走至承安跟前福了福身。
承安点了点头当做回礼,视线始终落在男子身上,“樊楼主亲演奏,不胜荣幸。”
“姑娘,识得我?”樊子房诧异道。
承安自知失言,看了看他手中的竹萧,笑道:“只是在望江楼远远见过一回,听人提起过你的身份罢了。”
“这样啊,今日可是近距离见过一面了。”樊子房笑道:“鄙人平日里好丝竹之乐,偶有雅兴会充当乐师演凑之一二,姑娘可是觉得鄙人的演奏有不妥之处?”
承安摇了摇头,道:“甚好,并无不妥。”
“那为何……”樊子房欲再问。
承安往口中倒了口酒,拂开帘子往回走去。
“此曲可还要凑完?”
“不必了,退下吧。”醉书画挥挥手,替她回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