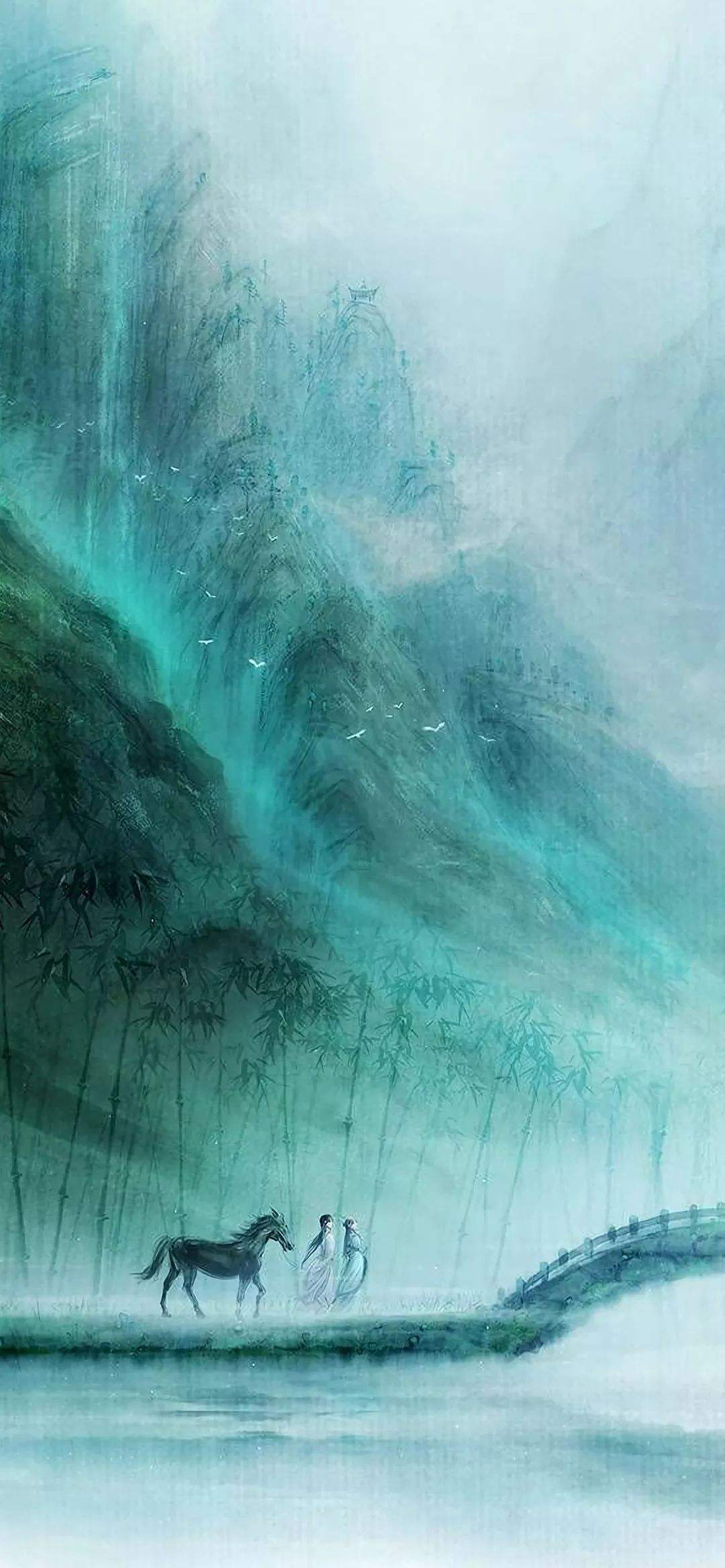承安不置可否,用扇骨敲打手中道:“好!”
“这把……”朱乔儿目光停顿在她的手上,余光打量着这位陋颜女子。
糟糕,承安暗自叹了口气,今天的她真够蠢的。
承安大大方方地打开缓缓打开扇子,凝眉道:“这把扇子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安娘姑娘的扇子好别致。”朱乔儿收回目光,“不知姑娘是否在秦州奉行街口的天云绣庄购买的?”
“这个嘛?”承安笑了笑,“我买东西图个兴致,店名从来不记,不过这扇子是我在京城购得的。”
朱乔儿“哦”了一声,没有太多表情。
只是这扇子的绣面与那天她见到的一模一样。寻常人看到只看花纹外貌,可真正的绣娘是从结构、局、绣法纹理、章程神韵上面去看的,以她之见这扇子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可眼前的安娘姑娘却说是在京城够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或许这位绣娘的绣品畅销到了京城吧,也可能真有人做到一模一样吧。
这位安娘与那日见到的女子天壤之别,怎么可能是一人,她真是多心。
承安笑着收回扇子,呆子的这位青梅竹马眼光毒辣,难保她细究下去发现破绽。
“经常听呆子……。”她刚脱口而出就看见朱乔儿皱眉,呵……这小娘子挺护短啊。“老听钟直念叨你,今日一见二位相配的很。”
朱乔儿闻言眉头舒展,笑意散开,含羞道:“安娘姑娘真会寻我打趣。”
钟直立在一旁插不上话,这话他从小时候听起,以前并没觉得什么不妥,好像原本就是这样的。可如今这话从安娘口出说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油然而生,胸口闷闷的,似乎还有些慌乱。
“谢老前辈的死因有眉目了,有眉目了。”有人奔跑高呼。
瞬间消息被传便每个角落,院内院外的脚步声动起来。
“走,我们瞧瞧去。”安娘率先走在前头,钟直朱乔儿跟在身后。
等他们到了议事大厅时,冰棺周围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三人刚找好位置站好,整个大厅就自己被围的水泄不通,外院都挤满了人。
里面主事的是谢一飞的嫡子谢崔旭。说来也奇怪,谢一飞身居高位,却没有把帮主位置传给自己人,据说是因为儿子不争气。
谢崔旭等人散开,这才看到原来在冰棺旁边还有一人,一个一身玄衣的女人。
那个女人缓缓脱下皮手套,侧耳在谢催旭耳旁说了什么,只见谢催旭脸色微变,神情凝重。
“怎么又请了仵作,这次竟然换了个娘们。真是对谢前辈大不敬啊!”
“女人怎么了,可别忘了冯家的女人当仵作是一等一的。”
“冯家与谢家结仇,断不会出现在此的。”
“你知道什么,这次验尸的可不是一般人。”
“怎么个不一般?”
“她是……”
承安认真的听着八卦,正到精彩处,谢催旭就控制住了场面。
谢催旭礼敬有佳的一番话的大意是已经查明了死因了,现在死者是大,当入土为安,谢家接下来要忙活丧失,备下薄酒款待远到而来各方英雄豪杰。
说是薄酒,其实异常丰盛。钟直她们三人坐在一桌。这桌不是随意坐的,而且承安特意挑的。
“刚刚你说穿玄衣的女人的女人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法?”有人小声问。
“这个女人就是冯家的女人。”
对方“咦”了一声,喝了口酒道:“这冯家与谢家怎么又往来了?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谢家的当家人换了。”
“难道是谢催旭有心与冯家重修旧好,化解夙愿。”
那人叹了口气,唏嘘道:“谢家本与冯家是胭亲,那谢家嫡子与冯家嫡女也早有婚约。谁成想这亲没结成,反倒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是何故?”旁边的人放下夹牛肉的筷子,继续问道。
那人看了看四周,又眼光扫了下同桌的几人。小声道:“这是一桩丑闻,在谢前辈过世的时节讲乃不妥。不妥啊!”
“也是,死者为大。”说罢,又重新拿起了筷子,大快朵颐起来。
“照我说也没什么妥不妥的,人啊,入土前就该了结生前的恩怨情仇,不带遗憾入土。”承安拿起酒壶主动替二位斟酒,“刚才谢大少只说查出了原因,也没公布结果,难道这也与冯谢两家的秘事有关。”
那人怔了下,只听承安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来,一起喝个畅快。”
那人戒备的看着承安。
承安笑道:“咳,其实外人都知道的秘事便称不上秘密了。你说不说,说不定私底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承安拍了拍钟直胸口道:“你看这是这次屠恶大会的屠恶英雄钟直。咱们都是江湖中古道热肠的人,绝无恶意,没准这个事情对追凶有用呢。”
“怪不得刚落座时我就觉得这位公子面善,原来是钟少俠,失敬失敬。”
那人赔礼率先自饮了一杯。
“使不得使不得,您比我年长,怎么能让您敬我。”钟直忙站起身,自罚三杯。
“折煞老夫了。”那人又了三杯。
承安见空杯就给他们添满,她就知道,对付这种满口仁礼仪的人此法最好使。
那人名叫刘浓渡,是谢家的远房表亲。另外一人是他半途结识的朋友,费道。
几杯酒下肚,刘浓渡脸色涨红,已有几分醉意。他想了想,这个姑娘说得也对,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今天验尸的那个人是酱霜夫人,我还是年少时来谢家做客远远见过两面。”
“醬霜夫人,那你怎么又说她是冯家人。”费道不解的问。
“醬霜夫人就是冯凝霜,冯家嫡长女。”刘浓渡以手淹嘴道:“醬霜夫人原本是谢家儿媳的准人选。”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婚事就此作罢,冯凝霜被逐出了家门,两家也不再来往了。”
“能将亲闺女赶出来的,想必真是丑闻了。”费道顿了顿道:“这个冯凝霜是不长脑子吗!”
“‘情’之一字误事呀。”刘浓渡感慨道:“当年冯凝霜恋上了他人,一心想与谢家解除婚约。当初的四大家中,安家为首,天青帮次之。冯家最末。两家本就是胭亲,几代交好,冯家看重这门亲事,怎能看着自己的女儿犯糊涂。”
“冯凝霜是个主意大的,竟然与她那心上人互通款曲,珠胎暗结。此等丑闻,冯家压制下去,不动声色的依旧筹备婚礼。直到结婚前夕冯凝霜逃出来向谢家说明原委,婚事此作罢,两家不再来往。”
“谢家大少爷痛失爱人,痛苦不能自拔,至今未婚,谢家就此怨上了冯家。”
“这等隐晦的事情你怎么如此清楚?”费道忙问。
“前面不是说过了,谢冯两家大婚。我们这种沾亲带故的亲戚早就到了谢家帮忙筹备。原本是冯凝霜与谢家父子的私谈,冯家为了掩丑,赶过来捉拿冯凝霜。冯凝霜性子烈,当场与父母大吵起来,动静闹得盖都盖不住。”
“就这样冯家与冯凝霜当下就断绝了关系,再后来就成了醬霜夫人了。”
“江湖不是传闻醬霜夫人孑然一身吗?放弃大好前途与父母闹翻,最后没与那心上人走到一起,不应该啊!”
“情爱的事情哪能说得清楚。”刘浓渡又饮了一杯,“我想那人定是负了她的深情。”
说完他就醉倒在桌上,嘴中喃喃念叨着“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