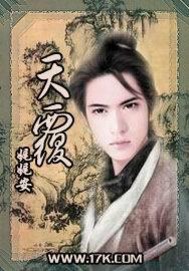这一战从子午时辰拖到卯时,天发亮之际白雪越发沉重,纷纷扬扬却掩盖不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任是阿史那厉尔一身虎胆英雄气,此刻都气喘如牛似那强弩之末,手中钺戟也变得沉甸甸没得力气提起。
自从被周沧斩了马前蹄,跌落了战阵,他就一直缠着徐真,双方相互纠结,你来我往,间中自有亲兵相护,虽伤不得大体,身上伤势却也越积越多,斗志却不曾落了半分!
徐真虽然年轻气盛,但得了李靖的《增演易经洗髓内功》,气息绵长活力浑厚,也不怯了厉尔的年富力壮。
甘州守军气势如虹,战线一路从城门推移到城外十里,沿途躺满了尸骨刀兵,马儿四处乱跑,却是那大雪都无法掩埋得住!
阿史那厉尔也是心中悲愤,多有英雄穷途末路的伤感,想那葛尔赫该是临阵丢了主帅,自顾亡命走了罢,午夜使唤亲兵去搬运救援,到得如今卯时天亮,这数里路就是横着滚,也该是滚到这厢来了。
眼看着二万兵马被徐真火炮一番扫荡,又遭那箭雨连弩一通乱射,折损了小半,猝然之下,又被甘州守军一番冲突,乱糟糟没个主心骨,又丢了数千首级,鏖战到得天亮,早已十不存一,眼下只剩苦哈哈的三四千人,兀自艰难支撑着不肯离去。
这些可都是厉尔的掌心肉,都是他一把手从草原最底层带起来的死士亲兵,战斗力绝非等闲,奈何如此长时间的消磨,却是经不住唐军的奋勇,折损了这好多人马,该是大局已定,厉尔却不愿就此狼狈逃难,心中一时犹豫,又被追剿了一段,数百条人命就这么被留了下来。
唐军这边也不好受,虽是乘胜之势,将士鼓舞,大快人心,然毕竟人数处于劣势,持久鏖战之下,慢慢也是颓然,连拿年近七十的老军神,此时都不顾劝阻,傲立于风雪之中,在后方擂鼓助威!
徐真用那长刀拄着,外头下着雪,红甲内里却出着汗,浑身乏力,手脚颤抖,不知还能支撑到哪一时刻,放眼望去,虽大雪纷飞,却遍地血红,如那炼狱现了人间,实教人心头发寒。
然一路走来,莫不是为了这一决战,若苦于微末艰难就轻易放弃,又岂是大丈夫所为,怎能积蓄雄壮军气?
念及此处,徐真那布满血丝的双目陡然亮了起来,如同注入了万千活力,见得一名啊柴嗷嗷着冲杀过来,他猛踢刀头,掀起雪泥,正泼洒在那敌人脸面之上,手起刀落,对面人头落地,骨碌碌滚了两圈半!
他只觉自己已经麻木不仁,可每次见得自己手下亡者,仍旧不忍直视,却又无可奈何,只盼着这一战尽早结束,好谋了三四斤军功,赏赐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回到长安继续混吃等死作罢。
只是周沧与谢安廷等一干狼虎儿郎却是兴致勃勃,闹腾了大半夜,却不见得困乏无力,手中兵刃早已豁口如锯齿,也不知砍断了多少脖颈骨,如今还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将这些个啊柴追杀了一路,简直落花流水,留得片甲却留不得头!
“罢了罢了!去去去!都与我逃了命去!”阿史那厉尔自不是那短气的英雄,然时势弄人,若非出了徐真这么个魔头,又如何让这八门挨千杀的火炮,葬送了好端端的战局,自古战事,时也,命也,既有那乱世出英雄,自然有那被杀的老汉。
阿史那厉尔虽然不愿承认了这事,然则事实确确实实如此,自己就是那无奈被淘汰的老汉了。
诸多亲兵早已丢了肝胆,听得主帅下了退兵的令,灰溜溜一路狂奔,连头也不敢回,生怕一扭头,眼睛里看到的只是一片刀剑的夺命寒芒。
又走得二里地,背靠了黑水河,诸人力气不济,却是想着迟早要被追死,不若置之死地而后生,哪怕死了,也要用那马革裹了尸身,也不枉戎马半生,活得痛不痛快自是另说,死时却要有头有脸堂堂正正了。
既心生死志,也就慢慢缓了下来,正欲与追兵拼命来着,黑水河那边却是人喊马嘶,蹄声隆隆敲了大地鼓,一彪人马林林总总说不得有三四千,浩浩荡荡就穿了风雪过来。
风急雪大,阿史那厉尔也看得不甚清晰,只觉得该是葛尔赫父子发泄良心,过来救援同袍了。
转念一想,战争最关键之时都不曾来看一眼,此时来该是收拾残局,坐收了渔翁好处,却是教人恨之入骨却又不得不心生期待。
若真叫这父子俩抓准了这时机,说不得久战了半夜的唐军会被反杀个干净,如此一来,功劳可就全落在慕容家父子俩手里头了!
然而现在连命都顾不上,阿史那厉尔又如何体谅这些个事情,连忙带着弟兄往黑水河下游转移,又被掩杀了一番,风雪凄凄惨惨,让人好不心酸。
徐真等一干唐军追得远了些,也不太安心,见得风雪之中刀枪旗帜林立四野,心里头也是发了慌,同样放慢了脚步子,集结了阵型,做了个防御的姿态,缓缓往前推进。
若说卖力拼命,周沧等几个弟兄自然不怯任何人,连张久年这等谋臣,都杀得满身满脸是血,但若说道推敲占据变化,又有谁人敢在李靖面前称大?
虽在后方擂鼓激励,然老军神时刻不在关注着战场局势之变化,此时异军突起,由不得心声警兆,然细细想了一番,却抓住了些许苗头来,当即下令道:“都冲杀上去,莫走脱半个贼虏!”
诸多弟兄还在担忧对岸是敌是友,主将却是下了死命,诸将士又岂敢不卖命追击?当即抖擞了精神,将地上的敌人尸首踢开,扒了一口干净白雪,草草塞入嘴中解了饥*渴,又不要命地往前冲杀!
徐真也不明白李靖何以如此,所谓穷寇莫追,自是有着天大的道理,阿史那厉尔的残部已然没了威胁,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就不怕狗急跳墙,多葬送了弟兄们的性命?
然而张久年却是冷静了下来,思前想后,不得不将老军神的底气,放在了契苾何力的身上!
想起契苾何力的援军,诸人也是精神振奋,主帅如此决绝,想来也是寄托了殷切切的希望,只好硬着头皮赌他*娘的一把!
“嗨!”
徐真闷哼一声,拔起百斤重的步子,跟着人潮往前走,却已然听得前面喊杀震天!
这番生力军气势惊天动地,为这死气沉沉的战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说不得又要白流鲜血染了黑水河。
只是双方都在赌,这援军到底是慕容寒竹与葛尔赫的狼骑,还是契苾何力的大军。
不过听得这喊杀声与沉闷的死前哀嚎,军中袍泽都振奋起来,因为喊杀声乃大唐言语,而非贼虏腔调,虽晚则晚矣,然契苾何力的援军,终究还是来到了!
阿史那厉尔仰天长叹,自谓回天乏术,只好接过亲兵递过的缰绳,跨上一匹大马,带着不足一千的残兵,往祁连山方向逃亡。
此时天寒地冻,他们身上又有诸多伤势,随身又无粮食,入了祁连山,跟自寻短见有何区别?
契苾何力也是个明白人,掩杀了一番之后,也就勒住了队伍,与李靖相见之后,各自描述战况,契苾何力却是遮遮掩掩,不太爽利。
此战之所以能大获全胜,皆赖徐真神火营那八门神火炮之威,李靖也不避嫌避讳,加上契苾何力与徐真又相熟,故而命人沿途打扫,自己人却是扎下了临时中帐,一干将领于中庆功议事。
李靖不敢坐,自然无人敢坐,待得李靖坐下了,仍旧无人敢坐,目光却都投在徐真的身上。
若无徐真,他们连屁股都保不住,徐真占了这首功,何人还敢小觑?
徐真也不是那糊涂人儿,自然不敢开口,待得谋士刘树艺诚意相邀,他才卖了个乖巧,让薛万彻和契苾何力先入了座,又是一番礼貌谦让,这才坐了下来。
契苾何力不是那弯弯曲曲的人,直来直往,见得徐真如此扭捏作态,也是打趣老军神道:“这小贼子本是个豪爽英雄,怎地到了卫公麾下几日,就养了一身婆娘气息。”
恶战大胜,大家又知晓契苾何力脾气,不由哄堂大笑,憋屈了两个月的闷气,总算是得以舒缓发泄出来,此番论功行赏,说不得又要转了勋策,提拔了官职也。
然而徐真心头却仍旧是不安,总觉着少了些许关键之事,下意识摸了摸手指,触碰到那铁扳指的冰凉,才恍然醒悟过来,如那冰水兜头泼下,瞬间冷到了脚趾头,慌忙问那契苾何力:“敢问领军将军,可曾将...将我那妹子也随军带了来?”
徐真心急,差点就将李明达的身世给说道出来,好险转了口,只道是自家妹子,诸人也是有些疑惑。
这契苾何力却不明所以,愣了愣神,这才点头道:“令妹与祆教老宗师都跟了过来,某已经着人保护在后方,想来半个时辰之内,就能够赶来了。”
徐真闻言,如那五雷轰顶,也顾不得礼仪,冲出帐篷去,放了命大喊着:“能动的弟兄,全部都跟我来!”
他本只是都尉,操控着自家本部神火营,不敢僭越呼喝其他诸营弟兄,然事关紧急,其又在此战中赚下了大片大片的好声望,故而一呼百应,果真是能动的都跟了上来!
契苾何力朝李靖投去疑惑的目光,李靖却是轻叹了一声,点出了关键来:“何力老弟,这回你是大意了,那慕容家的军马,从昨夜子午时分就不曾出现过,想来...想来是去做那件大事了!”
契苾何力猛然跳起,一巴掌就拍在自己额头上,兀自跟了出去,劈手夺了马匹,追随徐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