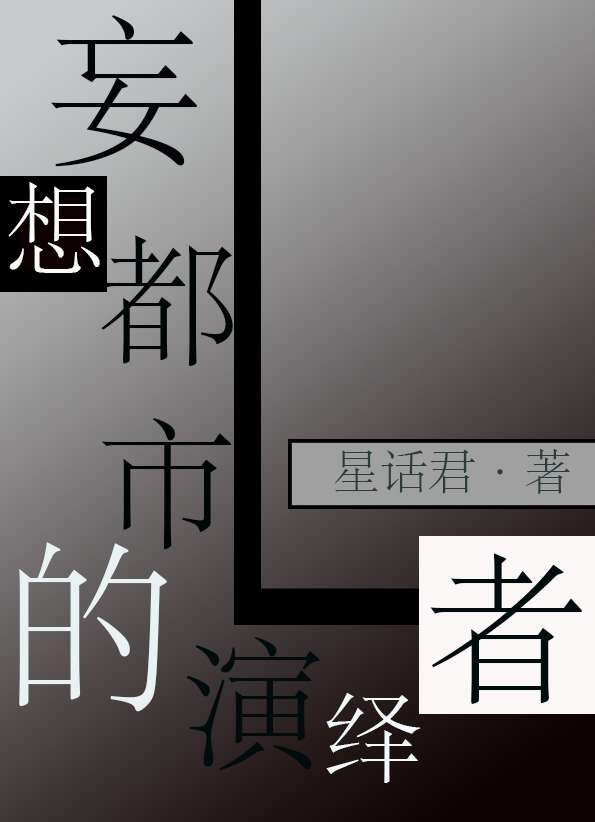“怎么会呢,和某并非嗜杀之人,不说你我二人曾是挚友,单是文兄身上挂着的功名,和某便起不了这般心思。难不成文兄的眼里和某是个视大清律法于无物的人?”
和珅似是渴了,抿了口茶液润了润嗓子,随后才不紧不慢的继续开口:“文兄不必顾左右而言他,用一些穷酸腐儒的体面话来敷衍和某。我记得文兄曾和我说过,幼时家中贫寒,苦于赋税,文兄十载寒窗、连夺三甲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能用功名免了家中赋税,让伯父伯母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罢了。所以追根结底文兄求学入仕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钱,不是吗?”和珅说罢双目紧紧的盯着文有道的眼睛,等待着他给出回应。
“是,文某入仕的初衷的确不是为了造福一方,可文某入仕后却是心忧天下黎民,为他们而思,为他们所急。说起来曾经的和大人也曾是文某这般,只是如今……”文有道回过身来面带愧色,神色中却更多的是伤怀和惋惜。
“是呀,我们曾是一类人。可如今呢?文兄早已离了仕途偏安于这聊城,而和某仍在朝堂为这天下黎民而奋斗着。”
似是看到了文有道面容上惊愕和略带讥讽的神情,和珅淡然一笑。
“怎么?文兄觉得和某人的话很可笑吧。我一个百姓眼中的贪官竟能如此厚颜无耻的说出这般为国为民的狂言。”说着和珅嘴角泛起了一抹无奈的笑意。
“文兄当年为何辞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能在朝堂青云直上吗?没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满腔的宏愿和胸中的志气可有半分能施展的余地。要登上一定的位置,除了为人玲珑透彻外,还不能少了他人的支持。在这点上,什么名誉、外貌、出身的都是次要,想要成为领头羊被人们拥护需要的是魅力,人格魅力。那文兄觉得是一个我吃肉,他人皆可跟着吃肉的能臣更值得人们追随,还是一个我不吃肉,别人也吃不得,每天只是满口空话和大道理的腐儒更值得人们追随。”
话听到这文有道竟不知该如何接,他有心反驳,却又一时找不到足以他言论能站得住脚的论点。
或是看出了文有道的窘境,和珅并没有强求他给出答复,缓了片刻继续开口:“和某也不往远扯,就说一说柳伯行此人吧。别人眼中的他可能是贤德、清廉的代名词,可在和某眼中这就是个无能、无知、且顽固不化的书生。他无能且顽固,散尽家财去救民,这点和某人做不到,文兄也做不到。可文兄有没有想过,何至于此?同样的事若在荏平,高平福宴请几个商贾就可以平白借到数倍于柳伯行倾尽家财且压上官印才能得到的钱粮。是高平福比起柳伯行来更有权势和名望嘛?那些富商不是因为高平福有面子才帮他,而是他们知道今日帮衬一把高平福,他日若有难处他高知县大笔一挥于他们而言多少会有些许便利。而这简单的一笔便足以抵清今日所赠,还会多有富余。而柳伯行呢,他会和这些商贾攀交?和某承认比起柳伯行来说高平福算不得清廉,可在一些事上,高平福却能比柳伯行处理得更好。他是个贪官,同时也是一名能臣。”
“柳伯行他无知的,文兄是不是也很好奇,朝廷派给高唐的赈粮为何如此之少。高唐的赈粮聂成龙并未克扣而是足数派给了他们,文兄也不必拿这疑惑的目光看向和某,和某还不至于在此事上诓骗你。文兄可知国库存粮几许?满打满算百万石罢了,举国大旱各地均需钱粮,莫说此中还要扣去宫中所耗、百官俸禄和将士们的粮饷,就是把这些算上,百万石足以救济全国吗?要救民于水火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想办法。他柳伯行倒是想了个好办法,散尽家财抵上官印借粮救民,好伟大呀。可他给大家开了这个头,一旦渔轮爆发,百官只能效仿。可自掏腰包往上垫,莫说大家愿不愿意,就是都心甘情愿。换来的粮,够吗?官当到需要散尽家财积蓄,那当着官还有什么意义。”
“人言麸糠和草料是给牲口吃的,可真的饿极了,牲口都罕吃的树皮,土饼,人们不照样狼吞虎咽吗?更别说还有些丧心病狂之辈生啖人肉,易子而食。那些饿极了的饥民只是想吃饱活着,他们没想过要吃多好。我们这些当官的需要做的是为百姓谋活路,而不是死要面子的维系自己清廉的名声,和去顾忌那冷酷的大清律法。不可否认朝廷派下的钱粮有部分入了官员们的口袋,可大部分不还是用来换取麸糠和草料救百姓的命了吗?柳伯行那边聂成龙是有和他说过这件事的,他一口回绝了。还直言事后要参这山东大大小小的官员一本。他的所做所行,得罪百官,还触怒了龙颜,此事舆情一旦爆发,本朝大大小小官员有几位能全身而退,怕不是就连圣上都要下罪己诏以慰苍生黎民。更可笑的是他还抵了官印,就他的俸禄,短期内能赎回来吗?本朝官员印信因这么荒唐的一件事落入商贾之手,文兄细想一下这是值得弘扬嘉奖,还是要抹灭清除?所以不是和某要他死,而是他的无知害死了他。于情于理,上至圣上,中至百官,下至黎民莫不希望死的一个古板固执的独身者,而活的是上百成千为民劳苦、求索的能臣。此刻众人之愿得以被成全,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喜事吗?”
”文兄,清廉不等同于死板,世上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和某也不过是引导百官用黎民之财办黎民之事罢了。在和某看来美好的生活,财富以及权势这些才是人们苦求功名并为之不断苦读,乃至于在朝堂努力攀爬的根源所在。而所谓的造福一方百姓不过是在这些渴求得到满足后的一个美好祈愿罢了,更何况这个愿望还非是人人都有。贪些许黎民之财,全百官心中所求,还能将他们藏于心底的愿念萌芽释放和催生,让他们更有心力和激情造福黎民。这样不好吗?”
听着和珅的话,文有道陷入了沉思。
“和某此次前来本是为了平息这高唐的乱况,途中偶然听闻文兄接了柳伯行一案,特地来拽文兄一把,怕文兄入了局中白白丢了性命。文兄呀,这世上很多人和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环境和际遇下他们并不会维持原态。孰是孰非,我说了做不得数,文兄也大抵如此,百姓所言不会骗人,文兄一路走来不知听闻百姓对这救灾之事是认可的多呢,还是仇怨的多呢。闲言多出于那些不饿的好事者,百姓和饥民没那多想法的,他们不过是想好好的活着,饿极了的人是不会去计较这麸糠和草料是否不如白粥更好入口,更不会过于关心何人做这一县父母官。处斩柳伯行的诏令公示的那刻,高唐百姓便不再记得这位柳知县昔日的恩情和所做所感,而是盼着他被稽首。若文兄不信,不妨回高唐去听听百姓的心声。希望到时文兄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本官还有些事要处理。言尽于此,文兄珍重。”说罢和珅挥了挥手示意少年送客。
文有道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这个庭院的,但他的三观均是在与和珅的这番闲谈中被颠覆了,他不晓得谁对谁错,朦胧中他只记得和珅最后说的那句话,不妨回高唐去听听百姓的心声,看他们是希望柳伯行死还是希望他生。
几日后文有道还是上堂了。只是他并不是为柳伯行辨解脱罪的,而是如数家珍般的列出了柳伯行的种种罪证,彻底将这位柳知县钉死在了耻辱柱上。而这次之后,山东再无文有道此人,他就这般销匿了声迹。
数年后,聊城某处深山中,一名身着布衣麻衫的中年男子正悠然自得的坐在湖心亭垂钩,凡俗几多苦乐事,不如隐于深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