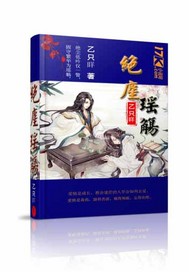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最后一个问题么…”素衣女子瞧着锁链之下阴沉不定的人,眸光微闪,“当年文琪的孩子固然是因为冥豆豆没有的,可我却想知道,你这个黑暗之子与此事究竟有没有关系?”
此话一出,冥越就将她护在了身后,冷眼打量着眼前这个面上含笑的人。
“孟婆问这话,可想清楚了后果?”兆阳似笑非笑的眸子紧紧盯着玄衣男子身后的那一抹白影,“你既是猜出了我今日究竟还有什么事,难道就不怕待我出去之后,与你撕破脸么?”
“三物只得其二的你都不曾怕我毁约,屡屡出言威胁于我,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孟孟轻声笑了笑,“三件东西换九个问题,一旦有问题触及你的禁忌,难道我还没有鱼死网破的打算么?”
“呵呵呵呵呵…”兆阳笑着摇了摇头,“我一向都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待我做了地府之王,必定要先换个粗苯些的孟婆。”
“那也要你先做了阎王再说。”冰冷冷的声音自暗处响起,银翼盔甲的流光都被这一片阴寒的黑暗吞噬,不见一丝光彩,突然出现的声音似乎并没有引起三人的注意。那声音一落,漆黑的空间便又恢复了寂静。
良久,叮当地锁链声打破了这一片寂静,“你真的要知道?”
“要。”文琪的身影自暗处慢慢显出,站在了冥越和孟孟二人身后,眸色冰凉。
“有。”话音一落,兆阳整个人又仿佛化作了一介文弱书生,席地而坐,闭目浅笑。
“有什么关系?”文琪的声音让这一片阴冷的黑暗变得更加凝结,孟孟喉间动了动,终究是站在冥越的身后没有说话。
“当年那碟点心,我早知道是被下了断魂草的。”兆阳狭长的眼睛蓦地睁开,面上还挂着一个阴柔的笑,“他为了王位可以狠下心,我又何须手软?”
“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吃下去?”文琪冷哼,“我总以为你再如何也从未骗过我…如今看来,只怕也未可知。”
“你因为那个回来的孩子心软了么?”兆阳的笑意更甚了些,那笑容仿若不是绽开在这般阴冷黑暗的地界,而是春暖花开的青青河畔,“只因为那个不明不白回来的孩子,所以他的一切罪过便都可以抵消了是么?当年的丧子之痛过了千年,怕是早被忘川河水冲平了吧?”
“兆阳…”
“文琪!”阴柔的声音蓦地提高,他谦和的面部也带着些扭曲,“我早说了那不是你的孩子!那不是!断魂草一旦入体,什么转世什么怨气通通都是狗屁!什么都没啦!你的那个孩子,早在千年之前连一丝灵识都未曾留下就化作飞烟了你听明白了吗?你…”
“啪——”兆阳被打偏过去的头隐没在暗处,他低沉的笑缓缓透出,“你既是不想听,我又何必再说。你的恨可以凭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孩子和千年的时光磨平,我的却不行。千万年,万万年,只要一日未登上属于我的位置,只要我体内的血脉之力一日未被解封,我就绝不会放过他!”
“你这个疯子。”文琪冷声斥责,眸光微转,“你们俩还不出去,当真打算一出去就被他当作踏脚石么!”
“凭他?”冥越不屑地勾唇,周身红芒微。
“即便今日未曾听得这些话,剩下的三个问题只要问了,他也绝不会放过我。”孟孟拉住身前的人,笑意浅浅,“文琪,我早知他不是善与之辈,所以从未想过全身而退。”
“你又何必搅这趟浑水。”文琪声音冰凉。
“那你呢?”孟孟笑着回头,看着那个面若冰雪的女子,“这么些年过去了,当年种种恍若过眼云烟,你若真是心死神灭便也就罢了,偏偏还放不下。文琪,你又何必?”
文琪冷着脸偏过视线,看向那个端坐的人,“你为何总说小係不会是我的孩子。你当年又究竟为何那般肯定我中的便是断魂草的毒?”
“断魂草是阎王本命养出的毒草,天下至毒,就算是天上的那群家伙也不见得有法子解开。”兆阳缓缓起身,眸色狠绝,“断魂草一出必断一魂,当年你既是能够保全,那断的必定就是那个小东西的魂!魂魄既断,又何来怨气?又如何能够结为係囊之体?且不说係囊生长存活只能靠汲人精血,满身邪气又如何能够修为灵体?骗局,这一切都是那个卑鄙小人的骗局!”
“哦?”文琪还未开口,孟孟倒是颇有兴致地笑了笑,“若是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理解是不是就说得通了呢?”
“你的意思是…”兆阳冷哼,“那小係囊本就是灵胎所化,是以不必吸人精血只要靠天地灵气便可以存活么?”
“果真是智计卓绝,心思深沉。我不过起了个头,你竟是就猜中我在想什么~”孟孟挑眉,拍了拍手,“怎么难道你觉得,这不是最合理的解释么?”
“若是寻常草药自然可以如此解释,可我说了,那是断魂!断魂之下,别说生命,连生机都不会有!”
孟孟皱眉,脑中不住地流转着这几日的听到的一切,蓦地挑眉,看了眼冥越,该不会…
“你瞧着我做什么?从九幽绝地回来便瞧到了现在,这天日还早,晚上没人的时候再看好不好?”冥越眨了眨眼睛,笑得满是乖巧。
孟孟一把推开他的脸,嫌弃地瞥他,“什么天界上古神祗,真该让耀光瞧瞧你现在这幅没脸没皮的样子。”
“那正好~”冥越贴着她的手又蹭了过去,笑得谄媚,“耀光一发火就该革了我的神职,罚我生生世世都跟着孟婆当小厮~”
“想得美。”孟孟嫌弃地收回了手,“我只是在想,这一次该不会又是我输了吧…”
“为何会这么想?”冥越挑眉,好整以暇地躺回了软塌上,眼角眉梢尽是倦散。
“你先别得意得太早。”孟孟暗暗骂了句妖孽,瞪着他道,“我只是觉得兆阳的那一番话太过值得深思,那样一个聪明的人倒似乎像是身在局中反倒看不清局势了…”
“你是怎么想的?”冥越好笑地点了点她凝结的眉心,“说给我听听?”
“你说…”孟孟看向他,“当年的那株草,会不会不是断魂草?”
“那兆阳像是连药草都分不清的人么?还是说你觉得兆阳为了把脏水泼向冥豆豆,故意说这是断魂草,让冥豆豆脱不了干系?”冥越一脸恍然大悟地模样,顺着她的话就一顿乱猜。
孟孟撇了撇嘴巴,“兆阳只怕比狐狸祖宗还要狡猾,这种低级错误他怎么会犯。我只是在想,当年他是不是凭借自己的黑暗之血,通过某种途径,偷了冥豆豆的断魂草?”
“偷?”冥越点了点她的脑门,“那你倒是说说,为何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冥豆豆拖了这么些年也没能给自己辩白清楚?难道自己东西被偷了也是什么不可启齿的事情么?”
“那是…”孟孟托着下巴,眨着眼睛颇有些茫然,想了许久像是想到了什么想要和冥越说时,却是对上了一双笑意盈盈的眸,气不打一处来地瞪他,“你少得意了!我现在就去问冥豆豆!他若是再不说,我就绑了文琪和那小家伙,看他说不说!”
“你打得过文琪?”冥越挑眉。
“不是还有你,嘛…”孟孟话一说完就想咬掉自己的舌头…这叫什么话?自己不行还有他?
冥越见眼前的人一副懊恼不已的模样,心间大喜,一伸手便将某只即将炸毛的兔子揽进了怀中,笑得既是餍足,“乖~说得没错,他要是敢不说就先揍他一顿,在绑了他的老婆孩子,看他说不说~”
“噗哧——”孟孟被他一番话逗乐了,乖乖地躺在他的胸口玩着他垂下的青丝,“这么一听我倒像是凡间打家劫舍的山贼,动不动就拖家带口地掳走,逼着人小娘子就范。”
“就他,小娘子?”某人满是不屑,“送上门也不要。”
“谁要你要了?”孟孟挣扎着想要起身瞪他,却拗不过他的气力,只好回手向他的腰间袭去。手伸了一半却又愣愣地停住,神色颇为复杂地垂了眸子。如今的自己,为何会越来越不像自己…还是说,这才是本来的那个“孟孟”?
“你也不准要。”冥越见她难得乖巧,自然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全然未曾察觉怀中人的不对劲。
孟孟被他极认真的语气逗得微微勾唇,低声开口道,“若以后做不得孟婆了,真拖了地府的关系,去凡间当个女山贼倒也不错。恣意妄为,潇洒随心,倒少了种种束缚烦恼。”
冥越凝眉,扶起她,冷声道,“区区小子,不足为惧。他就算是做了地府的阎王,也翻不过天去。”
“你打得过他?”她学着他方才的语气,回问道。
“或许打得过。但此子一日不除,终是后患。他若真制住了冥豆豆,天界与地府万年的平衡只怕就要不稳了…”冥越皱眉冷哼,“就算他真翻了天又如何?我在一日,他便不能动你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