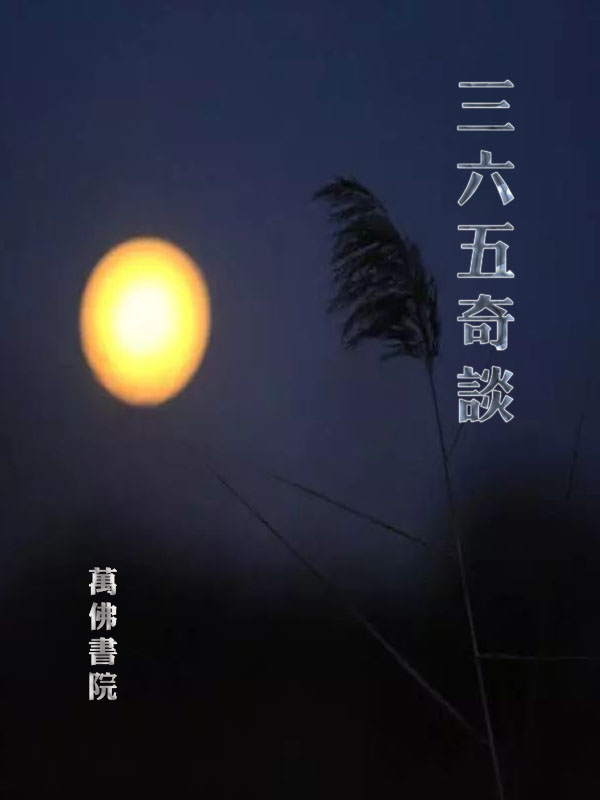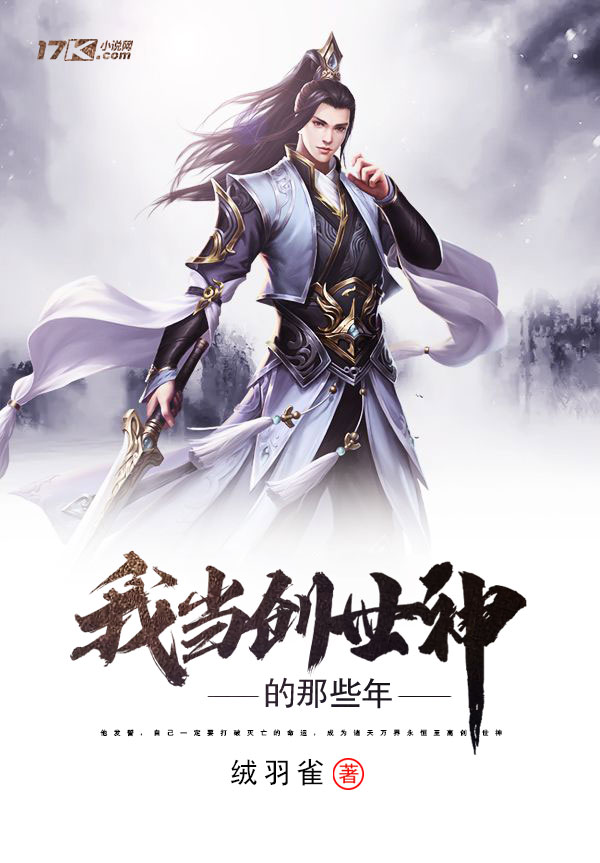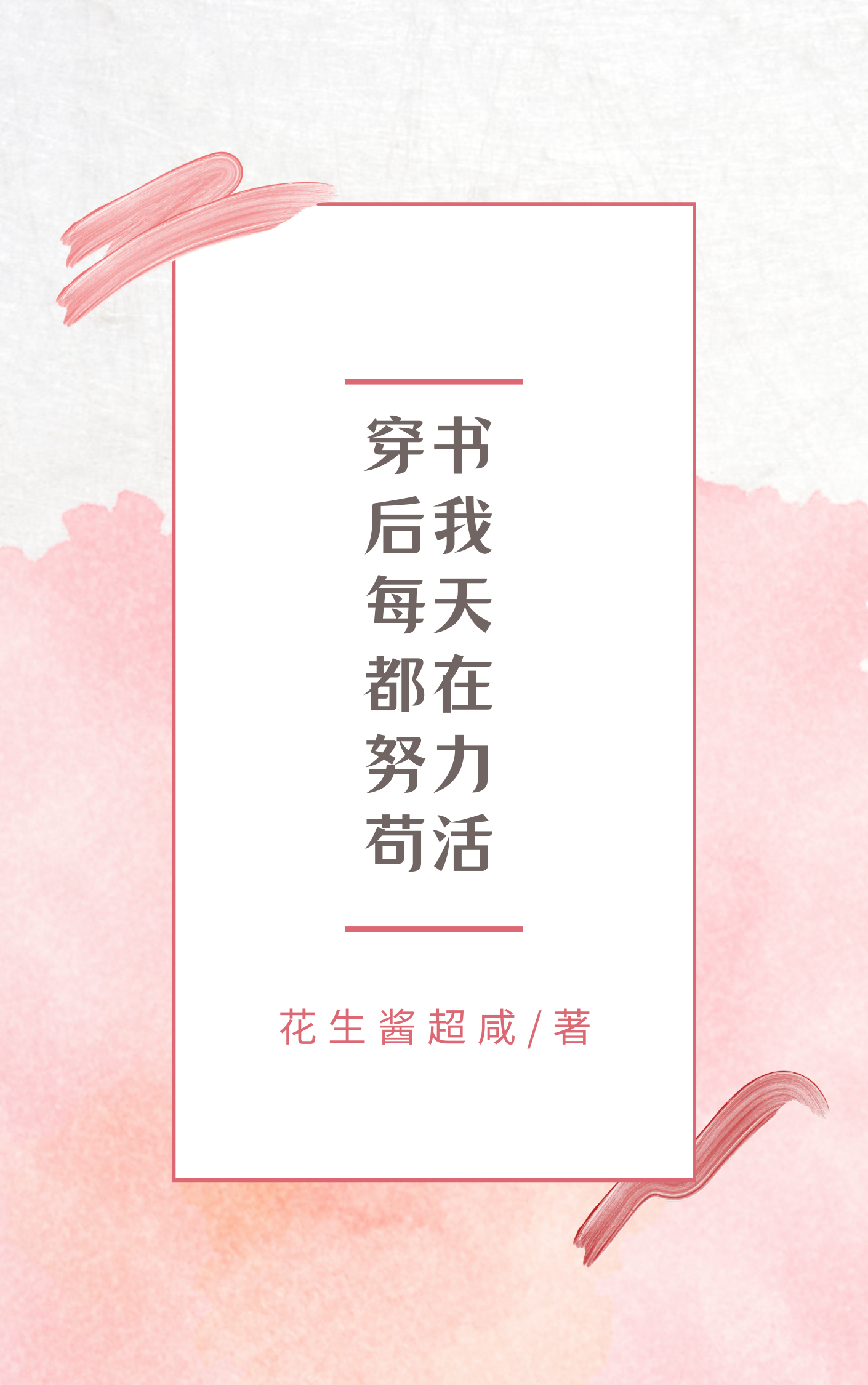此为前言,或曰凡例。
我说:“今我是我,今我非我,今我亦我。”
你能懂得?怕不能够。(因为我自己也不懂——我有着这种体会,在心里好似明白,但是却说不出来;就算说出来了,也不一定是你领会到的。)
盖言文言之弊,随时境之过迁而卒难解读。又观古人小说,纵近世者通文亦需注辅。我之文字乱衍,今人以为“半文半白多不通”,故注。
忽忆昔我为尊师,或尝评我曰:“目中无人,傲气过甚。”盖前者真切,后为非议。何以?其时眼界狭隘,不知而作;又不自信,佯狂装傲。
前我遭批自卑,恐是文非佳,如上述故;然今复观,思惟精妙,从中得获。乃不敢独藏,遂重修公布。
向初作注,意在保守,考补校正而已,琐无益裨;又浮躁冒进,妄解文作。其终不复行世,盖悉缘此过错。
故今重刊表,不独拘文字浅白与否,亦有意简雅之删改;博众评议以发己论,阐旨言趣而凝精华。既然,自尽力听天一试尔。虽不可行,亦无所谓。
又以旧附注正文之法索读不易,今遂置之于“作品相关”。如此,则电脑端可作二窗览对,移动端乃得截图分屏以相观,便利于前。
然今我下愚不知,所注但供参阅,亦或有误处不可具依;读者宜自主张,始阅正文而后再观思,得以与众探析义理,未尝不为一乐。
有作《唯于少时见夜澜》者,盖言及己创作原文时事,亦可与注共读。
我既为此前言一年,稿亡,缘由实难以述。闻昔外邦有罗氏善刻,为一像而断之妙手,是作益名世;今《悲》逸《无》亡,虽为天使,冀希亦能如之。
书之故要:“笑悲无”;后人补附一字,曰:“笑悲无有”;今己则以为“虚寂”。安得此诠?诸君可以一言而赅此作欤?是请览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