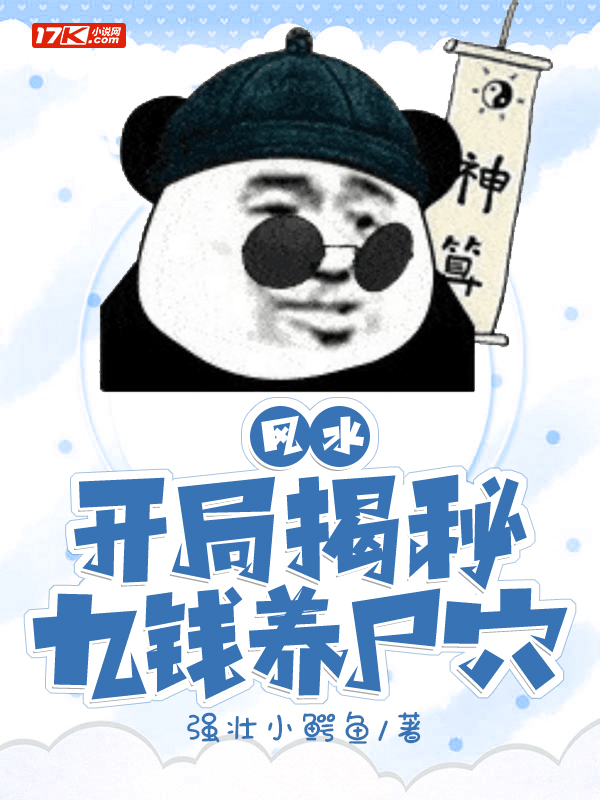才说那剑鞘落地,那明思隋只得站那左右为难,只得等人修好方能接着练了,只是又不免浪费多时。
未闻亦觉可惜,忽而想起自己平日过得拮据,从那装东西的大箱子至那小的食盒、妆奁都是入宫时便一直用着的,到如今未免损坏,自己亦常用那丝线以特殊技法绑了便完事,如今用这法子帮他,亦未尝不可,若是因此有了另一番奇遇更是一桩妙事。
便忙取了自己的手帕,叫住那明思隋,告诉了法子,那明思隋亦是别无它法,少不得一试,只得让未闻帮忙绑了,自己过后再去修理便罢。
未闻便接过那剑替他细细绑了一回,一抬眼只见那明思隋直望着自己一双手,半句话也说不出,又兼当日在家,村里亦有两三等人夸她几句容貌清丽的,便知他定是看住了,心中又惊又喜。又对上那一汪含情之目,似有欣赏之态,便含羞告诉了自己的名字并当差所在之宫殿。
“姑娘之名讳可是‘未闻花名’那二字?在下不敢妄意揣度。姑娘之恩德,在下定当铭记在心。只是这帕子,怕就要待在下修好这剑,方能洗净,恭敬送至姑娘那了。烦姑娘到时再收罢。”明思隋双手作揖,不敢久留,谢过便告辞了。
未闻一听便知他误以为自己告知当差之地,实为催还帕子之意,也并不解释,只更觉他为人正直有礼、不肯私相授受,心中更是钦佩叹服。
未闻看着那背影,“风姿特秀,萧萧肃肃,天质自然”一句跃然脑内,方才那短短一段如同圣光照射,将她整个人包含其内,如梦似幻地在假设中实现了她的种种光耀门楣之愿。只是无意瞥见的他腰上一支看着像常佩的青玉直笛和那熟读诗书亦未曾听说的“未闻花名一句”,令未闻心中着实疑惑。
直至上了那回宫的马车,未闻也反复思索,只是不得其解。
那友希见未闻低头一声不吭,不似往常般高谈阔论,又见刚才情形也猜出了几分,心中自是为姊妹开心,便忍不住笑着打趣道:“你当日还劝我来着,如今也有了心上人,自己着急看不说,还拉着我们陪你,可见是个假正经。”
未闻原为思隋那腰间直笛之事不快,又想起友希当日说的那不务正业的卖艺人,心中不免灰了大半。如今友希又提起,大有拿思隋与那等狂妄之徒作比的意思,不由大怒,又不好发作。
只得狠狠讥讽一番,“姑娘倒是大胆得很,堂堂的皇家侍卫也敢拿来跟那不入流的下等人作比,我是没这样的胆子,幸而这是宫外,不然得掉几个脑袋。这读诗书、知礼义也就这点用处了,不然成日里都像这样讲些大逆不道、没廉耻的话,岂不被人笑话。”
友希听了自知失言,心中虽不服,但又怕伤及姊妹情分,少不得忍了,及至回到宫中,下了马车便头也不回径直走开了,未闻也不在意。
五月初七,宫中武试大典也即将落幕,料想明思隋不日便要从那禁林苑回宫,到时为手帕一事又是不免要见一次,未闻自是辗转不安,成日里想着。又想起那日“未闻花名”自己不甚解,又似十分苦恼,只得去找林说会子话。
去了神女殿,友希也在那里,自己因前日之事不便搭理,只得随意找了一处坐下,一时无话。
抬头暗暗打量,见友希正拿着个西洋式的骨瓷鎏金花樽,细细地看上头画着的西洋神话故事呢,忽然想到友希这丫头平日也不留心文言经典,专在这等稀奇古怪的“杂学”上下功夫的,若是问她兴许还听闻过一二。
只是又不好开口,正踌躇间。友希倒抬起头来对上目光,却像是不大在意那日之事一般,忙含笑让座,无半点尴尬之意。
未闻一面想着这丫头虽不太通的样子,所幸肯于伏低认错,亦不是半点礼仪全无之人,一面坐了过去。便忙问那“未闻花名”之出处,友希果然甚是了解,亦十分感兴趣,少不得将所知一一告诉,又谈些相关之事,长篇大论说了个半日。
未闻开头还仔细听着,及至讲到“此句乃出自东洋画册”,便听不进后面所讲了,什么“浮世绘为最佳”、又是些“西洋画之借鉴”皆左耳入右耳便出,化作浮云泡影,半点不存于脑内。
只顾在心中纳罕,“明思隋一个侍卫,最是该有宏图大志之人,平日里不忙着习武练剑,倒有闲心读这等末流之物,况又是东洋文化而非天怀正统.....”
想着便心慌不已,又无法确定,只得又问直笛一事。
那友希自是调弄那乐谱音律惯得,亦知这直笛并非正统礼乐,又知未闻不喜此物,见未闻大有心灰意冷之意,便只得寻些好话搪塞,道:“这也难讲,兴许是为了平日练习些音域弹奏之法,好为日后担任宫中祭祀礼乐之职也未定,这宫里的礼器旁人也不可轻易得来,用直笛练着也一样。”
未闻听后信以为真,心安不少,又不免想像日后思隋任礼部官员是何等风光,心中自是叹服不已,唯愿其肯进取、担重任。
自此,未闻便十分欢喜,常于饭后寝前思及此事,接而又不免纠结一番东洋文学之事,只恨不能劝一番思隋。
幻想之殿便常开于未闻的被衾梦内,燃着祭祀用的神翼香将她笼罩,浩命之服闪着耀眼的金光照亮了她的过去....父亲打结的胡须由白变黑,家里的破草屋由旧变新,就连干枯如落叶的蜡纸书页也化蝶飞舞,盘旋于宫殿最高的上方,居高临下地俯视琉璃的屋顶、盘龙的宝座。
数日后,有人找到彩绣宫来,只说是来找未闻的,未闻只当是明思隋来还手帕的,忙跑了去,一路欣喜期待不已,只恨不能一时飞了去。
已到宫门口,那人却并非明思隋。道是何人,此时亦不能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