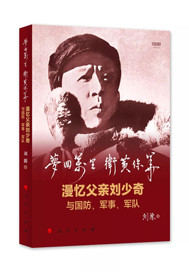琥国少年虽然博广见闻,但这件事显然并不知晓。
“这我可不知道!”琥国少年连连摇头。
“痞子将军到底是谁,恐怕没人知道,但是这人最近却在皓城出现了,那场轩然大波就是他掀起的!”断纹缁衣娓娓道来,神情却是十分向往。
“话说公子昊和费虞从王城龙田逃出,一路向东到了皓城。”断纹缁衣继续道来,如同亲见,“公子昊派费其候统兵驻扎在皓城西面百里处两山夹持的‘扼风口’关隘,以为那里易守难攻。”
“另一方面,向丹琅派出使者求和,条件十分丰厚,简直亡国之举啊——”老先生悲愤异常,捏紧了双拳。
“既是两国谈和交往,往来使者交换书简,必是国之机密,你又如何知晓,如何又亡国了,简直一派胡言!”那青衣男子涨红了脸,口出不逊。立刻众人一阵嘘声,要知道在酒肆中评议国事,是列国惯例,无论观点如何,只代表一家之说,根本不存在告官捉拿之事,更别说言语攻击,口出不逊了,是以青衣男子一出口,立刻招来嘘声。
不待断纹缁衣回答,一名黑衣男子从座中站起,从容走到中间,朗声说道:“在下孟清简,就是和谈使者的随行护卫,亲历此事,可以为老先生作证,老先生所言字字属实!”听众中立刻有人发问,急切要知道求和的条件。
“公子昊为了即位,稳定时局,对丹琅虎狼许下了无耻至极的条件……”孟清简将手指捏得啪啪作响,愤然道,“他许诺说,只要丹琅肯罢兵议和,他愿将王城龙田以北百里土地,连同王城一并割与丹琅!简直将祖宗的基业都卖了,不是亡国之举是什么?”
“啊?!竟有此事,卖国之贼……”
“公子昊费虞狼狈为奸,将大好河山统统割掉,万死难辞其咎!”
“……”各种贬鄙谩骂之词滔滔不绝,难以尽表。
孟清简又道:“丹琅与公子昊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谈,一方面却另有打算。”
“丹琅有何打算啊?”胖子忽然问道,他听着众人群情激昂,不住的骂公子昊和费虞,只觉得和自己并无关联,倒是非常好奇下文。
孟清简道:“丹琅答应和谈,公子昊以为大事已定,便在皓城先王行宫准备即位大典,费虞也拟了遗诏,就等吉日一到,便行登基大典。”
“看样子,即位大典你也亲历了?”青衣男子目露凶光,冷笑道。
孟清简道:“那是当然,当时我知道公子昊开给丹琅的和谈条件,心灰意冷,只等大典结束,便要卸甲回乡,不曾想即位之日,却又起了大波!”
“大典那日,公子昊和费虞特意在行宫内外安排了二千甲士,严阵以待,以防有人捣乱。另外在宫门外支起了一口大鼎,下面燃起熊熊之火,鼎内装油,烧得滚沸。”孟清简口齿伶俐,言辞便给,众人听得一清二楚。
琥国少年大奇,回头问那琥国老者,“烧那鼎做什么?”
“呵呵,少主人,”琥国老者说道,“为了震慑人心,谁要不服,定要烹了他。”
“确实如此!”孟清简点点头道,“大典那日,来观礼的贵胄士人、平民百姓是人山人海,准备的仪仗车马也是连天蔽日,公子昊先去东郊祭拜了大乾的历代先王,然后回到行宫举行即位仪式,这时突然狂风大起,乌云漫天。”孟清简越说越快,用词难免胡乱,但不影响大体。
“公子昊和费虞倒行逆施,也怕遭天谴,便想读了诏书,草草结束仪式,哪想到仪式执行到文官武将叩拜之时的环节,出了岔子!”
“什么岔子啊?”众人纷纷问道。
孟清简向窗外望了一下,外面天色已经黑下来了,阴云密布,风声大起,街上也亮起了灯。二掌柜吩咐杂役也将灯盏点燃,堂内登时灯火通明。
“所有的人惧怕公子昊的淫威,都违心叩拜,有一人却凛然不跪,口述公子昊和费虞丧师辱国、诛杀忠良、暗杀太子、阴谋篡位的种种恶行,滔滔不绝,义愤填膺,自己却气得口吐鲜血,溅满衣襟!”孟清简口若悬河,唾液横飞,学得惟妙惟肖。
琥国少年听得入神,不禁问道:“那人是谁啊?”
“皓城郡尉,宁原,”孟清简满是敬佩之色,“曾是公子玄朗的蒙童恩师,后来公子玄朗去了兵圣谷从学于启武子,宁原便任了皓城郡尉,再后来公子玄朗又去了琪国作质子,宁原却一直作郡尉,一呆便是十年。”众人心中均想,这个孟清简有点杂七杂八,公子玄朗去作质子和宁原呆在皓城有什么直接关联呢。
孟清简又道:“公子昊被宁原骂的狗血淋头,暴跳如雷,即令左右将宁原绑了,连连高呼,以汤镬烹之,以汤镬烹之!”他学着公子昊的语气,活灵活现,恐怖异常。
琥国少年失声叫了一声,“哎呀,真给这位先生烹了么?”
孟清简呵呵一笑,“是要行刑了,但是忠良自有上天护佑,没那么容易便死,两个甲士拖着宁原来到油鼎前面,正要扔入鼎中,忽然风声大起,将仪仗车马吹得东倒西歪,紧接着火光冲天,有人将仪仗点燃,火借风势,立刻蔓延开来,烧向行宫。”
“这火来得好!”有人大声喝彩。
“场面立时大乱,人们纷纷躲避,这时却驰来一匹快马,疾若闪电,眨眼间到了宫门外,护卫的甲士偏生无人能拦截的住,马上武士身着铁甲,神勇异常,弯弓搭箭,一箭将行刑的两个甲士射穿,连在一起!”
琥国少年咯咯笑道:“两个人穿在一起,太好玩儿了,这铁甲将军真是英雄了得!”
他身后站着的一个随从却道:“少主人,你别听他胡说,一箭穿透一名甲士也都是神力了,哪能连穿两人?”看见琥国少年如此仰慕神往,这人愤愤不平,颇为不信。
琥国少年瞪了他一眼道:“仲义,你才胡说,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别人也都做不到么,好好听着,少打岔!”那叫仲义的随从年轻的脸憋得通红,闷声退在一旁,心中暗自较劲,有一天碰着那铁甲将军,一定一决高下。
“呵呵,更好玩儿的还在后面呢,”孟清简说得兴起,神采飞扬,好像自己成了那铁甲将军,等到众人纷纷提问,方才继续说道,“那铁甲将军飞马驰到油鼎之前,一伸手便将那两名甲士拎起,一下投入汤镬之中,嘴里还喊道‘公子昊、费虞奸贼,今日尔等在此宣读伪诏,逆天即位,在下无以为礼,只好烹支人串献上,聊表寸心!’”
琥国少年一拍手,连连赞道:“烹得好,太好了,好一支‘人串’,他将公子昊和费虞一起烹了么?”
“哈哈……”蹲坐在红漆柱前的“小叫花”突然哈哈一笑,“那是即位大典,你当烹人大会呢,什么都不懂!”
“你才不懂呢!”琥国少年大怒,“同为风华少年,人家纵横驰骋,你却自甘堕落,摇尾乞食,不觉羞愧,反来多言。”
“哼哼!”小叫花一脸嘲笑,调侃道,“你又没见过人家,怎么知道人家是风华少年!”
琥国少年红了脸,强词夺理,“这等英雄了得,当然是风华少年!”
小叫花嬉皮笑脸,又道:“嘿嘿,那可不一定,没准是风华老年呢?”
琥国少年腾的站起,喝道:“你也没见过,怎知不是少年英雄!”
小叫花躺倒在地,双手环绕,以臂枕头,笑道:“唉,英雄少年我是不曾见过,思春少女倒有一个!”
原来那琥国少年正是一妙龄少女所扮,刚才坐定甫一说话,众人便已瞧破,认定她是大户家小姐,扮了男装出来玩耍,倒也无人说破,只她自己不觉得,还以为扮相天衣无缝。这会儿被小叫花一语点破,立刻引起一阵哄笑。
琥国少女气得柳眉倒竖,怒道:“你……”抬步便往前挤,看来是要找小叫花晦气,身后的那两个随从反应更快,***上前去。这真是别生枝节,倒底谁更晦气还不一定,厅内众人倒乐得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