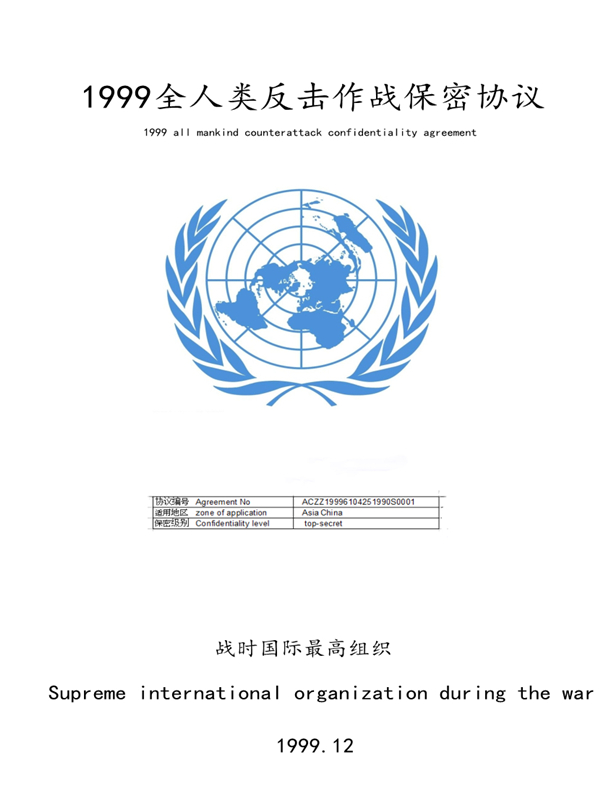“咦?”南宫彻眨了眨眼,生恐是自己看错了,又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没错啊!”果真是肤如凝脂!
可她的脸怎的又黄又黑?
行动在意识之先,南宫彻已经把云歌的袖子挽了上去,露出纤细的手臂,手臂也是凝脂般细滑。
这时云歌身子一动,似乎要醒来。
南宫彻毫不迟疑点了她的睡穴。然后趴过去仔细端详她的脸,足足看了半刻钟,才直起身子哈哈大笑:“丑丫头,原来一点也不丑!”一跃而起,打了一盆温水,在水中滴了两滴药,拧了帕子仔细给云歌净面。
片刻之后,一张如花似玉的脸出现在眼前。
南宫彻这才点了点头:“嗯,我这回才信你是那个女人生的了。我也说么,那女人虽然不是国色天香,可至少也算得上清秀佳人,你爹是有多丑才把你生成这样啊!”
云歌的面部轮廓和那女人有六七分相似,但五官却精致了许多倍,尤其是肌肤,竟是细腻如瓷的,隐隐有着珍珠般的光泽。
只是如今面色极为苍白,即便在睡梦中,眉峰也是紧紧蹙着的,眼珠不断动来动去,很明显如今正被噩梦缠身。
南宫彻又开始摸下巴,照理说,她不可能认识除他之外的适龄男子,她接触的人很有限,除非,那人是她的青梅竹马……
南宫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啐了一口:“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若雪一声哀号,从房梁上翻了下来,哭丧着脸道:“没有跟对主子,怎么正经的起来哟!”
门外传来“扑哧”一声忍耐不住的笑声。
南宫彻恨得直咬牙:“疾风,你给我滚进来!”
疾风推开门,小步走进来,低垂着头,肩膀却一抖一抖的。
南宫彻心中暗恨,磨着牙道:“你给我查一查……”话说了一半忽又打住,云歌若知道自己暗中调查她,恐怕会不高兴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自己使上水磨工夫,不信等不到打动云歌的那一日!而且,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她对自己也并非完全无情……
疾风支楞着耳朵等着下文:“您吩咐。”
南宫彻摸了摸下巴,阴阴一笑:“若雪,你换一身花哨一点的女装,疾风只穿一条犊鼻裤,然后你背着他在青城城里转上三圈!”
“啊?”若雪直挺挺倒了下去,“砰”一声砸得地上尘土飞扬,眼睛一翻,舌头一伸,“本人已死!”
疾风忍着笑走过去,拽着她的衣领,就那么把她拖了出去,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都跟你说了,不能说的那么露骨,你偏不听!这下可好了,连我也受了你的连累!”
屋子里终于又静了下来,南宫彻轻轻叹了一口气,把云歌的衣服拢好,解开了她的睡穴,起身走到了门外。
云歌进入了一个深沉的噩梦。
还是那间幽暗的囚室,身边有昏黄的火苗跳动,那是囚室里唯一的一盏小油灯。
灯花爆了一爆,室内陡然一亮,随即又暗了下去。
刘蕊带着银铃般的娇笑,领着五个彪形大汉走了进来,她一进来囚室内光明大放,四壁儿臂粗的牛油大蜡被同时点亮。
“表姐,你想好了没?”刘蕊笑得欢畅,眼睛里却寒光闪烁,身上那一套翠蓝色绣西番莲的蜀锦衣裙在烛光中熠熠生辉,满头的珠翠更是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把这间小小的充满血腥气的囚室映得少了几分死气。
秦韵低垂着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她一声不吭。
“让我算一算,”刘蕊装模作样地在地下踱着步,“这是第几日了?似乎是第十日了?表姐,我连鞭子都打折了两根,如今这手腕还酸痛着呢,你能不能叫我省点事?你若早说了,还至于受这些皮肉之苦么?啧啧啧,你这细皮嫩肉的,我可真不忍心下手啊!”
秦韵仍旧一声不吭,到如今,刘蕊说的话,她一个字都不信!
秦韵霍然抬头,一双妙目瞪得滚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哑着嗓子道:“刘蕊,我爹娘对你有养育之恩,堪比生身父母!”
“表姐,”刘蕊歪着头,眼波流转,露出几分昔日在闺中的娇憨俏皮,“这就是个笑话!”她意味深长地笑着,“你明知道,你我的陪嫁相差有多么悬殊!你明知道,我从小是活得多么小心翼翼!你是金尊玉贵的千金大小姐,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罢了!舅舅舅母?表姐?谁不知道,你姑姑是我的嫡母,我不过是个妾生子!你爹娘但凡真心疼我,那些下人也不敢背地里指着我议论了!”
秦韵闭上了眼睛,她以己度人,别人又能说什么呢!
刘蕊举起袖子擦了擦眼角根本不存在的眼泪,嘿嘿一笑:“说这些做什么!表姐久旷之躯,你们要好好卖力!”后面这句话却是对那五个壮汉说的,说完,退到一旁,坐到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以手支颐,唇边含笑,等着看好戏。
那五个彪形大汉齐刷刷脱掉了身上的衣服,露出肌肉虬结的健硕身躯,脸上带着垂涎欲滴的笑,一步步向着秦韵逼近。眼前这是南明首富的独生女儿啊!在他们这些人眼中便是公主一般的存在,这辈子,能和她有一夕之欢,便是死了也值了!
秦韵浑身开始剧烈颤抖,她知道落到了刘蕊手里自己好不了,可绝没料到她会这样恶毒!
眼前这五个男人,令她觉得,脏!
那脚步一声声似乎敲在心头,她的心也跳得擂鼓一般。
刘蕊看着秦韵本就苍白的脸变得没有一丝人色,只觉得十分享受,娇笑着吩咐:“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若是表姐说一句不舒服,你们下半辈子就只能做太监了!”
五个大汉赤着身子转身对着刘蕊深深一躬:“夫人请放心!”
门外忽然传来一声低喝:“不要胡闹!”
刘蕊眉毛挑了两挑,悻悻然一摆手,命那两个婆子退下,提起一把小铁锤重重敲在秦韵手肘上,听着那清脆的骨头碎裂声,狞然而笑,“表姐,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你若觉着熬得住,你只管闭紧了你的蚌壳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