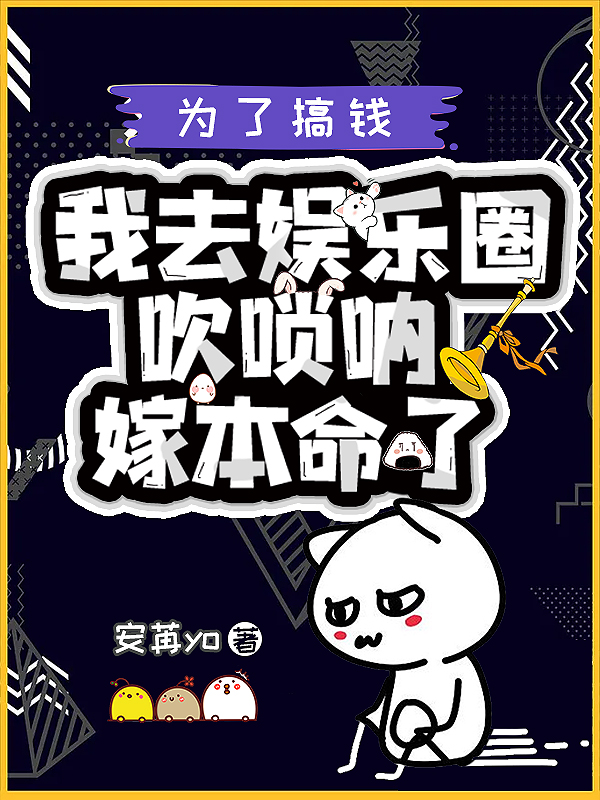那人拖拽的似乎也很费力,毕竟楚宫央虽然清瘦,但身高却是比那人要高,而且她箍住楚宫央的肩膀,见她身子贴在自己身前往后拖拽,楚宫央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背摩擦着那人身前的两团软软的东西。
楚宫央嘴角抹笑,原来是个女的!
拖了大约一百多米的路,那人拽着她进了一间废弃的民宅,关上了大门,才松开楚宫央。
天虽黑,可借着雪光可以看见那人的确是个女子模样,只是脸被黑巾蒙住,楚宫央无法辨认,于是警惕的问道:“你谁啊?要干嘛?”
那女子冷嗤一声:“才几日不见,楚大人就记不得下官了。”
她一开口说话,楚宫央才知这人居然是...
那女子摘下黑色面巾,果然,这人正是一悦。
楚宫央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女人在朝堂上混的风生水起,却不想武功竟也在她之上,她楚宫央还没与其过招,竟被她以一指之力擒住,太可怕了!
“怎么会是你?”
一悦将她拖进屋子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火折子,找了几根柴火点燃起来,楚宫央身体被点了穴动弹不得,只能站在一旁,一悦却闲散的坐到屋内废弃的木椅子上。
然后才看着楚宫央回答她的问题:“你不能去山神庙,娄贵妃正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楚宫央声音徒冷:“果然是娄贵妃!”
“哎,你怎么知道的?”楚宫央突然想起这才是目前应该关心的问题,一悦为何会知道,又为何要阻拦自己去山神庙赴约。
一悦突然站起身,一步步朝楚宫央走过来,她的眼中似有异样,楚宫央也分辨不出究竟是什么,因为太复杂,复杂到不知那种目光才是她真正想要表达的。
“三小姐,你进宫来是何目的?”
许久,一悦才开口说道。
楚宫央一愣:“你,叫我什么?”
一悦眼中闪着泪花,但又随即掩去,声音中透着几分悲痛:“三小姐,你进宫是为了给西商五万亡灵复仇!如果你因为那两个根本不认识的所谓父母而去送死,那你进宫这八年多所有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了!”
她越说越让楚宫央震惊,楚宫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磕磕巴巴的问道:“你,是,西商人吗?”
一悦点点头,楚宫央瞪着大眼睛盯着她,思绪乱成一团:“你怎么会,会变成西商人?”
一悦笑了笑:“三小姐,你是被一悦刚刚吓到了吗?一悦本来就是西商人,哪里会有变成西商人一说?”
楚宫央声音略带黯哑:“我,你...”
见她惊诧的语无伦次,一悦其实也都明白,素来与其关系不好的敌对之人,忽然变成了自己的族人,换做是谁都会惊讶的。
“三小姐,你是族长之女,生活在西商主部,所以是不认得一悦的,但其实,从你入宫后我便知道了你的身份,可我怕有心之人对您不利,所以不敢与你相认,我表面上与你不和,当你的绊脚石,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惹人怀疑,但是一悦暗地里却是时刻关注您的安危。”
楚宫央眼睛逼出泪花,她怎么会想到,这么多年,在仇敌的身边,会有一位西商族人暗中保护着自己。
一悦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她拍拍楚宫央的肩膀:“三小姐,今日说出来心里瞬间舒服了,只是今晚之事您是万万不能去的。”
楚宫央道:“可是,我那爹娘...他们毕竟是无辜的...”
一悦叹口气,道:“三小姐,实话告诉你吧,娄贵妃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你上钩,而且,她还请来了荣轩,今晚只要去山神庙赴约的人,就是混入大祁的细作!”
楚宫央眸底一惊:“荣轩怎么来?他会听娄贵妃的怂恿吗?”
一悦慢慢道:“皇帝是什么?是这个江山的主宰,在皇帝眼中,江山社稷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敢对他的江山有威胁的人,无论真假、不管是谁,下场都一样!三小姐,你在荣轩身边这么多年,还不了解这一点吗?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道理你不知道吗?”
楚宫央垂下眼眸,深宫争斗,步步都要小心,而她根本就不是个有心计的人,整日大大咧咧,难怪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悦知自己说话过了头,于是柔声道:“三小姐,一悦不是有意伤你,只是为了让你看清现实,这深宫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善茬,更加不要相信任何人。”
楚宫央点点头,问道:“那要怎么办?就算我不去,荣轩若是相信娄桂华,还是一样会杀我的!”
一悦凝视着她,半响才道:“我今日既然在这里拦住你,就是为了救你的。”
“什么办法?”楚宫央好奇的问道。
一悦没说话,只是笑了笑,楚宫央心中隐约有些不好的感觉,便忙急着问道:“一悦,你要做什么?”
一悦摇摇头:“我没想做什么。”
楚宫央不动声色:“那,你将我穴道先解开好不?这样我身子都僵了,好累啊。”
一悦果然没有任何动作,而是顺着破旧的窗子看向屋外,楚宫央算算时间,估计娄贵妃的人马已经埋伏在了山神庙。
楚宫央见她不理会自己,便扯到别的话题上去:“哎,一悦,你既然是西商人,那你本名是什么?你又怎么会来到祁国,成为荣轩身边的女官呢?”
一悦沉默半响,还是提起了那段充满伤痛的过往:“我本名叫姿月,我爹爹是西商守护恩河滩的将士。”
楚宫央想到那时候振边侯为了抢夺月湖雪明珠,血洗恩河滩,难道一悦的父亲家人是死在那场战争中的吗?
一悦继续道:“我爹爹本来是守护恩河滩的将士,但是因为遭人陷害,被四长老贬为贱民,而那日,为了找到雪明珠,我爹爹以及母亲弟弟都被振边侯所杀,他们连我只有三岁的弟弟都不放过!三小姐,这不仅是我们一家人的仇,也是整个西商的仇,后来,我被送往祁国军营做军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