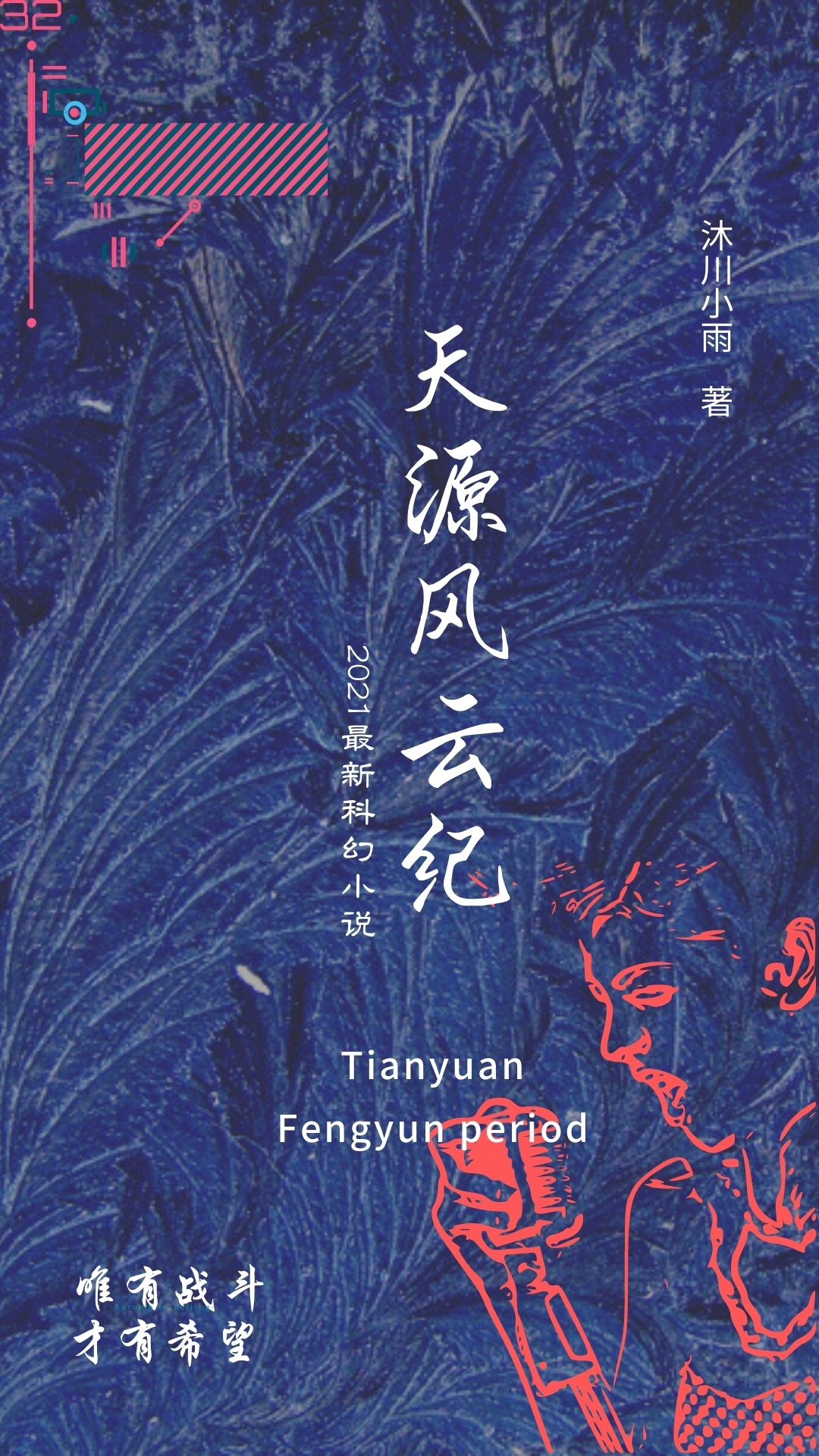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度量差异引发的统计、运算难问题。栾奕决定继秦始皇之后,再进行一轮系统的度量衡和度量单位统一。
他先简单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身高,大约是后世所说的两米。然后用标杆将之记录下来,平均一切为二。切开的标杆一根相当于一米。接着将一米长的标杆再次平均切割,又得到四根半米长的木棍。随后进行第三次切割,八根约二十五公分长木棍便出现在了面前。
每根木棍的长度——既二十五公分就等于一尺。
十尺等于一丈,一丈也就是二十五米左右。一尺等于十寸,一寸也就约等于二点五公分;二百丈等于一华里也就是五百米。
为了适应未来高精密器具对尺寸的精密要求,栾奕还依据“毫厘”一词,设置了厘寸和毫寸两个单位,既:一寸等于十厘寸,一厘寸等于十毫寸。
新的长度单位和标准就这样出炉了。
在重量和容积方面。
栾奕以自己的身高为标准,找到了单位尺的长度——一尺等于二十五厘米。将一尺平均二十五分便是厘米的长度。
他以厘米长度为基础,令工匠制作了一个高十厘米,宽十厘米、长十厘米的琉璃容器,它容积也就是一立方分米,依据后世的数学知识,一立方分米等于一公升,而一公升等于两市升。
单位:升就这么得出来了。
同时,众所周知,一公升水的重量等于一公斤,水的重量不难测量,只需称出容器加水的重量再减去容器的重量便可计算出来。一公斤的实质重量就这样测量出来了,它的一半便是一市斤。一市斤的十分之一便是一两。
如此一来,华里、华丈、华尺、华寸、华升、华斤、华两等新的度量单位就这样面世了。
诚然,介于栾奕对自己的身高存肯定与两米存在差距,所以得出的其它度量单位必然与后世有所误差。
但是,作为衡量事物多寡的标准,度量单位只需明了、精确而又富有逻辑的将事物的多寡诠释出来便可,没有参考后世参数的必要。所以栾奕编制出的这套度量单位具备了足够的科学性,至于一华寸和二十五厘米间那点微弱的误差已经不重要了。
单位出炉,剩下的就是度量衡的锻造。在这方面栾奕责令帝国军械局用目前掌握的耐热胀冷缩性最强且最坚固的合金打造一批直尺,并依据他所给出的数据在直尺上标识刻度。同时还令军械局按照他所给出的华斤重量锻造秤砣。
为了彰显自己对更换度量衡的重视,他在圣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将帝国各州刺史、宗主教、三军都督招入帝都,在大殿上亲手将一箱箱新的度量器具交到他们手中,勒令他们回到地方后,以此为依据,政、教、军联合组织专项行动,立刻着手督促州内百姓换掉手头现有的度量衡,按照帝国给出的标准统一度量单位。争取在今岁秋收前,依据新的度量标准,上报年度税收。
上面重视,下面自然不敢怠慢。
于是乎,圣元二十六你按上半年,整个帝国都深陷在轰轰烈烈的度量衡更换工作中。
更换度量衡,听起来简单无奇。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异常繁琐,让帝国五千万人口一改往日习惯了的计量单位,换上新的尺度和秤砣,百姓难免不适应,甚至有所抵触。
不过,在帝国朝廷的统一调度下,在地方官府和教会的呼吁、劝导,以及帝国地方驻军的监督执行下,百姓们很快接受了这一现实,各地富贾乡绅和普通百姓依据法令、法规相继将旧的砝码、秤砣、直尺、米斗上缴官府,换得了新的度量标杆。
在帝国所有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度量标准赶在秋收前一个月,自七月一日开始便在帝国各地投入使用。于是,当年的粮产统计变得简单了许多,数据也更加精准。
统计结果显示,仰赖于圣元二十六年各地既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帝国又迎来了一个丰年,粮产量既连续三年增长后,又提高了一成多,百姓沉寂在丰收的喜悦里。
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栾奕比谁都要高兴。更让他兴奋难当的是,在经过了思念休养生息后,帝国国库、粮仓充裕起来,粮食多到无仓可装,金银堆积如山……帝国又有资本对外发动一场大战了。
介于华夏帝国主要的强敌——塞外草原民族已被帝国征服,余下的番邦、部落实力稍逊。这一次栾奕准备开启双线作战,同时攻伐两个战略目标。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有三次历史转折,第一次是在明朝,随着大明帝国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大有一副由封建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过渡的趋势。就在这个时候倭人冒了出来,他们的军队扮成海盗在福建、浙江包括山东沿海四处作乱,大幅延缓了大明的资本化进程。最终,满清入关将华夏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彻底断绝。
第二次转折点是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随着以夷制夷策略出炉,满清政府逐步开始改革,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然而,就在满清政权各个领域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再一次成功阻隔了华夏民族追求进步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拉开了序幕。
第三次转折点更不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对中华大地民族经济的破坏暂不必说,还有一千二百余万同胞死于非命。五三惨案、南京大屠杀……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件见证了这场人间悲剧。华夏文明险些遭受灭顶之灾。
当然,除了报仇以外,栾奕之所以急着消灭倭奴还出自对倭人的担忧。这群生活在小岛上的人群,别看他们人口不多、国土面积不大,但正因为人口稀少、国力不强,他们才畏惧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战战兢兢在中国和朝鲜的夹缝里度日。也正因了这份时刻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不得不拼了命让自己变的强大——他们培养出了强大的学习能力。
他们学习,但凡好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学。公元四世纪时他们还处于青铜时代,但五世纪时整个日本社会就完成了铁器改革,别人用四五百年完成的青铜到铁器的转变,他们仅用了不到一百年就从大唐学了来。他们本就聪明再加上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便培养出了极善去糟粕取精华的能力,中国的东西好,他们就学中国的。西方的技术高,他们就学西方的。他们虽然始终没站到世界的巅峰,却也从来没有被拉下过。
这个民族就像他们的国旗,跟块狗皮膏药似的跟着强者走。
栾奕害怕有朝一日,倭奴把神圣华夏帝国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学了去,反过头来再祸害帝国。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一听这话,文武眼睛一亮。现在的他们已经不再是诸子百家独尊儒术时期的道德模范了。在他们眼中什么恃强凌弱、以德服人,那是人与人交流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