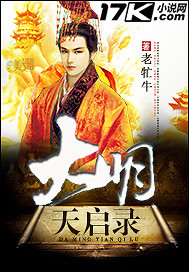苏安一脸急色,应道:“禀告渠帅,大事不好了,神教的人马杀过来了!”
苏安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朱英结结实实给那苏安一记耳光,“狗屁神教,圣母教是邪教,邪教懂不懂!”
“呃,哦,哦……”苏安万分委屈,嘴上却连连应承,“是,是邪教。邪教的军马杀来了,现正在营北鸣鼓进军。渠帅,咋办?”
“还能咋办?”朱英怒不可赦,“还不速速给本官点齐兵马迎战!”
“呃……喏!”苏安连忙呼喝手下去各营唤醒刚刚睡下的黄巾士卒,让他们披挂上阵。
可是,当黄巾士卒各个整装待战的时候,大营北门外却偃旗息鼓,没了动静。二万余黄巾军守在大营之外,借月色打量黑漆漆的远方,不明所以,面面相觑。
“邪教军呢?”朱英怒问身侧苏安。
苏安疑惑不已,“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会儿不知怎地退了去。”他兀的露出几丝献媚似的笑容,“他们大概是畏惧渠帅英明,自己退却了吧!”
“放你娘的狗臭屁!”朱英大骂出口,“栾奕狡猾似狐,才不会如此不战自退。速派探马寻觅栾奕动向,另加派人手守卫营盘。”说完,马鞭一挥,退回大营中去。
望着朱英离去的背影,苏安啐一口唾沫,低声叫骂:“狗东西,神气什么!要不是你横插一缸子,这渠帅的位子本该是我的!”
教会大军不见踪影,黄巾军众士卒亦是各自散开,回营歇息去了。
朱英折返回帅帐,大步走向帐中的美娇娘。他那双贪婪的眸子在姑娘身上上下打量,在看到女孩一脸惊恐神色之时,他兽性愈发膨胀,亟不可待扯掉甲胄,向姑娘扑去。
姑娘吓得心惊肉跳,凄厉大喊:“啊……”猛地,她忽然记起教堂里的神甫讲经的时候曾说:圣母的子民不得与异教徒通婚,更不能让异教徒玷污了身体,若是违反,必被圣母厌弃,不得入圣母的国。思及此处,姑娘虽又恐又惊,心底却冒出无边的力量。她宁肯死也决不能让眼前这个恶魔沾染自己的躯体,哪怕一尺一寸也不行。她用颤抖的语调惊声高叫,“别过来,再过来……再过来俺就殉教!”言毕,她连滚带爬,跑到帐中铜炉之前,做出随时追被撞个头破血流的模样。
然而,她终归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男人的强壮超出了她的想象。
朱英三步两步冲到姑娘身旁,不等姑娘赴死,一把将她硬硬拉到怀里,邪笑道:“想死,没那么容易。”他将姑娘扑倒在地,人类最原始状态下的反应霎时间显露出来。
姑娘死命挣扎,可她怎可能是雄壮的朱英的对手,只能用惨叫发泄。
“神啊!俺最敬爱的母……请您宽恕您最忠实仆人的罪吧!”姑娘大哭!“求您救救您的子民吧!”
正当姑娘陷入绝望,朱英即将开展实际性行动时时,又闻营外一阵锣声大响。随之,帐外传来副帅苏安焦急的呼唤声:“渠帅,不好了,不好了!神教……哦不,邪教的军马又杀来了!这次是在西边!”
“王八蛋!”朱英闻讯,瞬间疲软下来,骂骂咧咧从姑娘身上爬起来,七手八脚穿上衣袍,提着甲胄冲出大帐,却在一撇之间发现苏安脸上流过一片怒色,在看到自己出账之后,怒色才渐渐掩去,换上惯有的献媚笑容。
朱英霎时明了,知道苏安会错了意,以为刚才自己叫骂的那声“王八蛋”是在说他,心中懊恼。不过,对此朱英并没有解释什么,自己堂堂渠帅,骂个人算的了什么!“速速整军备战!”
于是乎,刚刚躺下进入浅睡眠的黄巾士卒再次被各自校尉呼喝起来,骂骂咧咧披上衣服,无精打采随军出寨。可是踏出寨门,却如刚才一般,哪里有圣母教大军的影子!又等了将近一个时辰,还是没有动静。
朱英一脸疲态,暗骂栾奕卑鄙。忙活了大半夜,“正事”没干成,圣母军的动向有没有察明,疲惫不堪。他渐渐明白了栾奕的意图,知道栾奕这是故意想要拖垮自己和旗下军队,却又拿它没有办法。
“渠帅!”苏安走上前来,思索道:“俺咋觉得邪教大军这是在故意折腾咱们呢!”
“傻子都能看出来!”朱英怒气尽显。
“傻子”二字如针毡一般直入苏安心底。早对朱英心怀不满的他,下意识认定,朱英这是在说他是傻子。他脸上再次闪过一片一闪而逝的怒容,摆出恭敬模样,“禀告渠帅,士卒们劳累一天,经不得这般折腾了。要不然这样……反正他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咱们何不不去理他,任他们自己折腾去。咱们继续睡咱们的觉?”
“笨蛋!”这次朱英真是在骂人了,“那样就真的中了栾奕的奸计。他正等着咱们这么想,再趁晓光浮世,我等大悲蒙身之时攻陷营寨。届时,谁来守寨?”
朱英一席话直顶的苏安满面通红,灰溜溜看着朱英拍马回营。
这次回账,朱英再没有心思了。他怒气冲冲对姑娘吼道:“等灭了栾奕再收拾你!”
姑娘没有多言,心里却乐开了花,直叹:圣母显灵,救她于水火。有了信仰支撑,方才的恐惧感觉顿时消去了不少。
朱英见状,越发愤怒,令人将姑娘押去别处,好生照看。
诚如朱英所想,丑时鸡鸣过后,在这个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营外鼓声、锣声、棒子声震天动地,比昨夜任何一次都要强烈。他暗讨:该来的还是来了,栾奕果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总攻。
他连忙召集人马出寨迎敌,可是当大队人马在寨外集结完毕的时候,却发现仍旧看不到圣母教大军的踪影。搞得他莫名其妙,猜不透栾奕到底想要干什么!
思虑间,却听黄巾兵众怨声载道。出奇的,副帅苏安率先发难。他一改往日嬉笑模样,板着面庞对众人,发起牢骚:“你看看这一宿把大家折腾的,连个觉都没睡好!”
“是啊!俺要睡觉!”
“困死了!俺不干了!”
“再这样下去,不让人杀死也困死了!”
……
应和之声不绝于耳。
苏安转向对朱英说:“渠帅!你看,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要不……让兄弟们好好睡上一觉?只留些许护卫巡视应付邪教兵马便是,反正他们又不真打,不过是玩些敲锣打鼓的小把戏罢了!”
朱英环视一眼满脸期待的将校士卒,坚定摇头,道:“不行!若是真打那可如何是好!”
众士卒看向朱英的目光瞬间添入怒色。
“那便这样!”苏安想了想,又劝,“留半数人马随时戒备,另外一半安心歇息可好?”
朱英再望一眼众士卒,心知众人却是疲惫不堪,时至此时,再不让他们休息,军心必然大乱。军心一乱,仗也就没法打了。“那好!便依副帅所言,半数戒备,半数休整。”
一听可以睡觉,黄巾士卒无不举手欢庆,兴奋致谢,“谢副帅体恤!“丝毫没提朱英的事。
朱英心头不快,可有拿这些刁民愚民没有办法,恶狠狠瞪一眼得意洋洋的苏安,回账去了。
返回帅帐,朱英也不脱甲,坐在案边反复猜度栾奕总攻的时限,久思不得其解,困意栖身,沉沉睡去。
睡梦中,他梦到自己又回到历城县济南王府之中,坐在他蹲守了20年的大堂上。时值用餐时刻,白日掳来的那位美娇娘为他端送餐点,那菜肴各个珍馐,香气扑鼻,细细数来足有13道菜,都是他最爱吃,且自离开济南后许久没有吃到的。
他大块朵颐,吃的甚欢,满嘴流油间,却见栾奕闯了进来。
栾奕满面堆笑,一脸邪象,冷冷地对他道:“朱贼,吃吧!好好吃,这可是你的断头餐!”
梦至此处,朱英猛地惊醒过来,抬头一看,见案头摆着碗筷,碗里撑着面汤、野菜等菜肴,想必这便是他今日的晨食。
他端起碗来,刚想喝一口面汤,却在感受到陶琬传递给五指的温度时,猛然惊醒,弃了碗筷大步冲出营帐,望向后营。只见,后营之中炊烟淼淼,清晰可见,想必正在埋锅造饭。
朱英大叫一声“不好”,奔向后寨,绕过排成一排打饭的兵卒,来到伙夫身边,一脚把饭锅踢翻,面汤流了一地。
朱英怒声高喊:“谁让你埋锅造饭的?谁让你埋锅造饭的?不想活了?”
话音刚落,去见苏安带着数名亲随匆匆赶来,傲然道:“朱渠帅!是俺让他们这么做的。士卒们征战许久,总得弄口吃的不是?”
“饿了可以吃面饼,啃干粮,烧火干啥?”
“渠帅久处高位,可能不知兵将疾苦。面饼、干粮乃起兵来济之前制作的,如今放置许久,都馊了,连狗都不吃,人怎能咽得下!是以,本副帅才命人升起炉灶做些热乎饭食,好让兵将们征战之时身上有气力!”
“是啊……我们想吃口热乎饭!”
“俺再也不想啃那臭干粮了!”
“简直不是人过得日子!”
“望渠帅体恤!”
众人一阵聒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