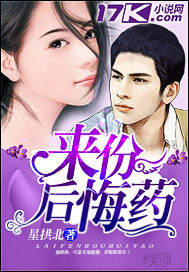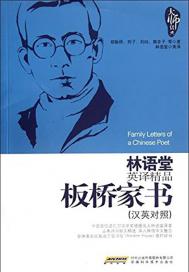不知不觉中竟然到了新年,前两年的大年三十都是和健一起过的,但是今年不同了。因为之前两年的健都是独自一个人在上海生活读书的,不过今年因为健结婚了,所以他的父母也留下来一起过年三十了。估计今年得是孤家寡人了。
在小年夜的晚上独自在床上感叹着人生苦短,半夜十二点了,可是眼睛却睁得圆亮,久久不能睡去。我站了起来,打开窗户看着烟雾弥漫的天空和热闹的人群倍感无奈。仰天长叹了一口气。今晚的气氛实在难以让我入眠。
“我操你妹!他妈的别放鞭炮啦!”吼完我就立即躺在了床上。人家在小年夜放鞭炮也没什么大错,而我刚才也只不过是属于一种宣泄。
大约到了十二点二十分的时候,鞭炮声渐渐没有了,当我刚进入梦乡快吃到那个烤鸡的时候,那杀千刀的健来了电话。
“喂!你干吗啊!”我恶狠狠地说。
健先是楞了一下,“你吃炸药啦你?”
“我这梦里吃着大餐呢,你搅什么乱啊你。”
“今天小年夜啊,你那么早就睡啦?”
“你过年过疯了吧,小年夜你也守?”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没有过年守夜的习惯了,可是今年大家的热情似乎特别高,连小年夜也不放过,都放着鞭炮欢快。
“呵呵。”健傻笑了一下,“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吃年夜饭吧?”
“不去。”我回答得斩钉截铁。没等健发表什么意见就挂上了电话。翻了个身打算大睡一场。怎料健仍不死心,发来短信一条以作骚扰。“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要不今年还是我们俩一起过吧。”
以防健的二次轰炸,我果断地关了机。
几番折腾,虽然夜空是平静了,但是我的心却激荡起来,只好坐到窗台上去看看心。觉得这样或许能够得到些平静。楼下之前热闹的空地上只剩下了鞭炮的尸体,欢快的人们调皮完回去睡觉了,之前睡觉的人们只好看着外面发愣了。在远处的地平线泛着暗黄的光芒,月光映出了空中游离的云彩,想到了夏雨那堆云。我开始对这个如云般神秘的女人有些兴趣了。
次日早晨醒来并不见健的短信,心中些许落寞。昨天拒绝健并非我的确不想去,而真的如健所言,是有所顾虑。人家一家门搞团圆的年夜饭,我去凑个热闹算什么?以前健单身的时候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敲他竹杠,不过现在健也是有家室的人了,我再插一脚,不合情理。而且……沈莹都说了那样的话,我哪里还有脸去面对他们家人呢。
去楼下买了两个大饼上来泡在牛奶里当早饭吃,这种吃法是我外公在我小时候教我的。牛奶随便加上个什么东西都有股怪味,但是单喝却挺香的。今天嘴里又长出了三个溃疡,也只有这种吃法能不刺激溃疡。醒来的时候觉得头晕晕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吃完大饼后就坐在餐桌前发愣,胸中有说不出的忧伤。对于今天这个症状这两年有些频繁,而周期也正好是一个月。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得了什么抑郁症,就求问了强大的百度,百度的答案也是非常强大的。说我这是男人的生理周期,就是除了不流血之外,症状都相同。更通俗的说,就是男人的月经。
知晓了这个答案后,我便把QQ签名改为了“老子今天来月经了”。
出去逛了一圈后发现了很多留言,有部分是令我热泪盈眶的。
大脸:怎么了?被人打了?流血了吗?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能哥:魔兽开服了。
冰雹:我的护垫借你。
胖子:哥们,做变性手术了?
豪(曾经的高中老师):我记得你是叶潇吧?好像是男的呀……
DaMn:我就猜到你是个女人,我们玩LES吧,我当T!
鸟人:你欠我的两百块钱什么时候还?
……
估计今天的留言数是可以破我的流量记录了,虽然有很多人我已经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不过还是很感动。虽然今天不是初潮,但是他们知道后也第一时间来关心我了,这份心意我能够感受到。其中冰雹的留言最直接也让我最温暖,因为其他人都只是言语上的关心,而冰雹是真正向我伸出了援手,即使真的用不到我也会收下,我下次也一定买一包送给她。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新年里的这段日子真的是闲得蛋疼,找不到正当工作也没有小说写,只好我去看电视。正巧调到一个偶像电影,带着找灵感的心态我忍着反胃看完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高中挫男两次被同一个女人同一种方式玩了两次感情的故事。虽然有那么点感人,主要最后几分钟男一号哭得太凄惨了。首先得肯定这个男主的确挺纯情的,同样的当上两次也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戏是可以无限拍下去的。按照主人公的性格来看,是绝对会继续上第三第四次甚至第N次当。
看完后站起来想去倒水,可是觉得头一阵晕眩。我扶在了墙上差点就一头扎倒地。我以为是由于这两天电视看得过头了,就躺到床上睡。解结果一睡也没个头,睡醒了还是想睡。不论怎么睡都是睡不醒。
在被子里不断打着冷战,肯定是发烧了。拿了体温计一测,怪怪,我大吃一惊!巨骇,把体温计拿近了再仔细看着。确定了没有眼花才放到一旁。
三十六度五。
我“咻——”地一下从床上爬起来,三秒钟后又“啪——”地一下倒在了床上。想去医院但是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只好打电话向健求救。
“喂……是我……我快……快不行了……”我奄奄一息。
“我……我也快不行了……”健喘着大气不知道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或许没有什么。
当告之健我是病得不行了的时候只听见挂电话的声音。用医院的体温计一量,已经是四十点二度了。
“怪不得我觉得那么冷。”我靠在健的身上对他说。
“恩,可以煎蛋了。”健摸了下我的额头。
医生看了下体温计摇摇头,“先打一针。然后吊个水。”这医生座位的背后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救死扶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