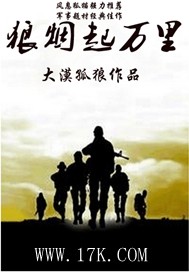我一身男装着体,头戴鸭舌帽,大摇大摆走在一群打扮得楚楚动人、贤淑曼妙的女孩子们中间,一举一动有意模仿着男儿形态。
俏目盈盈含波,美面精中趁秀,所经之处,总会引来那些长久囚于“牢笼”,未经世面的“金丝雀”们青睐而惧怕的目光。
每每望她们脸红心跳,无比娇羞之态,我便总也禁不住低头阵阵窃笑,少不得捉弄她们几番。
故意背着手,漫不经心走过近前,拍拍这个肩膀,撩起那个袖子,硬要探看她们有无传染病;尔后,嘻嘻笑着,往她们白嫩透红的面颊、大腿上拧一把。
爹爹创办永程女学,本打算最多只招两个班,各五十名新生。可眼下女学已成一种气候,报考者之多、咨询之广,却是爹爹所始料未及的。
先前校舍显然不可满足需求,但若增加班级、名额等,师源、资金定都成了问题。
爹爹左左右右,反复忖度,方下定决心,按先前初衷招生。不然,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如此一来,每每应征之时,淘汰、压缩新生的担子便如数落在了我纤肩之上。报名者得需过我这关,经我目测、淘汰。尔后,由爹爹复试责录。
花里挑花,百鸟选凤,这差事,做来真真无味。
不过还好,我素来顽皮喜闹,生性活泼。无味之中,也总可找出事端凑趣,是以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
惟妙惟肖的男儿神态,“过分”的举止,足可以假乱真。
“哎你!”眼下,这羞涩小姐经了我一喝,显然被吓到,双眼无辜而望,不知所以。
我心下暗自得意,窃笑徐徐,不怀好意的拍拍她的肩膀:“量身高了!一米五以下不要,你可要站稳哦?”边说着,边将手中尺子甩过,故意吓她。
到底是富贵人家的娇小姐,经不得吓。见我尺子飞过,不躲也不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只是无聊之中找趣,固而吓吓她,又未与她来真。见她哭了,不觉翻了个白眼,接着无聊的迈入了正题:“喂!我说量身高了,你到底量是不量?”
这小妞哭得更凶,转身掩着面跑了出去。
见此情景,我耸耸肩,会心而笑。毫不例外,每每那些受了我欺负、戏弄的小姐们,胆小些的,糊里糊涂忍了;略胆大些,便如出一辙的哭哭啼啼跑到爹爹那里告我的状。问明缘由之后,总也会惹得爹爹啼笑皆非。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一会儿,便有其她女孩儿找到我说,爹爹要我过去。
我点头应下,还不忘跳起,在她头上拍了一把,尔后,趁她尚且没能反应过来之中,借势将身跑开。
爹爹笑呵呵的看着我,他的身侧,站了适才那位被我加以戏弄,还在抹鼻子的小姐。
我也二话不说,学着男人的样子踱步上前,搭上爹爹的肩:“哎,又是哪个娇小姐怕我撒野?”语尽,开怀大笑起来。
爹爹不答我话,顺势一把摘掉我头顶的鸭舌帽,沉下声调,要淘气的我向她赔礼道歉。
我亦是不答话,微微莞尔,观那女孩子面目神情转换。
她一见,“翩翩美少年”头顶,盘着如云青丝美发,高高麝月,云鬓花颜,顿然会了缘由,破涕为笑。
不知是太过惊讶,还是容貌自愧不如我这假小子?脸颊越发羞红,纤指捂住,咯咯笑着跑开。
。
结束了一天的紧锣密鼓张罗,我和疲惫而兴奋的爹爹,一起往我们的家——白公馆里赶去。
“水伊”随着爹爹出了女学月门,走在熙熙攘攘,人流如潮的大街,爹爹突然唤了我一声。
“嗯?”我漫不经心应下,天真的仰起额头,等待着下文。
爹爹抚摸着我光洁如玉的纤纤素指,面目之上严肃而不失亲切:“你已经十六岁,是个大姑娘了。该收起那一身的野性,穿戴的同大家闺秀一样,准备读书了。”
“哦?要我丢掉男装,做回本来面目?”我反问回去,撅起了粉嘟嘟的小嘴。
“你本来就是女孩子嘛。。。。。”爹爹素来最怕我撒娇使蛮,无可奈何的辩白着我的言词。
我却不等他说完,果断的将他打断:“不,我要做男子汉!那些受人欺负的小女生们,我才不要做!”
“那你怎么不去男校读书,跟男孩子们厮混?”爹爹有些着恼。
“行啊!”我回答的干干脆脆,一双清澈如水的美丽眸子里,追捉不到一丝一毫后天的伪装。
其实爹爹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去。
幼时,还没有女校这一说。上学、做功课都是男孩子们的专属。女孩子呢?只好呆在家里刺绣、作画之类。
可我天性要强,比那些同龄女孩多一份铮铮然傲骨,自是不甘这般的。固此,上学,像男孩子们一样坐在光明敞亮的校舍里读书,一直都是我最为深切的愿望与追求。
我在这个家里排行第二,也是最小,上面有着一个姐姐。爹爹很疼爱我,巴不得把一切他能够到的东西,皆数收于我囊中。
可奈何,我却生不逢时。姐姐命好,到了就学的年龄,白家尚没有如今日般败落,爹爹思想觉悟又远远高于其他中国公民一筹,便花钱将姐姐送至美国留学读书。
姐姐才走没几日,爹爹便破了产。他并不是个肯轻易服输的人,仍在为了我日后能过上好的生活而终日在外劳苦奔波。他虽在乎我,但他的生意却很忙。回到家里,我所能做的便也只有宽慰与支持,哪里还能提这上学之说?久而久之,也便瞒了下来,直至今日。
爹爹听了我这话,苦笑着摇摇头:“水伊啊水伊,你为什么不是个小子呢!”
我黯然垂眸,理解爹爹的苦楚。此时,却也不由想到母亲,心里便是一痛,慌忙牵起爹爹厚实、温良的大手,急急赶路回去,不再言语。
。
白公馆坐落在上清寺一带中,一段幽静的深巷子里。古柏参差,落叶萧森。
这是一幢上了年纪的两层小楼,纯砖木结构筑成,雕窗画楹。最前端的八字门楼之下,朱漆大门井立。因了风雨侵蚀,已然有些斑斑褪色,但铜狮铁环仍可寻觅得到当年的华美,肃穆阵容。
老式的屋梁,陈旧的建筑,狭小的茶餐厅,凌乱的小巷。。。。。。都是重庆当代历史环境的真实写照。
楼宇后面,是一座小巧的苏州式园林,以半月形的低矮墙落围住。可赏,可游,可居。
园中,最大的看点便是借景与对景在中式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庭台楼榭,游廊小径蜿蜒其间,步移景异。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得以流畅、流通、流动。
透过一排排雕镂精细的格子窗,广阔的自然风光被浓缩成微型景观,浸染于眼眶之中,美不胜收。
外公在世时,曾做过陇西总兵,也就是青海都尉。这“白公馆”,便是爷爷为后世子孙遗留下来的祖业之一。
我的奶奶,也就是爹爹的生身母亲,因为是小的缘故,在杨家素来没有什么身份、声望。她是外公从陇西一带掠夺而来的农家贫寒女子,身世比不得那些名门媛淑,大家闺秀;却是长得极美。
自打进了爷爷家的门,便一直受嫡妻的嫉妒虐待,甚至辱骂鞭笞。
也正正因了奶奶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性子绵软、愚钝怯懦,才激起了爹爹那一颗济世扶弱的万丈雄心。同情弱小女性,发誓要为女性谋得福利,不再受着压制。
爷爷去世之后,父亲果断的从杨家孤立出来,在上海一处别院之中,安置好奶奶;身系一腔人世不平与求知欲望,远渡日本留学。
就在爹爹就读日本东京泓文师范学院的这一段日子里,奶奶亡故;我的母亲,可怜的母亲,惨遭大上海散落在各街角,防不胜防的“瘪三”们的摧残**,以至于投黄浦江而死。
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年,姐姐七岁,我三岁。
。
我唯一的姐姐白颜,自小性子文静,与世无争,典型大家闺秀风姿;而我却是真真截然不同。
大抵是受了终身征战沙场,做过总兵提督的爷爷隔代遗传的缘故吧!自幼好动不好静,总也爱女扮男装,同街头巷尾的男孩子们一道打闹、嬉戏。
父亲起先是摇头,后又叹气,眉头一日似一日皱得深了。
他怕我竟日以来只顾玩闹而学坏,便想了个办法,抓住我的喜好,干脆请了武术界的朋友教我功夫。小有所成之后,又将我送到上海国术馆中学习了三年。
待我毕业后,他却没能料到,我功夫上身,却越发的胆大开来,竟滋生出一个可怕万分的念头————为母亲报仇!
那时,我才十三四岁的光景,就已经时常女扮男装,怀揣一柄宝剑,出入于十里洋场之间的跑马厅、赌场、妓院胡乱闯荡,扬言要找到害死母亲的仇人。
父亲整日以来不断为我而担惊受怕,最终,为了我的安全与前途,于去年春天,辞掉上海的教职,携我回到这久别的山城,安身在白公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