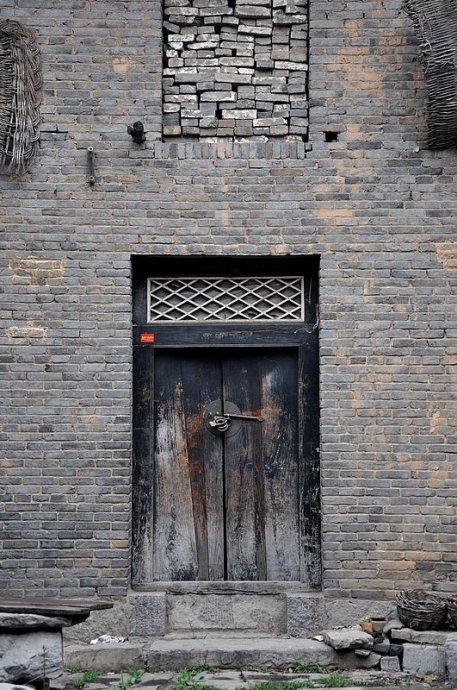包办婚姻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从崔菊被父亲用树勾打她就可以看出,父母在处理儿女婚姻上是带有私心的。
用自己的养育之恩,来压着儿女无条件的听自己的话。
他们抱着父母才是儿女婚姻的主导者这根大树不放,死死的掐着儿女相爱的颈部。
其实,对于儿女的伤害是无限的,也是无情的。
残酷历史记忆看似难以启齿,且是被受伤害者的柔弱体现。一代又一代的有情人难成眷属,一代一代匹配的婚姻被棒打鸳鸯,情理何在?
作者写文不是反对父母惩罚做错了事的孩子,而是反对包办婚姻。这座大山,已经压趴许多人,已经到了坚决摈弃的糟粕。
闲话到此,话归正传。
耳聪回家背着被子,随着辉叔佬准备往恩施州城出发。
一路的伙计很多,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有说有笑,把不愉快抛之于九霄云外。
正福,文华,正清,正兴,永胜,还有国清表叔。
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家里出发,过石心河,迈过三岔街。
由于车辆少,人又无钱,便亦步亦趋走到州城。
傍晚,城里照样冷冷清清,越走越远,越走越饿。
耳聪几天来萝卜在肚里少之又少,饥肠辘辘。
大过年的,人们还在过上九日,准备过元宵节。
可耳聪们却来到桂花树,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
摊开铺盖,就在早准备好的竹条板上扎营。十几个人挤一间地铺,其实,出门人就是如此。
早晚起床方便,裤子一搂就好了。一回来就坐着,抽烟也可以,还可以打牌。
出去不认识人,周围也没有好看的女孩子。
大家就赌香烟,一般都是打打“捎糊。”
上大人,邱已己,化三千,可之礼,佳作人——
可以喊门子,方式自己几个伙计定。喊门子必须口齿清楚,句与句必须连贯。
自己手里有两个同样的字,别人抓起来可以喊喷起,或者喷哒。如果自己手里有两个同样的字,另外一个字又是自己拿起来的就喊捎哒。
有时候运气好 ,有十几个门子。首先必须喊大糊什么?什么?又什么?
大糊,二圈,自摸是常事。首先得有十糊牌,然后才能足齐句子,一个字遇见另外两个其中任意一个,就是单钓。
大家都是一块的人,也是乡里乡亲。谁喜欢怎么打牌,爱怎么打牌,喜欢记那些牌。
牌桌上不分老少,不分男女。就分技术,只看谁有钱。
到处都是烟蒂,甚至铺盖都燃起来还不知道。
大家都是抽的九分钱的双杯香烟。过年都舍不得买大公鸡香烟抽,还是老价格,一角五。
每天都是;“日地日空气,挖土和奔泥。斗笠防雨来,吃的在肚里。”有的人技术不行,十分热爱打捎糊,每个月的钱都输得一干二净。
这个地方是州城的空旷地,原来有名有姓的金子坝,就是稻谷多,是一马平川。
如今变化成为桔苗圃,而且是州特产局办的种苗基地,成天车辆呼啸。
一众人有说有笑,热热闹闹,慢条斯理的,整整齐齐的在沟坎边讨论什么?
几个大汉,还有一个撅着嘴巴的小丫头。围着一位尖嘴猴腮,面部清瘦,爆着牙,眼睛却有神的男人说着什么?
那女孩子,时而把老陈喊过来,问这问那?
其实,老陈早已经过去了。就是几句话,又回来督促大家加油搞。
那一趴人,时不时又去池塘边瞧瞧,可能是在讨论水源问题。然后,一溜烟就走了。
都是风驰电掣,都是吉普车。那女孩樱桃小口,柳叶眉。着一身呢子外套,脚翘在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门框边,手放在嘴边,无聊的抖动裤腿。
像这样的场面第一次见过,号称一百多亩的基地,蔓延在许多地方,确实也名副其实。
从耿家坪到金子坝,桂花树的八斗丘才是苗圃中心。像沙河,旗峰坝都是附属基地。
好田好土都被征收了,三百元块钱一亩。农户都认为比春天载稻谷,秋天种油菜,或者麦子强许多。
到处都是挖土的,整田的。管家叫老陈 ,名志勇。声嗓特大,说话时喜时怒。走在又仄又松的堤坎上,屁股都在甩。
成天在工地来来去去,个子很高,很蒯,很会管理人员。
是舞阳坝建筑公司,总经理陈家齐的侄儿子。
颇高的身材,又颇有肉。看似都是平常喜欢喝啤酒的人。
不管天晴下雨都要把人撵上坡,下雨就掏沟,天晴就挖田。
反正不让你休息,即使瓢泼大雨。
一个月八十块钱,按月拿。
久而久之,大家都熟悉了。
在准备栽苗子期间,又来好好一批男女。又是年轻娃,高个子叫游明亮,小个子黄强。
还有陈总的姨侄叫卢昌松,也是龅牙,还有他二姐。
陈总的二姨侄女,昌翠。
许多苟枳苗运到工地,本来一天一个劳力,只能栽七八百苗子,陈老板看见却很着急。
就用包的形式,一粒一根,大量的招人。
开始大家还认真的做事,也没有什么不当,只是说发不了。
后来就慢慢变质了,漫山遍野都是栽苗人。有的人干脆背回家自己栽起来,乘人不注意一把一把地掩埋苗子。
管家老陈装着没看见,即使看见了屁股一挒就过去。有人尝到味道,慢慢的肚子更黑了。
下雨确实不能出去做事,老板陈家齐开会训话。脚翘得高高的,手举的平平的。一会指着这个怂几句,那个骂一会。
如演讲一般,滔滔不绝。
你们都晓得,恩施的橘子树七六年都死光了。我这苗子三年以后就是俏货,连浙江,福建,湖南都与我定有合同。
你们都看见的,手也动起来,指着那些去来的路口。州里的唐局啊!杨科长啊!都亲自督导,他们都是县团级额。
嘿!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不错,我会着重培养。
又客气起来,给每个人一支永光香烟。继续他的海阔天空 ,翘起二郎腿,习惯性一上一下。吐出的烟圈圆圆的,白白的,飞一会就破灭了。
看似烟圈很多,很大,密密麻麻。且有香味,一个个破灭。
经常开会表扬耳聪说;“耳聪你很聪明,好神搞,今后抽你去州畜牧局学习兽医,我准备在沙河承包几百亩土地,到时候我们两个搞,办大型猪场,你就帮我搞。”
你做兽医,比挖田挖土轻松多了。他的神情是认真的,也是有能力的。他的构想,期待逍遥子随他的心里走。
他夸赞耳聪,旁边的女孩子就一直盯着耳聪。炯炯有神,一眨一眨。
有事无事靠在门方的屁股柳来柳去,又是夏天,线条彰显无疑。陈总滔滔不绝,她小嘴兜得更紧。突然叉话二姨爹;“你别忘了我弟弟昌松额!”
滑溜溜的裤子,紧身的衣服姿态迷人,确实也算一位女神。
扯归扯,呱归呱。陈总胆子确实很大,看人也准。却是不会知人善任,眼睛并不独到。
他用昌松的姐姐两行泪,管理都归他。昌松爱搞小圈子,又无大志,对于苗圃利益不顾。
本来苗子需要间隔,需要淋水。为了赶工,一切抛开。
一个月左右,苗子栽完确实奇迹。那些水田的苗子东倒西歪,碗口大的泥巴压着针一般粗的苗子。即使成活,秧苗也会死气沉沉。
原来是栽稻谷的水田,一下子改为汗地本来就是一种外行。
苗小,草深,又用包工的形式安排活路。
一天下来是把大家差一点累死,可是苗子就更残了。
那年夏季,太阳晒屁股的日子,八斗丘简直就是火笼。耳聪便请假回家,看看爹妈。
妈妈不同以往,和颜悦色地说;“后山姑娘,芙蓉跑来家里找你,我说你去恩施了。她想上楼上你睡的铺上看看。”
又说“我很喜欢她,长得很好看,真的乖。”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乖的姑娘。
难怪你被鬼摸了脑壳,一天就喜欢她。耳聪就跟妈妈说,如同把心掏出来给妈妈看,就是想娶芙蓉做媳妇。
妈妈一下子就发火了,你又来了,“秀芝那门搞”?唉!
她那么勤快,一干干隔就打背猪草回来哒。又一干干隔,就砍一回柴回来哒。你就喜欢乖,乖吃的莫?我和你爹给你选的,你二天就好玩,你听见没得?
你看她,都跑这里来哒,找不到羞,还是姑娘娃,不像话。
秀芝昨天也来的,来哒就帮我砍猪草,饭都没吃就回去哒。哎!你说我喜欢那个?你说啊!我的个天,就喜欢些鬼花花。
耳聪好话说尽,妈妈还是不同意娶芙蓉这门亲事。
芙蓉也去过恩施,可就没有寻找到耳聪的身影。
耳聪听见很伤心,很伤心!伤心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妈妈不管耳聪同意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拿出一斤白酒,一包白糖,放在包袱上。
又去鸡窝,拿起几个鸡蛋,足齐十个,还放有两斤面条。
还是那根花布包袱,四角一搂,就栓好了。
“你听我的,秀芝要得,那门就不听话呢?”
又说;“找不到你回来,就这些东西,快去三姨家里看一看吧!秀芝几次都问你的。”
知道爹妈对于自己好,自己三岁时,吃了好多桃子,麦李,饿很了,把虫子都吃肚里去。
后来肚里许多小虫子,天天在肚里滚,逍遥子就像死一般的哭。爹妈成天到处找医生,大家都没有办法。
有一天夜晚,耳聪听见水响。原来是爹爹,三姨夫,还有荣生哥背着自己去万寨医院治病。踩着河流溅起水响,这样也不是第一次了,医生还是没有办法,又只能往家里背。
耳聪被放在堂屋铺着的门板上,妈妈与爹爹在讨论, 万一不行就只能像二妹一样。
妈妈又说,我们去二黄看看,哪里有一位医生很猫。
过了河,耳聪就睡着了。一会儿就到二黄医院,一位慈祥的医生,一看就知道耳聪得了什么病。早已经熬的有药,说这几年这种病比较普遍。
药到病除,就喊饿了。医生又把自己煮的米饭给与耳聪吃,又可以下地跳起来了。舅舅,舅母早知道,来到巨大的石头上看,妈妈就喊舅母,回去做点吃的。
那医生姓杨,大名鼎鼎,叫杨红秀,是位男医生。
杨医生解释说,每家每户孩子特别多,家里没有吃的,到处捡东西吃。耳聪属于桃子,李子吃多了。
又没有洗,小虫子就慢慢长大了,所以就像死人一般。
今天与妈妈争论实属无奈,又沉默一会,知道自己的一场病痛,从三岁多疼到五岁多,知道爹妈的苦与累。
仍然拒绝背背篓,妈妈又骂起来,每一句都是都很难听。
耳聪耳朵都快炸了,头很痛,很痛!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