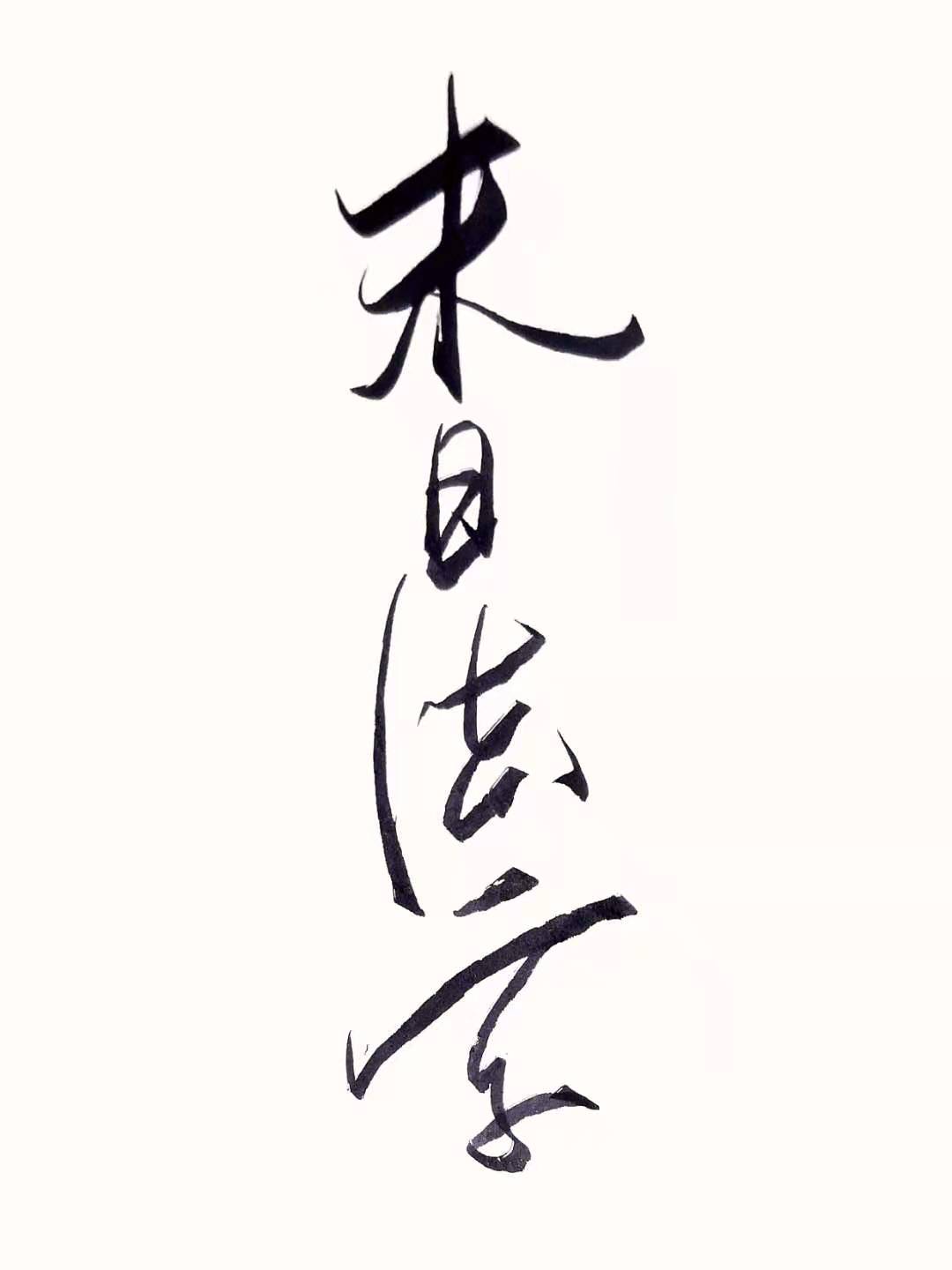海姨娘的棒伤算算时间,差不多该好了,看样子这母女两个耐不住寂寞,要借此机会出来蹦跶了。
没多久如意回来,愤愤不平道:“海姨娘也去。”
海姨娘惹了炎王府,只是吃顿板子,禁足几十天,这么轻易就被放过了,连如意都感觉到罚的太轻。
“果然如此。”严清歌冷静道:“如意,这次去庄子上,我们可要仔细点,只怕海姨娘被关了这段时间,心里有怨气呢。有什么情况,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如意答道。
严松年说走就走,大暑来到第二天,带着全家浩浩荡荡去了严家庄子。
严家家奴连老带小一百四十三户,五十多户在京城里伺候,剩下的呆在庄子上种田干活,家奴种不完的地,才租给京郊的佃农。
平时庄子上的家奴,日日要伺候田地,不得闲功夫,现在老爷一家忽然跑过来避暑,他们农忙之余,还得收拾屋子,拨人手伺候,一时手忙脚乱,对即将到来的严老爷一家,实在说不上欢迎。
严淑玉和海姨娘坐在一辆车里,车队一停下来,她就急忙跳下来,扶着海姨娘下车,叽叽喳喳道:“娘,我们到了!”
海姨娘只是被打了屁股,脸皮儿还是之前那样,姿容无损。加上休养了两个月,身上多了点儿肉,看着婀娜些许。
尤其今天她穿着掐腰宽袖上衣,和露出半个精致鞋面的裙子,头发妆容也都是仔细收拾过的,眼睛像长了钩子一样直朝严松年坐的车子看,旁人就知道她心中挂念着什么了。
严松年下车后,对上海姨娘含情脉脉的眼睛,看着她的那身打扮,喉头耸动,显然是想起来海姨娘的好,对她递过去一个微笑,海姨娘顿时得意的忽闪眼睛。
严清歌就当没看见这一幕,自顾自去了庄子上,叫下人领她去房间里。
严家的庄子盖得村土风味十足,原就不是为了给主子们住的,房间低矮,院子狭小,能避什么暑?反倒比京里头还热。
如意在外面看着下人把严清歌的行李搬过来,一阵儿的收拾屋子。严清歌搬了凳子,坐在树底下的阴凉里绣花乘凉。
过一会儿,如意出去打水,准备回来再擦洗一遍房间,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体态结识的农妇。
这农妇大概四十多岁,鬓角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见了严清歌就跪在地上磕头:“奴婢余赵氏,见过大小姐!”
严清歌听这农妇自报叫做余赵氏,想了想,问道:“你和余花儿什么关系?”
余花儿就是被她叫做泥巴的那个丫鬟,后被海姨娘母女下毒手弄死,伪装成投井。余花儿的父母来认领尸首时,哭的好不凄惨,严清歌听到,叫人送去二十两银子。
那农妇立刻红了眼睛,道:“是,奴婢就是余花儿的母亲。”
她好好的女孩儿送进去,才两天,变成冷冰冰的尸首抬出来。就算她再眼拙,也能看出余花儿脸上的青肿是被人打得,而不是在井里泡的。她将海姨娘杀女的仇恨,牢牢的记在心里头,日夜受着煎熬。
知书、达理被海姨娘收买,在庄子上不是什么秘密,这两人被放回来以后,偶尔也说起来一些京城严家的事情,余赵氏一一记在心里,其中就包括海姨娘母女和大小姐关系很恶劣这一条。
严家全家来到庄子上,余赵氏立刻寻摸了机会过来,给严清歌磕头。
严清歌知道余赵氏心中所想,淡淡道:“你起来吧,你所求的事儿我明白,只是有些人暂时动不得。还请你回吧。如意,给赏,送客。”
余赵氏拿了赏钱,惴惴不安的出去。她也知道海姨娘势大动不得,不过听大小姐的语气,似乎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
晚上时分,如意忽然进来道:“老爷今晚留在海姨娘处。”
“留就留吧。”严清歌没放在心上。
如意挑了灯花儿,忽然道:“不知道咱们严府里的小少爷,将来是莺姨娘生的,还是柳姨娘生的,不管是哪个,总比海姨娘生的要好。”
严清歌笑她:“如意这小脑袋整天总想那么多。别看莺姨娘、柳姨娘现在听我话,为母则强,真生下来严府小少爷,可就不好说了。”
“小姐不是有她们卖身契么,怕什么?”如意道。
“一张卖身契能顶什么用。知书、达理还不是家奴,一条命攥在严府手里头,还敢背主。有些人是天生的破落户,越是什么都没有,越是能糟践自己,不把自己的命当命的人,是最凶狠的。”严清歌叹气道。
如意不是很开心道:“我今儿见到知书、达理了。他们俩看着白白胖胖,比在府里养的还好呢。因为伺候过老爷,虽然是犯了错打发回来的,可是旁人还是把他俩尊着宠着,简直是这庄子上二老爷、三老爷了。”
“海姨娘还能用得到他俩,当然不会叫他们吃苦头。”严清歌道。
主仆两个闲话一会儿,就准备去睡了。庄子上没有蜡烛,点的灯是小盏油灯,光线弱,看东西费眼睛,严清歌索性早睡早起。
半夜时分,严清歌睡得迷迷糊糊的,总听见一阵阵翻来倒去的动静,似乎是什么东西在屋里头窜动。
如意也听见了,两个人起来找了半天,没发现有东西。熄了灯,一会儿那窸窸窣窣的声音又响起来,好不恼人。
如意苦恼道:“小姐,你睡吧,我点着灯看着,有人就不会有那声音了。”
严清歌摇摇头:“兴许就是几只耗子,碍什么事儿。明天使人把屋里的家具和箱笼都挪开,堵住洞便好了。
就这么给吵了一夜,主仆两人盯着没睡好的黑眼圈,早早起来。
如意去叫人帮忙往外抬家具找耗子洞,院子里忙的热火朝天时,海姨娘扭着腰身,夸张的走进来,一进门,就用帕子捂着脸,道:“呦,这是做什么。弄的乌烟瘴气的。”
严清歌冷冰冰道:“只是堵几个耗子,海姨娘在自己屋里呆着就是,难道心痒难耐,要来多管闲事么?”
俗话说得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海姨娘听出来严清歌是骂她,脸色青白,生气道:“我好歹是你半个长辈,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叫你这边清静些,别吵了人睡觉,老爷还没醒呢。”
严清歌竟是笑出来:“一个妾也敢大口小口说自己是长辈。”背过身不再理她。
海姨娘恨恨的盯了严清歌两眼,嘴里低声不知道嘟囔了两句什么,满脸狰狞的走开。
严清歌住的那屋子里,的确发现了几个耗子洞,着人用糯米水调了黄泥,将洞堵上,没多久便凝固上。家具东西被抬回去,来干活的家奴道:“好了,今晚大小姐就不会觉得吵了。”
严清歌给过赏银,谢了他们,才回到屋里。
中午吃过饭,知书、达理走进来,穿着崭新的袍子,道:“大小姐,老爷今天兴致好,叫大小姐出去坐船游玩,软轿已经备好了,就等大小姐过去。”
从庄子出去三里地,就是灞河。灞河泛舟,的确是很好玩的。去灞河这段路,男人可以骑马,女眷则坐软轿。
知书、达理以前没少在严松年耳朵边为海姨娘说话,惹了严清歌不是一回。他俩被贬斥回庄子,便是因为偷严清歌的帕子,现在长了狗胆,还敢来她这里通报消息。
想必是是严松年好了伤疤忘了疼,乍一看见这两个用了多年的“忠仆”,又起心复用了。而昨晚海姨娘吹的枕头风,估计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严清歌坐在上首,任他们跪在地上通报完,半天也不叫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悠悠道:“要是我说不去呢?”
知书、达理心里发憷,继续跪着,不敢跟她顶撞。严清歌冷笑一声:“滚吧!”他们赶紧退了出去。
如意担心的问严清歌:“小姐,老爷来叫,咱们真的不去么?”
“去!”严清歌站起身:“衣裳也别换了,就这么走吧。”
幸好因为在庄子上,严清歌常见到外人,所以衣服都穿的很规整,不用换也不碍的,就这么出去,倒挺合适。
严松年看见严清歌过来,一副慈父面孔,关切的问她:“我听知书、达理说你不想去,恐怕是你是苦夏,怎么又过来了。”
“父亲不知道么?我住的屋子里有耗子,昨天闹了一夜,今早上叫人堵耗子洞,这才忙完。幸好父亲还没走。”
“竟有耗子?也难怪,这是庄子上,不如家里清静,你先委屈几天吧,天气凉了我们就回去。”严松年道。
“是呢。海姨娘早上也是这么说的,嫌我找耗子洞打搅她睡觉。好奇怪哦,她又不是耗子,我堵洞怎么会吵到她。”严清歌表情娇憨的告了一状。
旁边海姨娘气的直揪手帕,严松年呵呵两声,没有多说,叫抬轿子的人启程,带他们去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