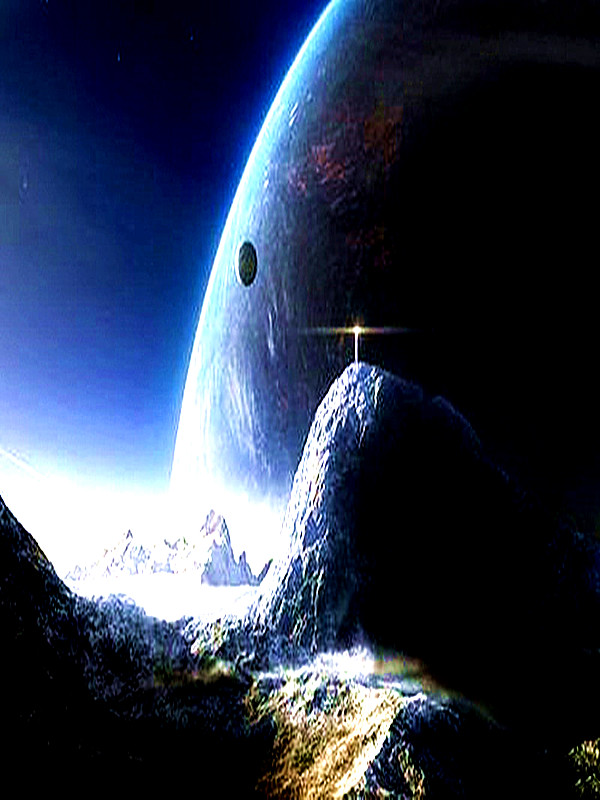青瓷茶杯里,香茶散发着袅袅热烟,扑鼻的香茶味道,在这间不算大的屋子里弥漫。
茶香,春好,日暖,正是品茗的最好时机。
但客人却丝毫没有品尝香茗的心思,一门心思的要离开这个地方。
身为半个主人的严清歌,戏谑的打量着严淑玉。她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将严淑玉的那些勾当说出来,只要点到为止,让严淑玉有所忌惮就行了。
因为她发现,看着严淑玉自己往死里作,比她亲自动手,竟是舒畅多了,似乎老天也在帮着她惩罚严淑玉一般。
严淑玉心惊胆战,在严清歌处呆了半个多时辰,慌慌张张告辞了。
回到储秀宫后,严淑玉回到房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伺候她的宫女流晶就走进来,道:“主子,殿下请您过去。”
严淑玉脸色难看,她离开前,太子交代过她一些事情,但是,她一件都没有做到。
但是,在宫里面,太子就是她的天,太子来叫,不得不去。
她收拾了一下衣裳,敛神静气,才道:“我换过衣服就去。”
严淑玉换上一身淡青色的简易宫装,头上的钗环一样不剩卸下来,只将头发挽在脑后,素面朝天,朝太子住的屋子去了。
太子正坐在案几后,处理着许多奏折,自从回京后,太子处理朝中事物,再不遮遮掩掩,遇到难以决定的事情,还会自然而然的召见朝中大臣到储秀宫商讨,皇上对此半句都不曾多说。
而此前风头大出的二皇子,再也没有人提起。二皇子和静王所做的那些事情,罪无可赦,但是,到现在,也没见有人动二皇子和静王。
私底下有种说法,静王挟持了年幼的五皇子和素来低调的四皇子,若是皇帝敢对二皇子和静王府下手,静王就让皇上这两个儿子陪葬。
五皇子倒还罢了,他和静王和二皇子血脉相连,但四皇子却不同。
四皇子是容贵妇的儿子,地位还在候妃之上,虽然并不讨皇帝偏爱,可是玉妃出身千年士族的顾家,祖父、父亲、伯伯、哥哥,以及外祖父、舅舅等等至亲的家人,全都在朝堂中占据一席之地。
她本人也非常会做人,在宫内交好各宫之人,且将四皇子养育的非常妥帖,即优秀,又没有争权夺利之心,比起平庸的大皇子,和总是惹是生非的二皇子,好到了不知哪里去。
四皇子若是被牵连丧命,别说顾家不答应,皇上的儿子们,也会只剩下不堪其用的大皇子和体弱多病的太子了,整个朝堂也不会答应。
投鼠忌器,两项僵持,说的便是眼前这种情况。
太子的身后,一名姑姑安静的站着,像是一尊雕塑一样。
见到了严淑玉,她才抬起眼睛,对着严淑玉轻轻示意,让她不要惊动太子。
严淑玉站的腿脚都麻了,太子才终于在奏折堆成的海洋里抬起眼睛。
他对着严淑玉看了两眼,对她招招手,温声道:“到我跟前来。”
本对太子的冷落暗恨的严淑玉,心情霎时明朗起来。
她维持着平静的表情,心里的盘算却越来越多,轻步到了太子跟前。
是的,她是被欧阳少冥坏了身子又如何,但欧阳少冥现在生死未卜,只怕早就被草原上的狼群吃了个干净。
太**里面,现在只有一个压根不受宠的水英。据说,当初的宫难,侯晶晶、元芊芊和其余太子的女人都没逃出来,太子现在对她态度好,岂不是代表着,她有机会翻身了!
严淑玉心里的盘算只在一瞬间就成了型。
装成处子,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一袋鸽子血,和几两明矾,就是堂院里有经验的茶壶来了,也辨不出真假。
严淑玉越想越是激动,差点维持不住脸上的神情。
太子看着严淑玉那张脸,慢慢道:“母后那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明日你再去吧。”
严淑玉跪地磕头,道:“婢妾辜负了太子殿下的期望,明日婢妾一定不会让殿下失望。”
太子缓声道:“你很聪明,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的。下去吧。”
出了门儿,严淑玉回到自己住的殿门口,却不进去,而是抬眼看向天空中高高悬挂的太阳,阳光刺目,一瞬间就照的她满眼都是泪水。
她心里的茫然却都没了,那太阳不管多刺目,总有一天,她会将它攥在手心的。
回到屋后,严淑玉唤过流晶,问道:“流晶,你今年多大了?”
流晶是她随太子回宫后,新分给她的宫女,之前伺候她的那几个宫女太监,都已经在战乱中无从找寻了,可恨她花了大价钱才收买的人,竟全打了水漂,现在又要从头做起。
流晶对严淑玉不甚了解,因是主子问话,很快就将自己的一切兜底告诉了严淑玉。
她家是小富之家,还是家里唯一的独女,但是说了三家亲,都在成亲前遇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事情,被男方退亲。流晶的老爹一怒之下,决定养女儿一辈子,这时候,宫里面来人采选宫女,一个老算命的告诉她爹,让流晶进宫做几年宫女,叫宫里贵人们的贵气带一带,二十多岁被放出来时,身上的晦气就没了,便能嫁个好人家。
听完流晶入宫的缘由,严淑玉已经有了计较,这个流晶看来挺容易收买的。
但是,她并不急在这一时,转过脸去说别的了。
晚上,待流晶睡着后,严淑玉躺在黑暗中的床上,轻轻的将手伸到木头大床的雕花下,细长的指甲扣了半天,吊出来一根细细的棉线,她轻轻的拉扯着棉线,终于,从棉线的尽头拉出一包比指甲盖还小一些纸包。
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这东西竟然拿还没丢!这下,她的仰仗就更多了些。
轻轻的打开了那纸包,一股清甜的梅花香味,在空气里飘荡,严淑玉将那纸包收了起来,带着得意坚定的微笑入梦而去。
严清歌屋里,她却是怎么也睡不好,今晚守夜的是碧萦。
碧萦年纪小,人不比碧苓那么大方,话也不多。
严清歌觉得碧萦应该没有碧苓那么难打发,便柔声道:“碧萦,不如你去和如意换换,叫她来守夜,我习惯了她陪着我。”
碧萦摇头道:“哪里能麻烦如意姐姐。碧苓姐说了,如意姐姐从宫外来,不比我们耐熬,加上还要伺候小姐您的衣食住行,出不得岔子,晚上守夜的事儿,我们两个轮流做就好。”
这碧苓果然肠子比较直,几句话就给严清歌透露了不少信息。
看来,真正听令于皇后的,是碧苓,而碧萦听的是碧苓的话。
有了这一层认识,严清歌心里好受了些,她笑起来,坐起来,拍了拍床沿,道:“碧萦,你坐下来,陪我说说话。”
“奴婢不敢坐,主子想问什么,奴婢回答您就是。”碧萦跪在踏板上说道。
严清歌在宫里面做过秀女,知道宫里规矩大,奴婢的头不能比主子高,她逼着碧苓坐,反倒是害了她,也就算了。
越是凑近了看,严清歌越是觉得碧萦的长相熟悉,她和碧萦闲话几句,电光火石间,忽然醒悟过来:这碧萦的长相,和她未出京之前,竟然有五成相似。
以为她不爱照镜子,所以对自己的容貌竟是并没有那么熟悉。要是换了个跟如意或者严淑玉面貌有几分相似的人,她立刻一眼就认了出来。
她放缓了口气,轻声问道:“碧萦,你识字么?”
“识的几个字!”碧苓回答。
“哦,是谁教的你呀。”
“小时候被娘教过几个字儿,倒还记得。”
“你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的?”严清歌问道。
碧萦犹豫一下,轻声道:“奴婢是罪奴出身,父亲有罪,家里被抄,本来在浣衣局做事儿,幸得皇后娘娘垂帘,才叫碧苓到凤藻宫伺候。”
严清歌精神一震,问道:“碧萦,你原来姓什么。”
“奴婢……奴婢忘了。奴婢进宫的时候才八岁,前面的事儿都不记得了。”碧苓低头说道,半句都不肯多吐露。
严清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她打量着碧萦的脸,算了算时间,六、七年前谁家犯事儿被抄,她还真的想不起来。
但是,有一件事她可以确定,这个碧萦,绝对是皇后有心安排在她身边的。
严清歌心里苦笑,皇后可真是用心良苦,如此一来,太子若是非要召见她,见到了今非昔比的她,和与她之前有几分相似的碧萦,只怕就要移情于碧萦了。
这种被人赤裸裸摆在明面上算计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可是,严清歌又不能不做。而且,照着皇后这计策,太子若是能放下她,对她来说,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她在心里叹口气,面上却是不显,对着碧萦笑了起来:“说着说着,我就有些困了。我们睡吧。”
碧萦乖巧的应了一声是,扶着严清歌躺了下去。
桌上的油灯被碧萦吹灭了。看着黑乎乎的帐子顶,严清歌怎么都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