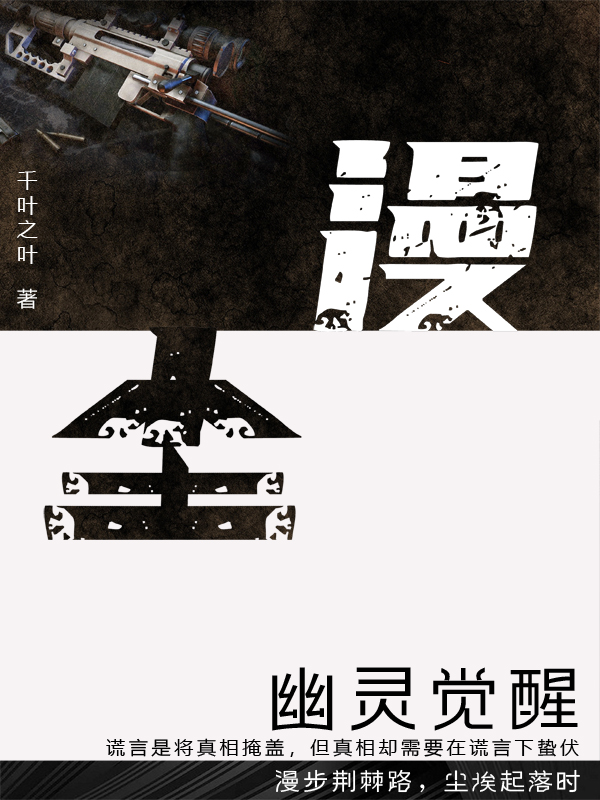刚开学的九月,冷风刮得有些许清凉,温暖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
地理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讲着月考卷子,并试图用他那略带磁性的声音震醒睡眼惺忪的同学;但从讲台上一眼望去,依旧有几个学生趴在桌子上。老师无可奈何地走下讲台,吓得近处几个人立马板直身子,像是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我瞟了一眼林子欣,她看着窗外发愣,老师不知不觉走到她身边,敲了敲桌子。
“林子欣,说说北海道渔场的形成原因吧?”
她好像被这突然到来的问题打搅到了,站起来许久也没有回答,老师接着把目光瞟向我
傅文,你来讲讲。”
虽然我也属于不听课梯队的一员,奈何我在地理层面高深的造诣,这种问题当然是毫不费力地解决的。老师点点头笑了,有点老父亲老怀安慰的意思。
“林子欣,要多向你同位学习啊,看你也回过神了,认真听讲,坐吧。”
一阵微风吹过,她飘逸的长发拂过腼腆的脸颊,我看到细小的绒毛在光影里舒展。心动,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
林子欣,我分班后的第一个同桌。在物历地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选科分班里,和一个女生同位是如此“珍贵”。她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有点黑,成绩和我差不多烂,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走进了我的世界。
“写什么呢,傅文?”她那双水灵的大眼睛凑到我脸旁,我手忙脚乱地合上本子,生怕秘密被她发现。
“别藏了,我看到了,写的歌么?这么好的文笔不和你同桌分享?”
“写的也不好......”我不情愿地把本子递给让她。
“哇!傅文,你就叫情歌小王子吧,文采都快媲美我了,给你看看我的。”
没想到她也挺自恋的,我接过她的本子,一首首富有节奏感的说唱映入我的眼睛。
“挺像法老的风格。”我开玩笑的说。
“你也不错。”
“哈哈哈,彼此彼此!”
于是我们开始不断写歌,她写一句,我接一句,不知多少个自习和课间就是这样度过的。
共同的话题让我们突然就熟悉了起来,我开始在意她的想法,开始在人群中找寻她的身影。大脑里心脏里血液里联合分泌的苯基乙胺和多巴胺,让我红光满面,手心微汗。
高三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的早,也下得更大。从窗户里望去,漫天雪花像春天的柳絮一般不停地飘舞着,整个校园,成了童话般的银白色世界。高高低低的松枝上,都托着大大小小的雪团,风一吹,又飘落到地面上。
在班长阿瑞的带头下,我们冒着大雪奔向厚到没过半个小腿的操场,大家抓起雪,搓起雪球打雪仗。林子欣怕被“误伤”,还带上了一个小棉帽子。我刚搓起一个雪球扔向阿瑞,突然就遭到了偷袭,转头一看,林子欣笑着转头跑走了,我追了过去,林子欣回头冲我笑,我跑到她身边,她没有说话,我也默不作声。她的小绵帽上落了层雪,我轻轻拍了拍帽子,她回头瞪了我一眼,嘟了嘟嘴。可能因为天气的寒冷,她脸颊冻得红彤彤的,睫毛上像结霜般晶莹剔透,云层渐渐散开,几缕阳光趁机从零零散散的云层间隙中射下来,原本只看灰和白的世界瞬间变得澄澈,仿佛每一枚雪花都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一枚雪花慢慢飘落到我的鼻尖,它在我鼻尖渐渐融化,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虽然雪花融化很冷,但我知道是我这颗心融化了雪花。
高三的生活很艰苦,不用说那堆积如山的书本,也不用说那映在窗前苦读不倦的身姿,更不用说那从早到晚被各科老师填满的课表,光是那写不完的作业就够让人刻苦铭心。
黑板上倒计时从三位数到两位数再到个位数,老班喊我们下去拍毕业合照。我故意挤到林子欣的身后。刚刚站稳,摄像的老师就问我们:
“奶糖甜不甜?”
我们开心回答“甜!”
在高中的最后一节课,老班一走入教室,就看到黑板上写着 “亲爱的老班,全体同学向您申请永远请假,请您批准!”
老班简简单单写了三个字“不批准”。
那节课我们都放下了卷子和笔,畅聊了高中三年一次次难忘瞬间,我把写歌的那个本子送给林子欣。
“留个纪念!”
她也微笑地把她那个本子送给了我。但最终,我也没敢说出来“我喜欢你”。
高考结束后,我如愿考上了本地的一所重本,而我与她却再也没有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说唱比赛。我拿出之前林子欣送我的那个本子,翻了翻,无意间看到最后几页塞了张纸条,小心打开,上面写着——
“还记得北海道的鱼场是怎么形成的吗,当千岛寒流遇上日本暖流的时候,会温暖整片海域,就像我遇见了你。”
原本以为我和她可能就这样错过了,参军第二年的时候,部队调防,到了南方,经历两个半月的魔鬼训练之后有两天自由外出的时间,说巧也巧,我和王凯、韩雷吃着麻辣烫,隔老远就看到一个那么熟悉的背影,她突然回过头,那种感觉,哎说不出来,反正之后就把她追到手了呗。
一阵呼噜声打破了美好的回忆,刘鸣和董旭不知什么时候早睡着了,行啊,你们俩,等以后再教训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