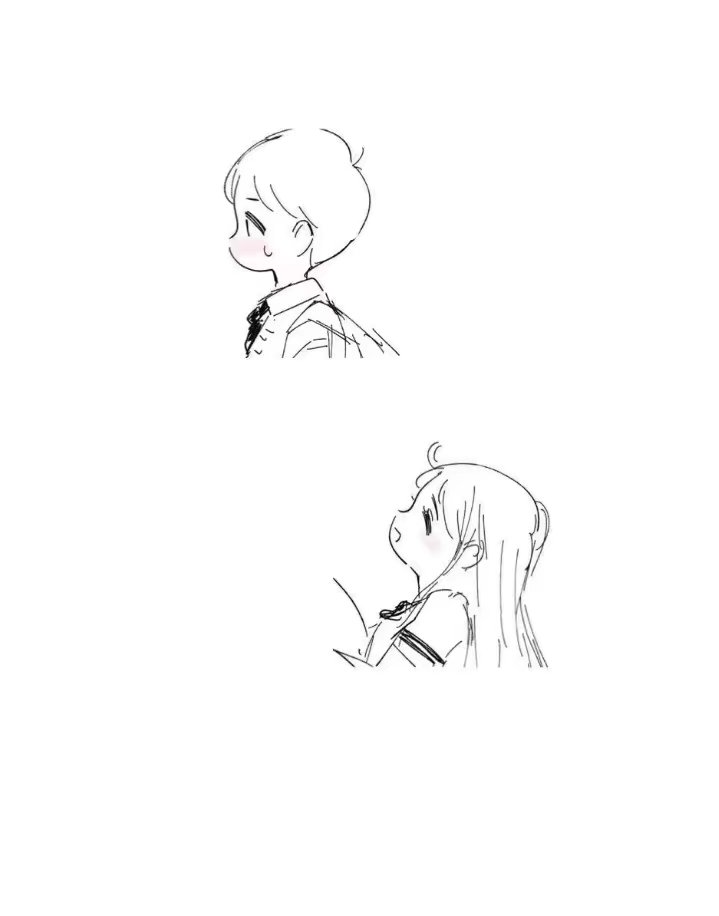“快点,磨磨蹭蹭的。”
药店的老板今天的心情似乎不太好,秦飘陵自从那晚外出给客人送药回来后,整个人就好像变了一样。
连一向对秦飘陵宽容的老板娘近来也逐渐耗掉了耐心。对着秦飘陵毛手毛脚的行为逐渐从开始的理解变成了不耐烦。
“飘陵啊,你最近是有什么心事吗?”
在晚上宵禁后老板娘端着一盏茶点来到了秦飘陵的房间。
夫妻俩膝下无子,又多年前灾荒逃到了这个地方,凭着家传绝学的医书白手起家开了这家医药馆。
八年前,当时才刚刚二十出头的小秦娘子和丈夫刚刚来到京城,打算现在破庙中将就住着,等天亮就去找工做,即使是苦工,在京城中至少是可以包吃住的。
两个人当时的盘缠只剩下了最后的、不知道已经在怀中捂了多少天已经硬掉的烧饼。
秦宇小心翼翼地撕掉边缘已经发黑发白的坏地方,生怕多撕了,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掰开,把小的那份留给了自己。
他们就是这时候看到的秦飘陵。
小孩子衣着华丽,身上不染尘灰,眨巴着眼睛看着夫妻二人,一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模样。
此时已经不早了,又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破庙中,小秦娘子一下就意识到了这个小女孩跟家人走丢了。
于心不忍的小秦娘子走出破庙,在小女孩面前蹲了下来,小心的询问着小女孩的姓名,生怕小女孩面对陌生人会有不自在。
不料小女孩不仅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向前了一步,一下子钻进了小秦娘子的臂弯中。
小秦娘子心生欢喜,转过头看着秦宇,秦宇走上前来,正好听得小女孩的肚子咕咕的叫,便顺手掰了一块馍递给了小女孩。
“什么呀,你看这个小姑娘穿的这么华丽,怎么可能吃得下去这种硬掉了的饼子。”
话音还没落,小女孩一嘴咬了下去,还冲着小秦娘子笑,小猫一样的眼睛微微上扬,黑色的瞳孔看下去仿佛一汪清水,小脸蛋红扑扑的。
就这样,夫妻二人决定今晚先带着小女孩在着破庙中借宿一晚,等到明天小秦娘子带着小女孩去街上问问能不能找到家人,秦宇则去看看哪里能找到工,虽逃亡前也是半个名门望族,但既然事情已经如此,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
秦宇非常顺利的就找到了一个搬运货品的重体力劳动活,只是作为江南一带名医家族的公子,对于这种重体力劳动实在是有点有心无力,即使也曾苦练过几年的武功,但那跟这个比起来性质可完全不一样了。
秦宇略显勉强的背着身后的大米,往雕梁画栋的饭厅厨房运送着物资。别人一下子能背起三袋绰绰有余,而秦宇两袋已经废掉了大半力气。
监督的小生一脸鄙夷的看着他,暗戳戳的想,这下克扣你的工钱总是没有什么不妥了。
秦宇推着运送的小车从后门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试探性的叫了一声,秦公子。
“刘叔?”
对于深宅大院的孩子来说,对于见过的各家叔叔婶婶的脸和名字对号入座是一项必备技能。
自从表叔被冠以勾结朝廷重臣,意图造反的言论面众以来,对于秦家人,各家是唯恐避之不及,这一代行医行善盘踞一方的百年招牌,竟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
没想到,来到了京城这种重地,竟然还有人会主动跟自己搭话。
在集市中抱着小姑娘到处询问,希望能够找到她的父母的小秦娘子累的满头大汗却始终是一无所获。
曾经“偷师学艺”的刘叔在京城开了家药店,算不上富裕,但勉强度日绝对是够了,只是学艺不精,太受局限,要非说刘叔是个好人倒也无可厚非,不过更多的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小药铺。
所以当刘叔看到秦宇的瞬间最深刻的感觉是药铺有救了。
事情的发展也确实验证了刘叔的看法。
药铺的生意逐渐好转,扭转了当初要依靠刘叔的人脉才能卖出点养生药物,仅能供应药铺的日常运转。
如今已经靠药铺富甲一方。
小姑娘逐渐长得亭亭玉立,说是学徒,却一直是按亲生女儿的标准养着,想着将毕生绝学都交给她,这大概也能理解为什么秦飘陵突然有了转变之后,二人的态度如此急躁。
秦飘陵确实也委屈,或许,应该说媛媛,一个绝对的千金小姐突然沦落为一个小小药铺掌柜的养女,还不得不亲手熬药配方。
“飘陵啊,虽说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一直把你看作秦家的接班人的,师母理解你有压力,才会大晚上晕倒在了药铺门口,我们能给你足够的时间修养,但是你也不能太让我们失望不是?”
小秦娘子浑身散发着母爱的光辉,可奈何现在的秦飘陵虽然在严府确实修习过药理知识,但那点皮毛,对于这种世家大族传承下来的各种细节就实在无计可施了。
秦飘陵只想着赶紧回去,赶紧回到自己的家。
母亲和三姨母还有哥哥们看到自己现在这番模样,不知道要有多心疼了。
想到这里,飘陵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但小秦娘子却更觉得她的无理取闹。
“如果只是因为不想嫁人,你就这样的话,那大可不必。”秦夫人佯装生气,只盼望能够镇住飘陵,小本生意,即使在舍不得这个女娃娃,又怎么斗得过那个出了名的纨绔,严子铭。
是啊,这么多年的浮沉,秦家夫妻已经逐渐学会了圆滑处事,再也不会出现刚刚接任时候那种意气风发,为了自己所坚信的无论付出什么都在所不惜,他们称这为成长。
飘棱也不是没想过反抗或是逃走,知识不管是镜中自己的面庞,还是深夜秦娘子望着月光的背影,都让身为受害者的自己觉得有所亏欠。
她知道二人的苦衷,所以也并没有多说。
毕竟,差点被毁尸灭迹的自己,就是被这个自己只知道姓名的女子所救啊,她又怎能忍心让她视为亲人的二位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