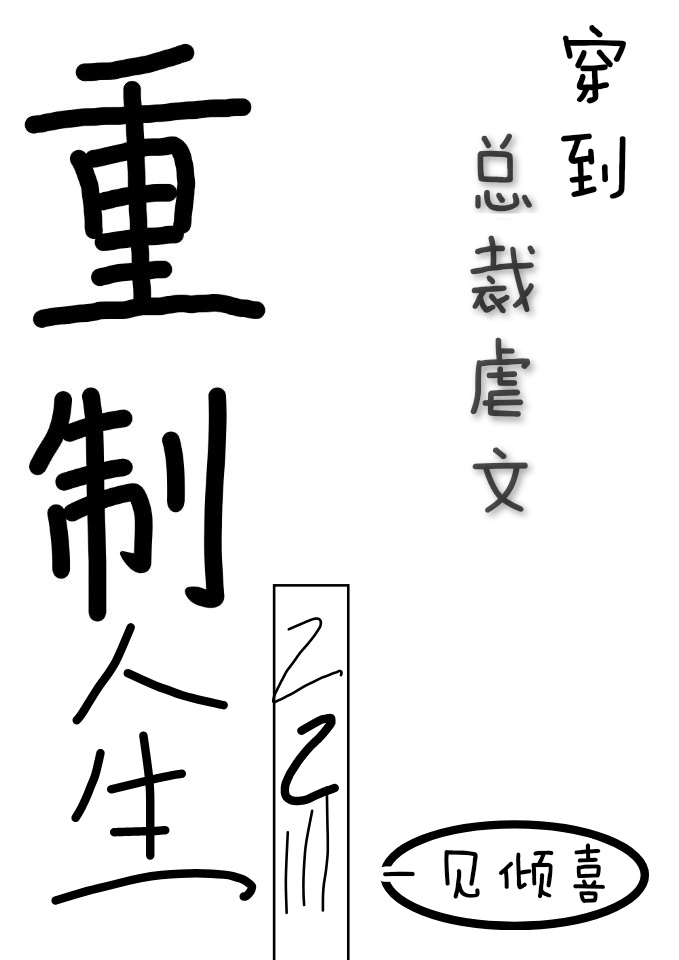春天来了,桃花红了,梨花白了,一群蝴蝶围着这片花丛飞来舞去,有两只飞着飞着就叠在了一起。桂芬打开房间的东窗,迎着暖暖的阳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群煽情的彩蝶,看着看着就想到了李国梁,就联想起他俩也曾像这两只浪漫的蝴蝶,时常出现在古城的角角落落,想着想着桂芬的眼角就红润了。
女佣小梅站在不远处见桂芬黯然神伤,想过去问问缘由却又不敢走近问,就故意把手里的活弄得响声很大,目的是想分散一下桂芬的注意力,好让她神情回归到自然。可是桂芬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趴在窗台上静静的看着想着,不时还用手撩一下被风吹乱的长发。
“今天的阳光真好,三少奶奶,我们出去走走吧。”小梅见手中的响动对精力集中的桂芬没起效果,暗想片刻又凑近桂芬找个话题。
桂芬这才转过脸,微微一笑,“好吧,我也正想出去透透气呢。”
主仆两人走出家门,来到人烟稀少的街道上。虽然说陈寿山奉左田之命劝回了一些做生意的人家,但街面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繁华的景象。桂芬跟小梅沿着萧条的青石街道毫无目的地边走边说,不经意就走到了李国梁家的杂货铺子门前。这个地方桂芬并不陌生,小的时候她常随李国梁来玩,每次过来李家伯父母都要把店里好玩好吃的拿到桂芬面前随她挑,后来大了,读书了,来的就少了些,因为那个时候李家伯父母再看桂芬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都与以前不同了,大有来了就不舍得她离开的意思。
现在,既然走到了这个地方,桂芬就不能不停下脚步去看望二老一眼。桂芬走近门前一看,大门上了铁锁,桂芬心想,二老恐怕外逃还没有返城做生意呢。桂芬站在那儿这么猜想的时候,一个中年妇人走过来疑惑的问:“你们这是……找人吗?”
“哦,是路过。想打问一下,他们家的人呢?为什么至今还锁着门?”桂芬反问。
女人回答之前小心的四周看了看,见没啥人就凑近桂芬耳边小声说:“唉,你们怕是不知道吧,这家人惨喽,灭门了。老两口因为儿子当了抗日的兵,也被当作抗日分子给杀了,听说那个当兵的儿子也在前段时间的池水大战中战死了。天老爷呀,这么一家子人呐说没就没了,绝户了。”
听完中年妇人简短的叙述,桂芬就觉着眼前一黑,一阵晕眩差点倒下,幸亏小梅伸手及时扶住了她。桂芬捂住嘴巴,强忍着没让自己哭出声,她被小梅搀扶着踉踉跄跄的往回赶,一路上,她耳边反复回响着从那个女人嘴里吐露出来的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这个噩耗似乎要炸破她的耳膜和脑袋。从李家杂货铺子到陈家大院其实也没有多少路,可桂芬却觉得很漫长,仿佛用尽她毕生的力气才走完那段路。
回到家,桂芬一下就躺坐在老式藤椅上,神情恍惚的眯着眼,似乎想睡。小梅端过一杯茶水放到桂芬手边的茶几上,轻声对桂芬说:“三少奶奶,喝点水吧。”桂芬好像没有听见,或者是听见了没有力气回话,她用手示意了一下,让小梅就放在那儿,自己翻动了一下身子,换了个姿势继续眯眼躺着。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男人无力的叫喊,桂芬迷迷糊糊听出是父亲在喊,她便硬撑着身体来到院门口,只见父亲趴在门框上,沮丧着脸带着哭腔说:“桂芬呀,你妈她……她……死了!”
原来,桂芬妈昨晚在陈家赌场玩到半夜,手气不错赢了不少钱,趁着手里有钱,她又躺到陈家烟馆美美的抽了几锅大烟,之后便梦幻般的眯到天亮。清晨,她穿着紧身的红花旗袍,扭着并不性感的瘦臀走在空寂的街道,刚好一群早间巡逻的日本兵从她背后走来,大清早就有这么妖艳的女人在他们眼前晃悠,一个个被撩得放大了瞳孔,都兴奋的叫开了:“花姑娘!花姑娘!”
桂芬妈听到身后有人呜哩哇啦的叫喊,回头一看,是群巡逻的日本兵在她身后紧跟着。桂芬妈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但她能意识到是冲着她来的,便恐慌的加快了脚步。鬼子见桂芬妈想逃,也加快了步伐,边追边喊:“你的,站住!花姑娘的站住!”
桂芬妈这回听清楚了,她知道小鬼子要犯兽性了。以前只是听讲,现在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害怕,她便放开步子跑了起来。
这就好比一只孤独的羔羊落进了狼群里,逃掉的可能几乎是零。桂芬妈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兵围住,当街扯下她的旗袍就把她强暴了,临了,又在她肚子上使劲的捅了几刺刀。
亲人和爱人相继死在日寇的手中,这让桂芬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心更加碎了般剧痛,似乎要跟身体彻底分离。虽然她在心里一直怨恨甚至恶毒的诅咒过母亲,但当生她养她的这个女人真的从这个世界永远的消失时,她的心依然会不由自主的割舍不下的痛。
笼罩在古城上空的清剿乌云越来越浓密厚重,低沉得让古城人无法呼吸。陈三像条狗一样领着鬼子嗅遍古城的每个角落,凡是不顺眼的有些怀疑的,不是抓去关押就是当场弄死,每天都要雷打不动把清剿的成果上报给左田。说实话,左田对陈三这段时间的清剿成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短短的十几天,陈三率领保安大队就清除掉城内不少的抗日反日分子,还配合皇军彻底剿灭了古城最大的民间抗日组织“红枪会”。
“红枪会”的总堂设在城西十多里外的山村杨家桥,堂主叫杨震山。此人浓眉宽肩,力大无穷,自幼就爱舞刀弄枪,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据说年轻的时候能轻松抱起谷场上几百斤重的青石磙子,名气传遍方圆几十里,因此,前来拜师学艺的人日渐增多,到后来他就在全县各地开设了好几个堂口。起初,徒弟们使用的都是些强身自卫的大刀长矛之类的家伙,后来匪患不断,单靠那些冷兵器难以抵御土匪的袭扰,杨震山又应时添置了土枪火铳这些厉害的武器。
杨震山育有两男,老大叫杨虎,老二叫杨龙,两个孩子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因病离世,杨震山从此再没娶女人,一个人领着两个男孩把那个家撑了起来。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两个儿子吃苦肯学,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本领,不到二十岁就各自掌管了一个分堂,杨震山见两个儿子这般有出息,也就慢慢退居二线,做起了甩手掌柜。可是,快活日子没过多久日本人来了,而日本人烧杀奸淫的罪恶行径杨震山早有耳闻,早就恨之入骨,因此,他不得不放弃逍遥悠闲的生活,狠心变卖大部分家产去购置枪支弹药,很快就组建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自封司令,大本营仍扎在这三面环山的杨家桥。
既然将抗日大旗树了起来,那就得要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这头一仗该怎么打,杨震山心里还真没有底,最后只得把各分堂的堂主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讨。杨震山看一眼围坐在身边的分堂主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主要就是合计合计这头一仗我们该怎么打?这回我们面对的小鬼子可不比往日里打土匪那么简单,他们能打进中国,又一路打到我们这儿,说明他们不是软瓜蛋子!”
杨震山开场白之后,议事厅里却没有人回应,静得只有杨震山抽旱烟发出的吧嗒吧嗒的声音。杨震山憋不住火了,高声问:”怎么了?都怂啦?”少顷,他瞥一眼坐在桌边一直拨弄大刀的大儿子杨虎道:“虎子,你给老子说说你的想法。”
杨虎平时也是挺能说的一个人,今天遇到这么大个事情他也小心的不敢乱发话,忽听父亲直接点了他名,便不得不抬起头来咕哝了一句心里想的话:“要我说呀就一句话,这头一仗必须打出我们红枪会的威风来!”
“说的好!说到老了心坎里了!其实呀,我们都知道小日本强大,但再反过来想想,他们也是爹妈生的,也是人,是人他就怕死,就会有软肋可击,大家细想想是不是呀?”杨震山神情自若的一手端着旱烟管,一手有节凑的比划着。
经过杨震山这么一点拨,会场的气氛即刻活跃起来,不少人就在下面议论开了。杨震山扫了一眼会场,笑着说:“有屁就放,别都闷在肚子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都说说,这一仗到底怎么打才能有取胜的把握。”
“杨司令说的很对!是人他就有软肋,我们要想以弱胜强那就得挑要害打,我的建议就是先挖掉小鬼子的眼睛,疼死他狗日的!”说话的人叫穆道锁,原来是古城南后街的回民分堂主,性格耿直暴烈,是个硬汉,日军清剿他们的时候,他带领几个兄弟杀出了古城。
穆道锁接着说:“我们进出都要经过西城门外的鬼子炮楼,我认为那就是他们的眼睛和喉咙,我们就先端掉它!”
杨震山放下烟袋,把袖子往上一撸,青筋暴突的胳膊就裸露出来。他将蒲扇大的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赞扬道:“嗯,看来功夫没有白学,知道四两拨千斤了,敌强我弱就得这么干!”
由于穆道锁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案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会议很快就进入到作战细节,最后经研究决定:由杨震山司令挂帅攻西面,这边靠近城河,河堤可以作掩体,可进可退;穆道锁领队攻东面,负责堵住鬼子撤往城里的退路;杨虎率队正面主攻北门,这也是最艰巨最关键的一面。
那天夜晚的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真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听说鬼子怕黑,很少夜间活动,所以杨震山就选定这种天时。不过,选择这样的黑夜同时也有不利之处,那就是天越黑炮楼上的探照灯就越显得明亮,如昼的光线通透而贪婪,转来转去的贼光把铁丝网围拢的炮楼守护得几乎没有死角。
杨虎领队就埋伏在北门外的草丛中,他定神观察了一会探照灯转动的规律,然后瞅准灯光移过的瞬间,领上一个身手敏捷的队员,迅速靠近门口两个正在打盹的伪军,上前两个麻利的锁喉,处在眯糊中的两个伪军挣扎着蹬了几下腿就不动弹了。当探照灯再次转过来时,杨虎已经闪进门岗拉下了电闸,顿时,黑暗吞噬了一切,炮楼里即刻传出哇啦哇啦的叫声,鬼子伪军就乱成了一团。
电一断,趁着天黑,三个方向的队员迅速合围过来,手榴弹、自制的土炸弹从不同方向一股脑儿投向炮楼,枪声爆炸声以及日伪军的惨叫声连成了一片,日伪军还没摸到自己的武器就被冲进来的“红枪会”队员击毙或者俘虏,整个战斗历时不到一个钟头,等城里左田的援军赶到时,带着战利品的队伍早己在撤往西山的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