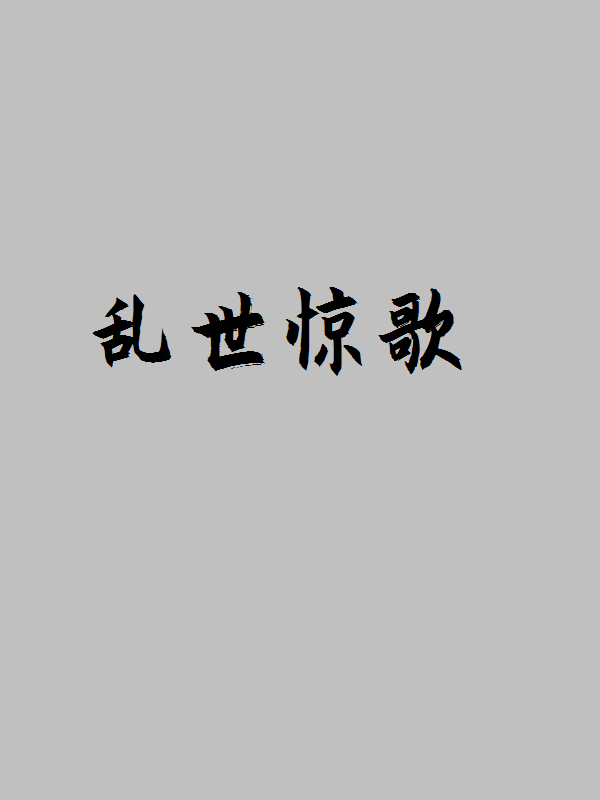昨夜夜殇走后钱沫沫就一直是在气呼呼的情绪中难以入睡,似梦似醒间她似乎听到了外面有人唱歌的声音,让她忍不住想要去分辨那些声音的内容。可是当她努力去听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声音又变成了嬉笑。
九王府中,何人能如此调笑不拘?就算是夜殇他也很少能如此开怀大笑,除非是在她出糗的时候,他才会大笑着嘲弄她,似乎欺负她就是他最高兴的事一样。
想到夜殇,钱沫沫的眼角又忍不住湿润起来,现在是晚上,没有人能够看到她的狼狈,她可以不用忍,不用克制。
哭着哭着她也不知道何时就是睡着了,都说要是哭着的时候睡着会变傻的。她却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哭着睡着了。而且每次梦中都会出现那个让她流泪的人,让她感觉醒着和睡着都一样痛苦。
浑浑噩噩的睡梦中再次出现他冷然决绝的脸,钱沫沫紧皱着小脸的睡颜让前面唤她起床的秋忆以为她梦魇了,慌忙摇晃着她的手臂将她从那个噩梦中解救出来。
“公主,公主?快醒醒,快醒醒,到起的时辰了!”
眼睛略有些浮肿的钱沫沫睁开眼睛见是秋忆,才慢慢地醒过神来。她坐起来看了看外面依旧黑咕隆咚的天,皱眉问道:“这才几更就要起了?”
“回公主已经快要寅时了,该起来梳妆了!刑嬷嬷她们都已经在屋外准备好了!”
秋忆一边将云床上的帐幔整理好,一边和钱沫沫说着话。她今日也换上了一套桃红色的大丫头制服,整个人也看着喜气不少。
钱沫沫看着忙碌的秋忆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寅时,算算也才刚要凌晨三点而已。有必要起得这么早么?她不就在这府中吗?又不用大老远的接亲,何故起那么早。
虽然睡着后的梦境不怎么样,但是她还是有些困,忍不住困意的钱沫沫顺势就要再躺下去。秋忆见状,立即上前将她拉了起来。
“公主,切莫再睡了,再睡就误了吉时了。”
将钱沫沫强行从床上拖下来的秋忆,一路将她带到梳妆台前,将她按坐在梳妆凳上才开门招呼伺候洗漱的丫头进来。因为今天是九王府迎娶王妃的日子,所有的小丫头俱是一身桃红色裙装,十分的讨喜。
开门后深秋的凉意在瞬间涌进屋内,冷气一激钱沫沫顿时清醒了不少。由着景嬷嬷和刑嬷嬷给她净了面之后开始一层层地扑粉。那一层层的百花蜜粉匀在脸上,让她感觉只掉渣。
需要解释一下了是刚才的净面,那不是以往的用水洗洗脸即可的程序,是有全福嬷嬷取一根细细的丝线将她脸颊和发迹间的碎发尽数缴去,说是碎发,其实就是发迹线上的绒毛。
身为全福嬷嬷的刑嬷嬷虽然已上年岁手指却分外灵活,一看就知道平常一直有在练习。虽然每次缴去绒发之际都会猛地的痛痒一下,好在刑嬷嬷手下麻利,也没几下就完成了这项程序。
等钱沫沫回过神来的时候,刑嬷嬷连百花蜜粉都已经扑好了。她看着镜中脸色白的吓人的自己,突然想到了她曾在街上买来的那个山鬼面具,本来准备偷偷戴在脸上在夜殇揭开盖头的时候吓唬他用的,现在看来,即使不戴面具就已经够吓人的了。
她冲镜中的自己扯嘴笑了一下,本来想想中的那种簌簌掉粉如下雪的景象居然没有出现,此时她才注意到刑嬷嬷手中的蜜粉和平常的有些不同,似乎更加水润一些。刚想开口问问,便被刑嬷嬷用眼神制止了。
看着刑嬷嬷嗔怪的眼神,钱沫沫才想起来,从现在开始她是不能随便讲话的。要一直等到夜殇揭开她的红盖头与她同饮交杯酒之后方才结束。
夜殇的身影随着她的思维再次挤进她的脑海,一瞬间她脆弱的心脏又是千疮百孔。为什么匆匆中秋分离之后他就变了那么多呢?以前他再怎么生自己的气都没有像这次这般让她心碎。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无非就是信任与包容。现在的他们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何来包容之说?
敛了笑意的钱沫沫任由这刑嬷嬷在自己的脸上抹抹画画,闭着眼睛也不再去看镜中的自己。反正她不能说话,不如闭目养神的好,天知道这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况且这几次她和夜殇的见面都是不欢而散,谁又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她可不信他们能一副琴瑟和鸣的欢度春宵。
刑嬷嬷的化妆好似面部按摩一般,只将钱沫沫弄的昏昏欲睡,好不容易化好妆天已经蒙蒙亮了,钱沫沫突然有种感觉,似乎这样下去,她这还有些起晚了呢!等梳好头都不知要到何时去了。
正研究着刑嬷嬷会如何给她梳头的钱沫沫被院中一阵脚步声与说话声打断,不到片刻就看到王府的管家带着几个宫中打扮的老嬷嬷走了进来。
景嬷嬷急忙上前与她们寒暄,听着她们话中的意思才知道这几位嬷嬷也是湘妃娘娘派来助阵帮忙的,她们更是将湘妃娘娘和皇上赏赐的一些吉祥物给带了过来。
弄得钱沫沫她们又是下跪又是谢恩的,只折腾了好一会子她才又被秋忆和景嬷嬷扶回到梳妆台前。跟着刑嬷嬷就将钱沫沫一头的乌发全部打散开来,手执一柄鸳鸯玉梳念念有词地从她的发顶一直梳到发尾。
“一梳梳到尾 ,
二梳梳到白发齐眉 ,
三梳梳到儿孙满地,
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
.......”
这些吉祥话陪和着刑嬷嬷梳头的动作一句一下,让钱沫沫直觉得似乎看来自己母亲为她梳妆打扮的样子,不知不觉间眼中就盈满了雾气,景嬷嬷一见她这样立即从旁边的贡品中拿起挑起一粒蜜果,递给钱沫沫。
钱沫沫知道这是之前刑嬷嬷说过的破苦(哭),只要吃了这甜果就能破出眼泪的不吉利。当下她眨眨眼睛接过景嬷嬷手中的蜜果放入空中,细细地咀嚼了起来。
“还苦(哭)不?”
“甜!”
景嬷嬷望着钱沫沫的眼神中满是宠溺的母爱,在她心中早已将钱沫沫看成了自己的孩子,看到钱沫沫流泪,她比这屋里的任何人都要难受,因此她也才能在钱沫沫眼泪尚未流出来之际及时打断。
景嬷嬷的宠爱让钱沫沫心中比口中更甜三分,她配合地朝景嬷嬷点点头,回过头来再看镜中的自己时突然觉得无比陌生。那个低眉顺眼,温婉柔情的女子是她么?当初的那种锐气与心高气傲已然不复踪影。
怪不得都说化妆是一种美丽的变身,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意境也不过如此吧。
癸形铜镜中钱沫沫螓首蛾眉,肌骨晶莹,纤巧的琼鼻下樱桃小口不点而红。妆台前烛火跳动,她肤若凝脂娇羞的俏脸上似乎轻笼薄雾,让人看不清透,又移不开眼。
镜中的女子额前的刘海已经从初来时的齐眉长到了耳际,被刑嬷嬷尽数梳到了发顶,露出额头的钱沫沫脸上的稚气顿时消去大半,俨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少妇。
层峦叠嶂的牡丹髻在刑嬷嬷的手中一层层显现,乌黑油亮的青丝转瞬间便从倾泻而下的瀑布变成了山峦。秋忆见状忙将一旁小丫头端着的凤冠头饰接过去,拿到了刑嬷嬷身边。
公主出嫁的凤冠是有等级规格之分的,钱沫沫看着秋忆端过来的凤冠,只感觉自己的脖子都要折了。纯金打造的凤衔珠花冠在烛火的照耀下褶褶生辉晃得人眼都睁不开,精巧的做工将一只翱意九天的飞凤做的活灵活现,飞凤的翅膀和尾羽都在每一步的走动间微微颤动,就像真的是一只金色凤凰落在了那里一般。
将凤冠头饰按预先算好的位置佩戴整齐,钱沫沫又在一众人的伺候下站起身形来到内室更换喜服。那套她未曾试过的喜服被两个小丫头一左一右展开,她头顶重金在秋忆和景嬷嬷的搀扶下晃晃悠悠地将那套喜服换上,等她穿上喜服的时候她才知道原来这套喜服上的绣线也都是金丝线。
这下真如穿戴了黄金刑具一般的钱沫沫,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如果就这样逃了这身行头应该也够她衣食无忧了吧。
她暗自好笑自己的想法,倘若真是那样,恐怕她将会成为这夜冥第一个因为一套嫁衣而出逃的新娘吧!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屋内的烛火除了长明灯都已经熄灭,而这盏长明灯据刑嬷嬷说是点亮她婚后到道路的明灯,在今日是万万不可熄灭啊。这样的话告诉她之后,她就总是时不时地想要去看看那盏灯是否亮着。
尽管她现在与夜殇出现了裂痕,她依旧在乎着。甚至从未动过离开九王府的念头,自嘲患有受虐症的钱沫沫知道她的心中已经被他满满地占据,无法再让他离开。
若真有让他离开的那一天,恐怕她不死也得脱层皮。一切就绪,屋内只剩下几个身边伺候的,剩下的人都在钱沫沫盖上盖头的那一刻离开了。被挡住视线的钱沫沫就在这方寸之间幻想着她和夜殇和好如初后的甜蜜,却不知等待她的将是一场狂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