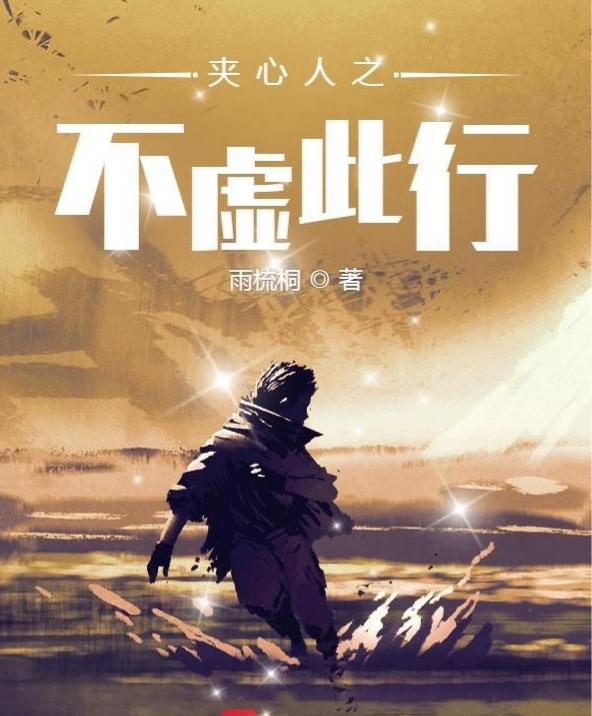12点多的时候,王森定了4:00的闹钟,睡了。
一夜无事,在这个世界里。
睁眼,明晃晃的房梁,在这个世界里。
王森一个骨碌爬起,身子有些酸。有叽叽喳喳的鸟雀群音透过纸窗,推开厚重木门,阳光媚灿,染金木屐。白雪覆地,茫茫舒人心。积雪若沉了,难免心灰龙钟;薄了,又生出凄清意,却是这最称于兴。
但每每意境总不能久留于心,如花香残弥。
“死呆子,你倒把风范装得高深。”
“唉”王森长叹,负手而立,夹杂着雪粒的风卷起残袍。“这位姑娘,敢问路在何方?”
“出门左转过两个沟沟,你出恭兼早食。”老子姑娘就是看不惯王森这副人模狗样。
“未必。”王森在木板门口解下腰绳,裤筒哗一下掉到底,就尿在花园里,脸上带着恶趣的笑。
“却是同鲁迅先生讲的一般,低级趣味的很。”羌笛意外地平静,鄙视道。
王森感觉到危机感,老土著都学到民国时期了,从自己心里那丁点的文化积蓄里学来的。
“嘿!这世界!”王森裤筒还堆在脚跟,不知怎的就是有点心朗。“还有那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世界,你们好啊啊啊啊啊啊啊!”
王森提上裤筒,忽然看到鬼鬼祟祟窝在墙边的陈丹。他见王森望他,谄媚地跑上前,张张嘴,又有点忸怩起来。“公子,早安。那个,你早食了吗?”王森摇摇头,太阳快升上头顶了,昨日的小孩儿还没来,看来自己是没饭吃了,只能自行解决。
“嗯?我烤鱼,一起啊。”王森意识到陈丹的意思了。
“那我也不好推辞了。”
“真香。”陈丹大快朵颐,手抓一个往嘴里咬,眼睛还直瞪瞪盯着火架上的,两白袖都弄得油迹斑斑。不得不说,这个陈丹挺让王森觉得值得请他一顿,但仅仅是一顿而已,看到陈丹的油手还要往火架上伸,王森给一把摁住了。“你道法挺高,等会儿教爷几招。”“必须的”陈丹嘴里塞满鱼肉,含含糊糊的,但神情确实一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王森这才松开手。
等陈丹躺在地上直打嗝了,王森拍拍屁股上的雪,向陈丹挑挑眉。白衣忽然一个鲤鱼打挺站起,向王森抬手作揖“公子……”
王森抬手就是一个巴掌“装,装,装,接着给爷装,让你教几招还扒你皮了不成。”陈丹抱着头鼠窜“好汉饶命,我教我教。”
莲花步,春风掌……陈丹理亏,不藏私地顺着口诀全教了。一晃便是一整个下午,直到陈丹的肚子“咕”叫了一声。
白衣把烤鱼大口大口往嘴里塞,也不顾烫舌。“你咋看出来中午的时候我还没变成那个之乎者也呢?”
王森觉得这鱼其实自己烤得不咋地,或许陈丹没吃过,尝鲜吧。听到他含含糊糊地讲,抬起头。“怎么和你说呢,感觉上的事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给人感觉,不管有多像,甚至于一模一样,但就是有特别处。”
“哦”陈丹又抓了另一条鱼。
“走了,小丹。”王森拎了刀,剩下三条鱼,走向小溪。
陈丹抓着鱼望拖刀人背影,这人真实在。忽然想起小时候大仙卿给他讲的江湖,豪杰相逢,一碗烈酒,五两牛肉。“小森!”他大叫“我俩当兄弟吧。”王森不理这神经,自走他的。陈丹自以为是“好!歃血为盟!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他说得激动,王森已扎进冰冷溪底。
空中有星辰。王森鲜血淋漓地爬上岸,没见到那神经病,估计又变成之乎者也了。
拖着的刀一路白雪滴血,王森这次朝盘坐老人冲得劲了,但同样离水圈半步,一把不知从何而来,从何防起的剑气穿透了胸膛,较上次,下手更狠辣了,怨他的知难不退。
王森昏了,也悟了。
不等四点的闹钟,王森醒了,看看手机,3:59,然后闹铃响了。
王森开锅洗米煮粥,然后躺在沙发上。
过了好长一会儿,卧室的门被打开,羌笛的小头鬼鬼祟祟探出,走过王森房门时格外小心,一直走到大门旁。
出于礼貌,躺在沙发上的王森咳嗽一声。羌笛立刻像受惊的羊地回头,惊讶地发现王森竟然躺在沙发上,好像此时他必须睡在卧室里似的。
“那个,我不是坏人奥,真的,里面有点误会”羌笛一点点蹭到手抓到门把手。王森松了口气,看来失忆好了,剩下的就是把什么粒子什么老子姑娘解释给她。“我煮了粥,你吃一口吧,我慢慢解释给你。”
羌笛嗖一下拧开把手逃出去了。
王森无奈地盛了两碗粥,四双筷子,这妮子,走的时候还穿着自家的睡衣。
果不其然,王森刚摆好两碗粥,就听见小小的扣门声。王森打开门,看到了通红了脸的羌笛。
“吃一口吧,我要是坏人,昨晚就下手了。”
――
王森一直在等,每天问道连刀,只是不再去老人那自讨苦吃,这样过了三天。
终于,冬天过了,天下雨了。
王森负刀于湖心,雨滴滴滴答答滴落白衣,刀身,黑发。王森拖刀劲冲,须臾间来到圈前半步,剑气从后而来,袭向背,王森知道,因为,剑气划破了雨幕。王森只脚点地,滚身躲过剑气,这一滚,便是那半步距,直冲向盘坐老人,触圈。
满幕雨滴悬停,滴滴射向空中王森。
王森落地圈旁,裸身尽是鲜血。
湖面激烈震荡,最终坍塌。
一白发湿漉漉捧一血身上岸。
那雨日,大仙卿吴蓑自破天关,反天道,为了心中的道。
那日后,世人众说纷纷,有人说,前大仙卿吴蓑反天道谴死淮山,却有一青衣说,大仙卿闭关悟了,真真悟了世间道。
只是从那后,再无天道闭关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