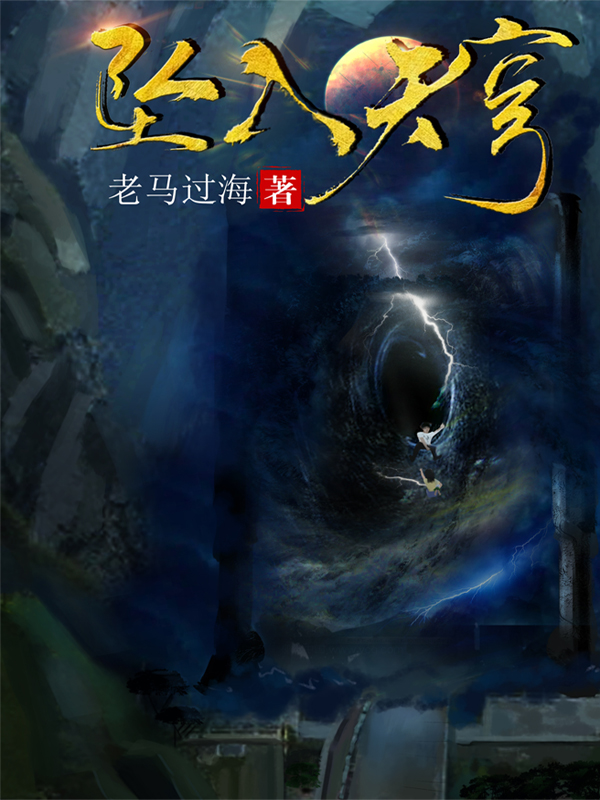地球上的仅存人类十分狼狈,浑身烂泥,赤身裸体,更严重的是没有食物来源。几个壮实一些的下到烂泥里捞东西,却一无所获。
“哎还不如当时死了,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们在走走,如果这死寂的鬼地方确实找不到资源,咱们就组团上西天算了。”
幸存者里有十四男,十六女,看上去岁数都差不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家都来自不同国家,而现在却出现在同一块大陆上。
有人发话:“你们来这里之前是干嘛的?”
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率先回答:“我在大学里上课,突然大地剧烈摇晃,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我在画画。”另一个男人回答。
“我在调整程序。”
“我在睡觉。”
大家说着不同的语种,奇怪的是,却可以彼此听懂对方的语言,很快,人们互相认识了,也更加迷茫了。
“难道我们开了上帝视角?为什么不经过翻译我可以听懂日语,中文以及法语?”一个木匠说。
人们对彼此的好奇大过了如何生存。突然有个人喊了句:“那好像有鱼!”
…………
人们顺着喊话人的手看向不远处的河道,之间几条幽影透着清光在水道里游动。
人们欣喜,几个壮劳力跳进河里徒手抓鱼,谁知那些唾手可得的肉身却无光影般穿过捕鱼者的手。
男人们惊骇不已。
“什么?我们已经死了么?为什么手是透明的?”
大家一时间定格在原处,这时,一名青年男子说道:“我们如果已经死了,为什么还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说这话的青年名叫杨不周,是一个遗传学专业的研究生,按照地球的说法,他记着自己是25岁。
那天,杨不周正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他这段时间习惯了低头走路,因为思想的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
本院博导及自己的父亲杨怀山在一周前刚刚溘然离世,走的很突然也很痛苦,医生诊断是小细胞肺癌晚期中的最末期,已经发生了全身性转移。
然而在父亲被宣布只能等死的前一个月,他们父子俩还在谈笑风生,父亲和他说,自己正在研究人类基因重组的相关问题,有机会会和他细说。
然后就在父子准备一起去食堂吃饭的路上,一阵紧急的电话铃声将父子俩分开。
当晚,杨不周在实验室找到父亲,想和他说点什么,却被父亲不耐烦地推出门,说一切等周末回家再说,
杨不周错愕,感觉父亲就像换了一个人,脸色也十分不好,就犹豫不走。
杨怀山见状,很无奈的说:“不周,你最近课业怎么样了,你周末回家要看下我书桌上的笔迹,那是我多年在遗传学上的见解,你要吃透啊,要吃透明白么!作为我的儿子,你不能就混毕业,分配工作,你要……哎,算了,说的有点重了,你不懂的,来,你把这条项链带上,这里面有我和你妈妈的合影,我最近可能不能替你妈妈分担家里事,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戴着这条项链时刻鞭策你好好研究,来,快点,我有点忙,戴上之后你先回家吧~”
杨不周听话的凑过脖子,又觉得父亲方才的一席话,不知道哪点逻辑有点问题,但见父亲有逐客状,是又不好多问,就转身关门走了。
……
晚上,杨不周打开项链坠卡扣,仔细端详相框中的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这是标准的俊男靓女。母亲在年轻时候下乡被冰河水激到了,坐月子时候又落下病根,导致四十出头就办了病退,但是母亲为人勤快温婉,又做得一手好饭,对在外挥洒文墨,驰骋仕途的父亲来说,是一湾安静的港湾。
父亲在遗传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后,频繁出国交流,和儿子杨不周的交流也很少。不过杨怀山是激励儿子也考遗传学的,他说自己毕竟研究了遗传基因三十多年,想把这些成果传承下去,如果儿子也是这块料那固然更好,如果儿子实在不喜欢医学,那自己就要尽快找个人品可靠的得意门生了。
杨不周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高考时顺利考上杨怀山所在的省重点医科大学,并顺利考上本院研究生院。
其实杨不周从心里真的对遗传学无感,就算考,他也会优先临床医学,起码这是最热门的医学。而杨不周学遗传学,其实只是为了多接近这个在外人看来,光辉伟大的父亲,取一点暖,弥补一下长期父子分离的缺憾。
可有时候杨不周却感觉,离父亲的距离近了,心却远了。父亲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交给杨不周,而是派给他一些流程上的任务,如:写一份关于小鼠吃了XX后对基因的影响的分析论文;去实验室观察杂交果蝇的基因变化……诸如此类。
杨不周终于安耐不住,去找了父亲。
“爸,这些实验我随便就可以做了,您不是有多年心血么?我想尽快接触那些东西”
杨怀山脸一沉:“遗传学是严肃的科学,哪能随便就做了!你的基本功还不扎实,这些实验已经是研二才会给学生做的,你已经提前半年多了。”
“可是……”
杨不周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屋内急促的电话铃打断了。杨怀山示意他出去。无奈之下,杨不周只得悻悻地离开。
他不甘心,于是就趴在防盗门上偷听,可是这该死的铁门太厚了,竟然出了嗡嗡的杂音,什么也听不见,这是,门内脚步越来越接近门,杨不周吓得赶紧快步走下楼。
……
杨不周从此和父亲有了隔阂,变得更加客气和疏远起来。这让杨怀山也感觉到了父子俩之间的空气在降温,他时常无奈的坐在窗前吸烟看着远方。
如果说感情要靠生离死别来拉近,那真是一种悲哀。
一个月后,杨怀山被查出晚期肺癌,并且化疗已经没有意义。这个噩耗让所有人都惊呆,难道杨怀山就从来没有任何不舒服么,医学常识大家都知道,癌症到了晚期,身体会有征兆,如后背放射性疼痛,咳血等,可是杨怀山就在宣告不治前一天,还在谈笑风生,面色红润地喝酒、吃肉,难道说杨怀山有着很强的克制力?
说什么都晚了,残酷的事实在这里摆着。杨怀山就像被火烧过的老木头,两三天的功夫已经干瘪碳化。主治医生连连叹息称很少见过身体恶化速度这么快的病人,任何措施都无法拖延杨教授的生命,也没有发现其体内有什么辐射迹象导致肌体迅速衰败。就像一个迷!
杨不周内心谴责自己对挚亲的疑心,他放下手头的实验,请假去医院陪着父亲。
杨怀山嘴唇焦烂的说不出话,只是在喉咙里发出“嘶嘶”的气流。他抬起手用仅剩的余力示意杨不周接近自己。
杨不周站起来走进杨怀山,将耳朵贴近父亲的口唇,杨怀山并没有说话,而是一把抓住杨不周脖子上的项链坠,用力往儿子胸口怼过去。
项链在杨不周的胸口膈的生疼。就是因为用力过大,杨怀山突然晕了过去。
检测仪上的血压一点点的下降到50-40-30-22,血氧也一落千丈,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了。
病房里哭声一片,杨怀山永远的逝去了,很突然。
杨不周却不知道该如何哭,大悲无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
很快半年过去了,杨不周上了研究生二年级。
虽然父亲去世前的点点滴滴时刻萦绕在自己脑海里,但是关于父亲的谜团还是没有一丝头绪。
无数个夜晚,杨不周都把项链卡扣打开、合上、打开、合上。一直参不透父亲临终那一刻为什么要在自己胸前怼一下。他是想摘下这个项坠,还是想让自己去破解什么秘密?
……
就在杨不周郁郁寡欢一周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变让他的人生开始更加奇幻和冒险。
这天他在回宿舍的路上低着头走,不小心撞上一棵树,这棵树一下子倒了,砸中一辆停在路边的车,杨不周猛然抬头,很害怕,因为车主找到自己可能面临赔偿,同时,他也疑惑为什么这棵树根基这么不稳,自己撞上去不是应该自己是弱势一方么?为何作为静止参照物的树木却轰然倒塌。
他正在措手无策之际,四周的万物突然像细小拼图一样层层裂开,飞舞在空中,向着天际某个点螺旋式上升直到消失。
缺失了“拼图”的区域,成了漆黑色,无数彩光从黑色区域射进来,就像舞厅的彩色镭射灯交织在一起,这些光打在建筑上,树木上,垃圾桶上,还有杨不周的身上。
杨不周瞬间觉得身上就像小时候去医院做冷冻瘊子手术那般,在一阵阵嘶嘶嘶的麻疼感觉中也碎了开去……
世界也碎了,碎成千万枚拼图碎片,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被人滚着圈儿的砸碎了,蛋壳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