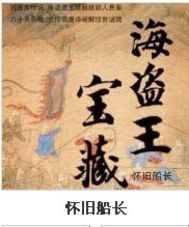李信干嘛去了?随着张四知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内阁大堂中谁都不吭声了,因为大伙都明白,这个声音不好发,弄不好是要担上莫须有的责任的。
至于张四知话中之意,只要不是傻子大伙都听的明白。无非就是指责李信在山海关大战时拥兵自重,坐山观虎斗,最后却是孙承宗一人力挽狂澜,这才是使得奸计没有得逞。
众人心中还是有疑问的,孙承宗毕竟是李信的伯乐,就算他再没良心,也不至于如此。张四知如此所为,无非是要公报私仇而已。
张四知似乎也没打算与众人商量,而是直接告诉记录的堂官,“记下来,将这一条记下来!”大伙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
“好了,该议的事也都议的差不多了……”张四知刚要示意散场回家,范复粹却插了一句:“差点忘了,还有件大事没议呢,万一明儿皇上问起来,可就临时抓瞎了!”
“左都御史傅永淳参劾江南织造局勾结市舶司贪污一案究竟是否属实,不论朝廷需不需要银子,都要彻查,查个水落石出!”
一直默不作声的薛国观也插了句嘴。
“皇上都说了,这不容后再议么?咱们内阁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将练饷这一节办好!”
“都不耽误,练饷的事不能耽误,打击贪污腐败揪出朝廷蠹虫也不能手软推迟!”
范复粹毫不客气的斥责了薛国观名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一便应该是一,二便应该是二,总拖下去是不行的。张四知也跟着范复粹敲起了边鼓,“玉坡所言极是,国之蠹虫绝不能放任,放任不管,大明的栋梁明日便会全部化作一根根朽木!”
薛国观受了两个人的抢白,气的一言不发,他之所以极力反对,还不是为了杨嗣昌,江南丝绸一案里大有瓜葛的浙江布政使赵秉钧是他的内弟,一旦赵秉钧被查出来有问题,必然会牵连杨嗣昌,到时候就算连皇帝都会对他心生恶感,若事情果真如此便再无回天之力。
“我不同意!”
薛国观被范复粹和张四知你一言我一语激的一拍桌子。范复粹却冷笑道:“不同意?皇上有旨意在此,你不同意可算不得数!”
“谁说我不同意彻查江南丝绸贪污一案了,我不同意的是对刘阁老与李信议功的不公平!”
这倒让范复粹愣住了,一时间便接不下去,只有张四知默默叨叨不依不饶。
“你给老夫说说,怎么就不公平了?李信带兵到辽西去无尺寸之功,又坐山观虎斗,坐看义院口被破,若不是念在他千里迢迢奔赴辽西的份上,老夫早就上本参他了!”
张四知连连冷笑,“老夫手下留情,居然还说老夫处置不公。既然如此,老夫便收回之前所议之功,这就上本参他!”
薛国观也针锋相对,指着张四知的鼻子骂道:“别以为薛某不知道你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李信在宣府坏了你的好事,到了现在便要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来诬陷功臣。好好好,薛某与你一同上本,你参李信,薛某便参你那些……”
“你,你,你……”
张四知急的一连三个你,指着薛国观便说不出话,一口气差点没上来,竟险些晕了过去,多亏身边有堂官手疾眼快,一把将他扶住了。
“阁老,阁老……”
老神在在的李侍问也坐不住了,上前来查看张四知的情形,刚才薛国观突然爆发差点揭了他的老底,老头子毕竟上了春秋,万一被气的血涌上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唉!都少说两句吧,诸位同朝为臣何必互相难为,各自退一步就算了!”
李侍问见张四知虽然身体瘫软,却似并无大碍,便想做和事佬劝一劝双方。谁知薛国观却咬住不放,“如何退?诬陷有功之臣,无视朝廷公义,若是让他得逞了,岂不是寒了天下百官的心?到时谁还肯为朝廷拼死卖命?”
一番话说的义正词严,李侍问撅着花白的胡子酝酿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是啊,张四知趁机打压李信,谁都看得出来,可是薛国观挑在了明面上,便叫人糊涂了。
李侍问糊涂可其他人不糊涂,谁看不明白,不论薛国观还是张四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看是为了李信和江南织造局勾结市舶司贪污的事争执,实际上是另有所指。
只是众位阁臣们也不便说破,若不是张四知将薛国观逼急了,他也不会撕破脸。
张四知在灌了两大口茶之后终于缓了过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颓然道:“好好好,老夫争不过你,念在同僚一场,也不能撕破了脸,江南织造局贪污一案老夫不追究便是,不过李信按兵不动一事,老夫却要一查到底!”
……
锦州,李信拉着孙鉁和他谈了整整一上午,从高阳到山西又到锦州,说起来这一年的经历却是让人唏嘘不已。
“李将军为国事奔走,孙鉁看在眼里,心里却是着实敬佩的紧,说起来惭愧,多少饱读圣贤书的举人进士们都没这般心志!大明啊……”孙鉁沉默半晌才缓缓道:“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你们武人其实也好,用不着操心朝廷上那些烂事,就说钱粮这一节吧,大军动与不动每一天都要耗费粮食数以万计。你们便只管打仗,可这大明的家却不好当啊。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你我就是那巧妇啊!”
本来说的好好的,权且闲聊,孙鉁如何又往朝政上提了起来?再说,这也不是一个文官该与武人说的事情啊。
“二公子的意思是,朝廷没钱了?”
李信对孙鉁一直保持了在高阳时的称呼,孙鉁似乎也不反对,甚至还有欣然接受之意。或许在孙鉁看来,李信称他为二公子,正是此人念旧的表现。一个武人虽然不能强求他讲究官场礼仪,而孙鉁最为看重的还是内心胜于表面吧。
“孙鉁守在母亲大人跟前四十余载,到现在才出来做官,虽然时日尚浅,却是知道朝廷根本就是一个大泥潭,一脚踩进去就算你想拔也拔不出来。在这大明朝想做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便不能秉持圣人那一套出淤泥而不染,是要和光同尘的,是要同流合污的!”
李信心道,你才看出来,想在大明朝做点事就得先搞政争,把反对的人都踢出去才不会有人掣肘。这一年来,李信在山西为官,自是深受其害,深有感触。
“二公子何以如此悲观?大明朝不是也出了个海瑞吗?”
“海瑞?清则清矣,刚则刚矣,却是于时局无补。”
李信没想到,孙鉁的看法居然更贴近世俗,一味的刚猛而不知妥协,最后可能什么事都做不成,就像海瑞一样,就连能臣如张居正者都十年而不用之,如此便可见一斑。
“尧舜禹汤,圣人那一套读书立说可以,拿到朝中来做事却是不成了,这也是孙鉁因何四十余载不愿出来做官的原因所在。”
孙鉁如此推心置腹,让李信大为感动,或许他真的将自己当作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武夫,以为自己听不明白吧。但随即李信便否定了这个想法,连他自己都会相信的。
“今夏大旱,粮食绝收,今秋和明春怕是又要饿蜉遍地,朝廷又连连加征饷银,百姓们苦啊,弄不好明年又不知有多少百姓被逼到流贼那里去!”
这番话若是在朝中说出来便是大逆不道,可李信却清楚孙鉁说的是实情,不过,这一点李信是早就有所准备了。
“二公子,别的省份不敢保证,至少在山西,今秋和明春不会出现饿蜉遍地的惨况!”
孙鉁大为奇怪,看向李信。
“哦?如何这么有信心?难道今年山西的雨水丰沛不成?”
李信摇头,“非也,今年山西一样大旱,几乎是滴雨未下!不过山西今年搞了庞大的灌溉工程,又改种了玉麦这种高产作物,虽然收成未必及得上丰年,但一定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惨况!”
孙鉁似乎大吃一惊,又详细的询问了李信是如何修建的灌溉工程,这玉麦的特殊脾性与产量,问的很细,李信答的也很细。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恍然,这李信除了能带兵打仗,居然还是个经世致用之才。
搁在唐朝以前,那绝对是出将入相的人才,可惜这是大明朝,非科举出身的武人就算可以封侯拜将,也决然入不了内阁,掌不了政事,朝廷也断然容不下他继续料理民事。
种种念头在心中起伏,久久竟然又颓然一叹。
“二公子何以叹息?”
“孙鉁只怕此战之后,李将军……”孙鉁忽而一扫满脸的忧虑,转而振奋精神道:“不说这些了,鞑子眼看便要围城,更是势在必得,你我可要准备好了应对这一难关!”
忽然有军卒来报:“孙中丞,孙中丞,出事了,洪部堂让您赶紧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