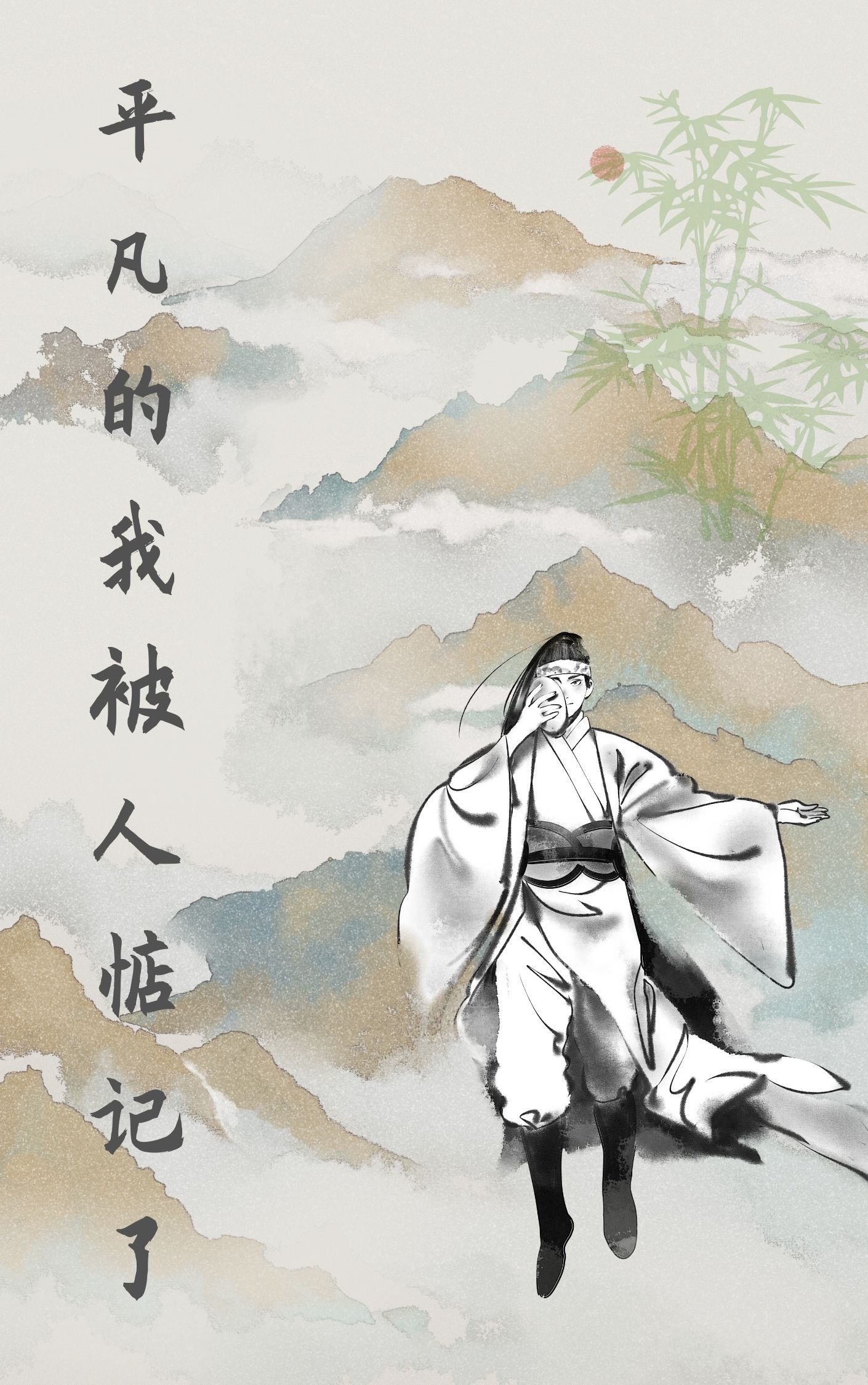郑四九继续颠覆着李信的三观,自己趴在了地上等着杖责。
我勒个去,这是什么节奏?不是为了成全那对奸夫**,宁可承受这八十杖责的痛苦吧?这哪里是打在他屁股上,分明是要打在他心头啊
连毛维张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他甚至怀疑这郑四九是不是受了刺激得了失心疯?自己若是也任由他胡闹,将来断的这桩案子传扬出去,丈夫与奸夫一同杖责,岂不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苦主伤心过度,行为失据。左右,去搀他下去。”
两个军卒上前便要将郑四九搀起来,岂料那郑四九却亢声道:“小人甘愿领罚,大人不必为难,只管下令便是!”
毛维张心道,这个令让他怎么下?一旦下了,传扬出去铁定就是个荒唐案子,他的官声就算彻底毁了。
郑梁氏在一旁泪眼婆娑,巴巴的看着郑四九,也不知道他是舍不得,还是希望毛维张赶快下令责罚完毕,他好与那金大有远走高飞。
李信实在看不下去了,将毛维张叫到跟前。
“律法也不外乎人情,郑四九有功与朝廷,又是苦主,咱们再判他杖责,恐有不妥吧!”
毛维张深为赞同,但却两手一摊。
“那又该如何处理奸夫?请大人示下!”
总兵大人出言干预他求之不得,正好就这皮球一脚踢给李信,自己可以摘的干干净净。
李信哪里有过断案的经验,忽然他想起古代有给犯人黔面刑法,便试探的问道:“黔面如何?”
毛维张眼前一亮,如此甚好,一点都不为过,如果太便宜了奸夫人神共愤,这样律法里的杖责可免,但却要以黔面为代价。传扬出去,谁也挑不出毛病。
得了李信的令毛维张立即令人强行将金大有与那郑梁氏强行拿下。此时此刻,他对金大有的那点好感已经荡然无存,一个道德败坏成如此德行的人,怎能堪当大任,果然是商人无义,贪图的唯有利耳,算是他看走了眼。
郑四九愕然,拦住毛维张问道:“大人这是?”
“还不谢过总兵大人,免了你的杖责,奸夫**倒要吃点小小苦头,才能放得,否则岂不是纵容天下这等不轨之事?”
郑四九将信将疑,他当然不敢如毛维张所言去向李信求证,但也还是跪在李信面前磕了三个头。
毛维张超台下挥手。
“都散了吧,各回各营,都散了吧!”
大伙热闹看的差不多了虽然意兴阑珊,但镇抚大人有令,便也都纷纷撤了。偌大的空地上顷刻间就变得冷清起来。
黔面一刑在宋代十分流行,即使到了明代依然存在,阳和卫城便有现成的刺青师傅,很快便被找了来,一切准备就绪停当,便捏着银针来到早就被绑好手脚的金大有与郑梁氏面前。
此时的金大有肠子都悔青了,受了那九十竹杖充其量养伤半年便又可生龙活虎,即便再领受八十杖只要不死就能将伤养好。可现在倒好,杖责虽免了,却换了黔面,将来额头上被刺了奸夫两字,他还有何面目再去见人?他自然便将这笔账算在了郑梁氏身上,如果不是这贱人,自己何至于此?
但是那郑梁氏又何曾不是自讨苦吃,一想到自己白皙光滑的脸蛋上要被刺上奸妇二字,她就有想死的心,平日里最得意的美貌顷刻间便要被毁掉,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但是一想到就算美貌没了,她还有金郎在身边陪伴,心里反而变得坦然了。
老刺青师傅显示长时间没有机会施展这门手艺了,将两个人刺得极为精细,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足足忙活了一个多时辰才算完事,将两个人疼的大呼小叫。
郑四九被获准来看郑梁氏,郑梁氏自觉毁容,再无面目相见,于是以袖掩面背对着他。她还有一句顶顶重要的话要说与他听。
“奴家到了这部田地也不恨你,只是还有一事不说出来总放心不下。”
“你,你受苦了。”
郑梁氏竟哼笑了一声。
“孩子是金郎的,与你没半分关系,还请还了与奴家吧!”
闻言,郑四九如晴天霹雳,这个一向外柔内刚的汉子再也承受不住打击,犹自不信。
“你骗我,你骗我!”
“骗你作甚,那几日咱们又同过几回房,没数么?”
骤然间,郑四九只觉得天昏地暗,心如死灰,踉踉跄跄出了刑房。
太阳西下,天色转暗,一男一女被军卒赶出了阳和卫城。女的怀中抱着孩子紧紧依偎着男的,男的却只想着如何能将这坑人的**卖个好价钱……两人一路南行,逐渐隐没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
在阳和卫城中有一堆的事等着李信处理,一转眼就将那对奸夫**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直到有军卒来禀报,说那郑四九前来求见,这才想起这档子事,却不知处理的如何了?于是便问身边的毛维张。
“那对奸夫**如何处理了?”
毛维张躬身道:“按大人吩咐,将那对奸夫**分别处以黔面之刑,而后赶出阳和卫城!”
什么?连女的也给黔面了?李信一惊,他记得自己的意思是只将奸夫黔面啊。怎么毛维张却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刚想掰扯几句,那郑四九已经被人领了进来。
郑四九好歹也是有功之人,李信对他很是客气,见他进来了,便忙令人看座。岂料,他却一口回绝,直接跪在地上叩头,然后淡淡的道:“大人在上,小人是来领罪的!”
李信诧异了,领罪?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毛维张则直接呵斥道:“总兵大人面前不得妄言!”
郑四九伏在地上道:“小人没有妄言,的的确确是来领罪的!”
“说罢,你何罪之有?”
这句话是李信问的,出了那等甘冒杖责成全奸夫**的奇葩事件,这个人身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足为怪。
“小人受人要挟,打开铁闸,放鞑子入城,致使城中百姓涂炭……”
毛维张当即喝止。
“莫要胡说,这可是凌迟的大罪!”
郑四九抬头望向毛维张,目光中没有一丝生气。
“小人拜谢大人好意,但是这的的确确是小人的罪过,人既然有过,就要甘受惩罚!”
李信忽然道:“本将没猜错的话,要挟你的人一定就是那金大有吧?”
“总兵大人慧眼如炬,正是此人!”
毛维张又是一阵心惊肉跳,这厮竟然是鞑子埋在阳和卫城中的细作,自己竟然还想重用此人,将此人树立为抵抗鞑子的典型。万一他真的以此在阳和卫城中混的风生水起,到时候的损失可能将是不可估量的。
一念及此,毛维张只觉得后背嗖嗖冒凉风,一阵阵的后怕。见到这郑四九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厮脑子里哪还有半点大局观,做事想问题都是以那点小家小利为根本出发。于是一拍案子斥道:
“那为何知情不报,任由鞑子细作逃离阳和卫城?”
“知情不报,纵容细作逃跑,小人甘心领罪!”
李信忽然又道:“本将可以免了你的死罪,但你却要为本将做一件事!”
郑四九此来本就是报了必死之心,听说李信能免他死罪,反而却不乐意了,执意让李信甚至让毛维张判他死刑。李信被这个奇葩弄的哭笑不得。
“听着,这件事关乎朝廷安危,九死一生,若殉国了也算死得其所,岂不比死在自家人刑场强上许多?更何况城中死了数百百姓,你以为一死就可以赎罪吗?没门!”
郑四九一脸的茫然,不明白总兵大人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既然他要交给自己去做的事九死一生,听起来也不错呢。
李信见他不再坚持求判死刑,便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本将需要你在阳和卫城中组织一支商队,会同这位法师一同前往塞北边墙之外,去打探蒙古人的消息。”
郑四九随着李信的手指,这才发现,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大和尚,这可大和尚不是旁人正是介休。
介休甩着肥硕的身躯,嘿嘿笑道:“施主既然看破生死红尘,何不投入贫僧门下?”
郑四九白了介休和尚一眼,毫不客气的回道:“死则死了,俺可从没想过要做秃驴。”
这话说的十分不客气,岂料介休和尚却一点都没生气,反而又嘿嘿笑道:“这脾气对贫僧路子,我喜欢!”
就在几个人商议如何组建商队一事的时候,有戍卒慌慌张张的赶了来,先是对毛维张耳语了几句,然后又一脸惊惧的看着李信。
李信见那戍卒如此做派,心里又是一阵咯噔,莫不是又出事了吧?
果真,毛维张忧心忡忡的开口道:“指挥使丘大人的长子,阳和卫指挥佥事,丘亮存回来了!”
原来是丘龚的儿子,李信奇怪。“回便回来了,何以你们都如此慌张?”
毛维张欲言又止,终是回答道:“此人脾气火爆,又在军中素有威望,恐怕会将丘指挥使之死迁怒于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