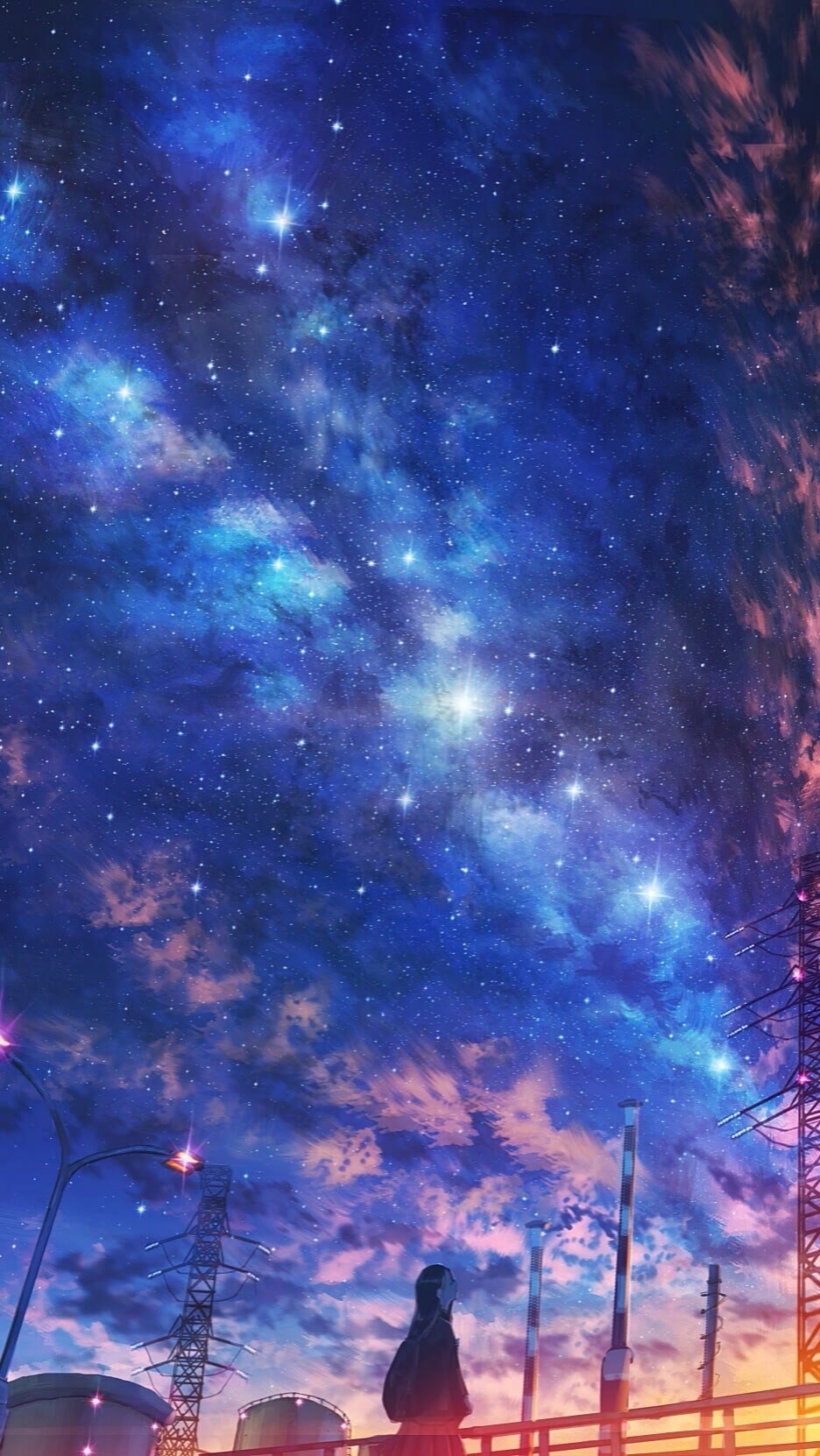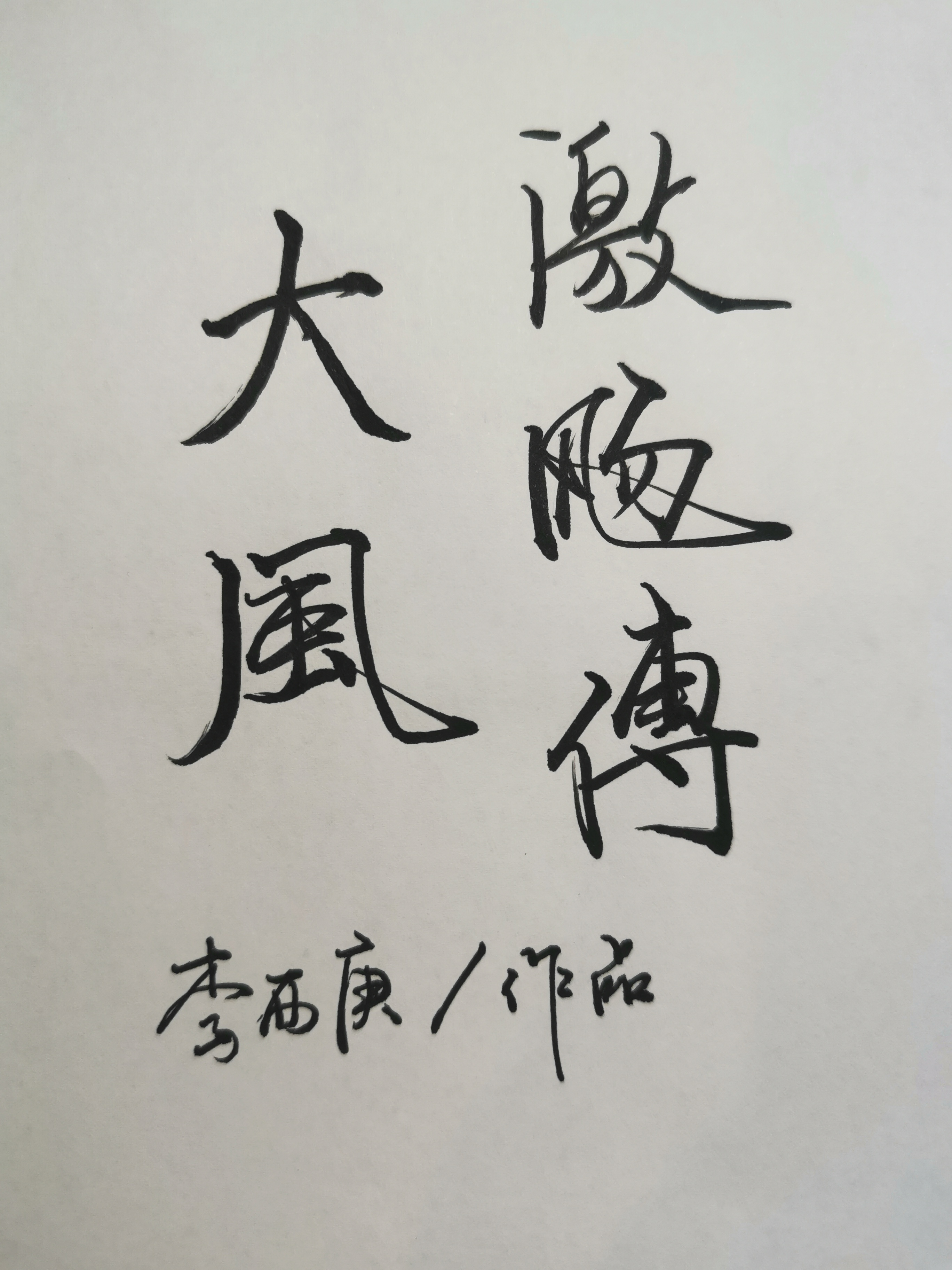民国五年,袁世凯多次复辟图谋失败,于六月病逝。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国民经济的法令,点燃了民族资本家振兴实业的热情,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从思想道德到文学学术等方面向封建专制思想发出猛烈地抨击。上海、北平等多地也掀起个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潮。
一条狭窄不平的道路上正行驶着一辆小轿车,光滑的车身被正午的太阳照得刺眼。迅速转动的车轮时不时激起水沟里的泥泞,脏水溅到了两旁翠绿的草木。
“二少爷,您这次出来就放心痛快地玩,放肆地玩,那个女人绝对找不到您的!小的我啊!都打点好了。”一名坐在后排的身着深绿长袍的少年对着身旁那位正在看窗外秀丽风景的男人谄媚地笑道。那男人专注于青山绿水,一言不发,弄得旁边那位紧张地攥起来衣袖。“哧。”男人对着窗子笑了笑,深邃的眼眸一直注视着窗外,似乎外面的风景令他身心愉悦:“这话说得,好似我就是个只知道玩的纨绔子弟。”话音刚落,那少年吓得变了脸色,立即低下头连喊着:“少爷!小的,小的不会说话。请少爷大人不记小人过,宽恕小的这次吧!”男人稍稍转过头看了一下一脸准备受罚的少年,温和地说道:“小空,我其实特别讨厌你叫我少爷,以后私下里,直接叫我哥!”男人刻意加重了“哥”字,希望他能开窍。可这少年听得有些懵,一时回不过神来。但他可以意识到的是,少爷已经原谅他了或者说少爷压根没生气。少年慢慢抬了抬头,似乎是在暗道内慢慢摸索,生怕踩着什么熟睡的蛇来咬他一口。
少年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男人,确保他面色温和后说了句:“少爷,哦不,哥!再过一炷香的时间应该就到花濛谷了。”少年开心地用手指向前面。身旁的男人右手随意地搭在少年的肩膀上,薄如蝉翼的双唇绽开了皓齿,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那时自己和他还是整天称兄道弟的,两人一起闯祸一起蹲马步。只是自己后来去了西洋读了五年的书,回来时面对的却是一声又一声的少爷。男人的回想突然被小空的话语打断“哥,那小镇的钱老爷月初就知道你要来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到时候给您接风洗尘。”男人微微点了点头,便又看向了窗外。
春日暖阳,明净苍空里的蔚蓝由浅入深的过渡色染,加之以飘霏装饰。两旁高大的青山如若两只熟睡的青龙蜿蜒卧席,道路旁的溪水潺潺流动着,清澈溪水底的小虾清晰可见。艳丽殷红的山茶,绯红的桃花,洁瑕如玉的梨花还有其他各种果树的花卉,流露的芬芳引来了无数的蝴蝶与蜜蜂,它们在花丛中起舞。这是他久日在繁荣街市里极少见的景象,蓦然想起陶潜的《桃花源记》:“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只怕这样的世外桃源将被军阀的铁骑踏灭,好景还是提前看看,免得遗憾。
“停车。”男人喊了一声,司机便停了下来。这还没到呢?处于茫然之境的小空,被男人迅速拍了下脑袋:“别愣了,老规矩。”小空吃痛地一只手捂着刚刚被拍的地方,看着一脸不怀好意的男人,强颜欢笑地说:“哥,还来啊!”男人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可是,哥,我与你相差太多,我不行的。”男人看着他痛苦又疑惑的样子心想:看来上次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太好。他不禁笑出了声:“傻小子,你不行,不是还有吴哥嘛!”说罢,男人看向了前排的司机,他勾起了嘴角:“行,唯你是从。”
此时,花濛镇的入口,一处本不宽阔的地方被人们挤得寸步难行。人们准备了鞭炮与自家的佳品,准备喜迎贵宾。站在最前面的是小镇上最出名的地绅——钱首名。可今天的他格外紧张,左手握紧檀木镶玉手杖,另一只手放在腰后紧紧攥着,硬是将他那有些许驼的背撑直了。他身后的随从们一样不敢怠慢,顶着正午的烈日任由脸上豆大的汗珠一一滑落,不敢擦拭。两旁立着的则是其他小有名气的商贩,有的是染布坊的,有的是酒馆的,有的是赌坊的,各式的人都来了,甚至花满楼的妓院里也来了几位花容月貌的美人。只可惜,她们脸上的脂粉快要被晒化了,这时时得注意补妆,倒是难为她们了。
离小镇不远处的山谷上,有一片梨园,那里有两个姑娘正在采拾梨花的花瓣儿。一双双纤纤玉手摘着树梢边的花,上边过高处的梨花开得甚好却够不着。倏忽,扬起一阵清风,欲落的梨花瞬间飘下,如同一场梨花雨,落了满地的香雪花瓣。
“阿雪,今年的梨花比往年开得更盛!”其中一个身穿素青高领上袄,下着碧绿布裤的女孩满心欣悦地对不远处的身着桃红袄裤的女孩说道。
“是,你开心,我可高兴不起来。”女孩一手一手狠狠地摘着梨花。“你可不知道,我俩刚出门那会儿。我就见着那钱家钱美娘打扮得跟花似的,还有那刘家的刘玉华,更别提那花满楼的妓子了。”姑娘见她一脸的苦愁样,放下手中的梨花,不疾不徐地走到她身边:“可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来这采摘梨花!谁让他好巧不巧的,选了春分这一天来。阿雪莫不是上看那人了!”阿雪微皱眉头,也不是不可以。
“阿梨,你是不清楚!那舒家可是上海市数一数二的大商人,家财万贯。有钱就算了,偏偏那舒家的三少爷是行军打仗的大将军。”
“那他有钱也是他家里的钱,有权也是他哥的权,他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阿梨,你是摘花摘傻了吧!那是一家人!要是我有幸嫁过去,那就是贵妇太太,那些好看的绸缎首饰想买就买。我定要趾高气昂的!看谁以后还敢瞧不起我!”语音刚落,她又连忙摇摇头:“错了,错了,太太什么的,我算是指望不起了,只求是个几房的姨太太,也是心满意足了。”
“你想要钱,依我看,那钱老爷不是有权又有钱的,你怎就不想嫁给他呢?”说完,女孩的眉眼笑开了花。
“阿梨!你又取笑我!那半个身子都已经栽进土里了,脾气又臭又硬的老头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
“哦,那你是喜欢那种又高又俊,又多财多权的年轻男人咯!”
, “你听我说啊,我前几日听闻那舒家二少爷是个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美男子。这样的谁不想要啊?”阿梨察觉到了阿雪疑惑的目光,故意偏过头去。“别告诉我,你不喜欢!”阿梨细想了一会,她倒是有个想嫁的人,只是......她慢慢从衣领里拿出一枚白玉吊坠。
“阿雪,你可曾记得这个?”阿雪接过玉坠,觉得有些眼熟,仔细想了想,才忽然忆起。
“这是,长生玉。我记得呢!你十岁那年受了风寒,看了好多大夫都异常不见好。就当干娘快要放弃时,一个江湖术士给了干娘一块玉,说能佑你长生。神奇的是,你第二晚病便好了。”阿雪说罢,便将玉坠还给了阿梨。
“这些年,我一直戴在身上。其实还有一件事,娘临走前在我的耳边轻语道这长生玉还有一个用处,就是一旦那个人出现了,这玉也就会自然裂开。娘说,玉碎消灾,但那个江湖术士却说不是大吉便是大凶。是凶是吉,都得看那人现了身再下定论。”阿梨看着手心的玉坠,光泽饱满,晶莹剔透,在日光的照耀下显出了夺目的光辉。
“所以说,你是决心要听从玉坠的指引咯。可是,这玉坠好端端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裂痕,无缘无故就裂开,我还是有些不信。万一,是娘记错了?抑或是娘说错了?”阿梨轻轻摇了摇头,她也不知是真是假。
“说真的,要是那人现身了,你会怎办?”阿雪期待地盯着她的眼睛。
“我会怎么办?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自己一个人受过罢了。”天生下垂的眼尾与那白皙的肤色,再加上飘落的梨花,给人一种我见犹怜的错觉。其实她并未在意这些,只是随口一说。
“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天底下那个女子不期望自己能嫁给个如意郎君。”阿梨听罢,自嘲般地笑了笑。
“这么想也甚好,可你若是越这么想,就越接受不了事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大事,又岂能我们做主!说心底话,我谁也不想嫁,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待在这片梨花园里,即使是让我死在这儿,我也愿意!”阿梨一直紧锁的眉头稍稍舒缓开来,从小在这长大,也不愿去看那世事繁华,山河更替。
“别这么说,你娘还给你留了个酒馆,你也坐拥这一片梨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接手醉芬芳了。而我是个孤儿,不知从哪来,也不知到哪去。”阿雪垂下了玉貌花容的面孔,整个人像是失了魂似的愁闷。
“你哪也不用去,就留在我这,保你吃饱穿暖。今后与我一同打理醉芬芳,好嘛?”阿梨挽起她的手,笑着安慰道。
“我又没说要离开,你我情同姐妹,我怎会离开呢!这太阳快落山了,花也要摘完了,我们走吧。”
两人将收集好的花瓣放进竹筐里,携手下山。一路上,她们穿过低矮的灌木丛,踏过细小的山间小溪。来到河水旁,乘那渡口的船,去到那边的小镇上。
在那河水的另一岸,一个男人躺在离渡口不远处的草坪里,他享受着这里的花草树木,简朴的小镇,有着从未见过的风土人情。才在这里一天,他仿佛就有种归隐山林的感觉。就在他闭目养神之际,对面山林飞来了一群青鸟,一会儿聚在一起,一会儿七零八落,最终又飞回了对面的山林。此时,只见那河中漂浮着一叶扁舟,随着水流缓缓飘来。忽地,见一女子侧卧于船身,那纤纤细腰露出船体,左手轻轻放在水面上,随着船体的移动,凝脂玉指在水中波动着,引起阵阵涟漪。可奈何那女子的相貌被前面的雪柳枝挡住。正当他要站起来时,船已经到岸了。
那女子凝眸皓齿,肤若积雪,一身素净的衣裤,头上戴着一块浅绿头巾,脸旁两边有些许发丝显得有些凌乱,一条乌黑的马尾辫由右至左静贴在胸前,上衣稍稍收紧,显露出了杨柳细腰,从侧面看去犹如一条凹凸有致的曲线。全身上下没有半分饰品,整个望去宛若那脱离世俗的神女,虽高不可攀,却摄人心魂。随后,只见那佳人从船舱中牵出另一位绝色佳人。她们付了钱,似乎要走过来了。
他立即坐了下去,一只脚舒展地伸直开来,另一只脚踩在草地上,左手随意地搭在左腿上。嘴里叼着一根马尾巴草,目视前方,仿佛没看到她们似的。
当她们走后,男人继续待在原地,感慨着这乡间小镇竟会有如此佳人,自己也算是开了眼。要是那天自己能睡了她,那做梦都得笑醒,可看她那清冷的模样,自己怕是在做梦。他继续看着眼前的长河美景,直至夕阳西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