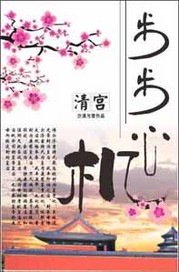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只蝉鸣一阵接着一阵聒噪的人心中烦躁不安。
顾讳庭立在乾清宫大殿之中,忐忑不安。那头顶上是鎏金的“正大光明”,却是异常的刺眼。皇帝着了件鸦青的绞花团福寿贡缎袍,坐在御前静静地望着他。顾讳庭却是汗珠如雨下,一阵阵的心中发紧,皇帝方才是昭了他与几位同僚来商议苗疆叛乱之事可说完一切却独独留他下来,他免不得便心生不安,忽然听皇帝慢悠悠地说道:“景寒今年岁数也不小了吧?”
顾讳庭不知皇帝何意,只答道:“景寒是康熙五十二年壬辰年生的,二十有三。”
皇帝却浅浅勾了勾唇,“如此说来,也到了娶妻立室的年纪了。”
顾讳庭悚然一惊,冷汗直流,却听皇帝又道:“富察氏李福荣的掌上明珠富察芷珊今年年方二八,端庄秀雅,是皇后的表亲,朕今日便替景寒做主将富察芷珊许配给他如何?”
顾讳庭匆然跪地,俯身说道:“皇上赐婚,臣深感皇恩,感激涕零,只是小儿顽劣,只恐……只恐配不上富察小姐……”
一言已毕却是费了全身的力气,头顶半响都未听见回应,顾讳庭身子紧绷绷的,几欲僵硬之际终听皇帝淡淡地说:“此事你回去同景寒商议再做决定。”
顾讳庭欲说些什么却听皇帝挥了挥手,似是极其疲倦的样子:“跪安吧。”
顾讳庭只得跪安走了出去。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隙照落下来,在地上勾出一个又一个模糊的影子,廊前的紫藤萝幽幽盛开,如一湾紫色的瀑布,盈盈生辉。
顾谚昭方下了差,穿过抄手游廊便准备回屋子去歇着,却不想远远看见花厅中正襟危坐的两人微微一愣,本该是歇午觉的时辰可父母又为何在花厅中坐着?略一思索便先进了花厅,请了个安:“父亲,母亲。”
顾夫人面带愁容的瞧着他,顾讳庭也是一脸的凝重,顾谚昭见父母如此心中只觉不安,于是便问:“父亲,出了什么事?”
顾讳庭长长叹了一口气,“昭儿,你心中可还想着沈家小姐?”
顾谚昭不妨父亲会如此问,一下便愣在那里,想到素依心中便是一阵伤痛,那一种愁苦悲凉只叫人甚感萧条寂寥,眼底的哀戚四溢,沉声说道:“孩儿与她已是今生无缘,再不敢奢望。”
“如此便好。”顾夫人见儿子如此说不免松了口气,笑着道,“今儿皇上叫你父亲去,说是要给你赐婚,是富察家的芷珊,她跟皇后乃是表亲……”
“母亲!”顾谚昭出声阻止道,“儿子现在不想成家。”
顾夫人蹙眉嗔道:“昭儿,你早已到了成家立室的年纪,那芷珊也是名门闺秀,样貌清秀又德艺双馨,比那沈素依也丝毫不逊,你有何不满的?”
顾谚昭只是沉默,顾夫人说了许久见他不为所动便对顾讳庭使了使眼色,顾讳庭于是说道:“昭儿,你若不愿娶亲,为父也不想勉强,只是这赐婚是皇上提出来的,又是皇后的亲眷,你叫为父如何推脱?”
顾谚昭抬眸说:“皇上那里我自会去说,父亲不必担心。”
顾夫人又待说些什么,顾谚昭却早已转身出了屋子,顾夫人不禁微微愠怒,对顾讳庭说道:“你这个儿子都叫你给惯坏了,他不愿意你便由着他去,长此以往,他何时能成家立室?”
顾讳庭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亦是心中繁乱,沈素依是沈卫忠的独女,他又何尝不愿意顾谚昭能娶沈素依进门,他也好替知己略尽薄力,可现如今,等了那么许久,却终究是一场空,莫说昭儿受不了,便是他也愧对沈卫忠啊!
云收雨过波添,楼高水冷瓜甜,绿树阴垂画檐。纱厨藤簟,玉人罗扇轻缣。
阳光透过柔薄的窗纱照进屋子里,空气中仿佛浮着金色的尘埃,柔柔地泛着光芒。大殿中的鎏金香炉中坟着极宜人的安息香,只见一团浅淡的白烟,轻轻淡淡,丝丝缕缕,袅袅升起。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我赢了。”
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身着湖蓝色缎绣茉莉夹衣,浅粉色镶银丝边的长裙的女子笑吟吟地去摸古牌,她容貌俏丽,皓白如雪的明腕上戴着一双银白的绞丝镯子,那镯子上还坠着小小的铃铛,叮叮地发出清脆的声音,正是富察芷珊。
坐在上位的是身着秋香色百蝶妆花缎袍的女子,她眉目温婉,头上戴着翡翠玉嵌金扁方外两端各插累丝金凤,那凤尾垂着长长的流苏沙沙地打着衣领,襟口上是一只猫眼的盘扣,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却是皇后。
只听皇后缓缓地勾了勾唇,笑道:“你这丫头骨牌倒是打的好,算了,本宫也乏了,这支玉簪子便当是本宫输给你的吧。”
芷珊接在手里满面的欢喜,笑道:“多谢娘娘。”
见皇后起身忙扶了她去坐在炕几上,接过宫女手中的团扇悠悠地替她扇起来,皇后瞧她如此模样不禁扑哧一笑:“你可是有话要说?”
芷珊闻言,羞怯地浅浅一笑,耳廓慢慢嫣红一片,半响方干干地问道:“娘娘,皇上前些天说要为芷珊赐婚……”
皇后见她面红耳赤的模样早已忍俊不禁,说道:“你放心,这事自有皇上为你做主,只不知顾讳庭的公子你可还满意?”
早几天皇帝便说要替富察芷珊赐婚,因不知会指给谁,芷珊心中一阵担忧,此时听皇后说竟是顾谚昭,免不得心中大喜,满脸窘色地说:“皇上恩典,芷珊自然满意,谢皇上与皇后娘娘厚爱。”
自从那晚之后,弘历便对素依冷淡了起来,那样子竟像是对一个普通宫女一般。秋若与云柔心中愕然,找小六子问询了一番却什么也未问出,倒是素依一脸的平静,每日里只是在御茶房帮着煮茶做些杂活,偶然去御前送茶,皇帝却总是头不抬,并不瞧她。她心中亦是千回百转,从开始的疑惑不解,到后来的坦然顺之。
这日,她前去养心殿送茶,远远便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跪在地上,心中一凛,端着盘子的手便微微颤抖起来,大殿中静悄悄的,弘历着了件黛蓝贡缎团福袍子在御前端坐着,眼神有意无意地瞧了她一眼,素依对上他的目光不由得一惊,加快了脚上的步伐却听一个淡淡地声音响起:“富察芷珊是皇后的表亲,容貌也颇为端秀,品行甚佳,莫不是配不上你?”那声音明明是淡漠的,可听在人耳中却仿佛夹着冰粒子似的冰冰冷冷的。
素依心中咯噔一跳,眼神不由自主地去瞧跪在地上那人,他要娶富察芷珊?
顾谚昭跪在地上,头也未抬可却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气,胸口仿佛压了一口大石沉甸甸的竟叫他喘不过气来,他见皇帝已有怒气,不由得便脱口而出:“臣不敢。”
素依却已是愁思顿生,心中凄凉一片,双手颤抖地将那青花瓷杯放在案子上,急急地便退了出去,刚出了屋子眼泪便落了下来,她在害怕,目光落到颤抖的双手上,腕子上是一只碧绿的翡翠,在阳光熠熠生辉却一点温度也无,冰冷地贴在手腕上,如一条毒蛇正在咝咝地吐着芯子,她忍不住便啜泣起来,他要娶亲了……
她早知会有这么一天,她负了他,他此生会有其他女子陪他共度,只想不到会如此之快?琴瑟和鸣,莫不静好,终究不是她跟他,这漫长的一生,他会有如花美眷,她却只能待在这囚笼般的深宫孤独终老,曾许三生三世,却原来,一生一世也叫人辜负……
弘历望着素依瘦削的背影微微怔忡,她那样急匆匆地出去是怕会落下眼泪还是怕听到不想听到的消息,她的心里终究忘不了他吗?
顾谚昭见皇帝一言不发,心中愈是忐忑不安,沉声说:“微臣身份低微,恐委屈了富察小姐,况且大丈夫尚未立业又何以成家?微臣愿去西南平定苗疆叛乱,安抚百姓,替皇上分忧,望皇上成全!”
皇帝垂眸望着他,半响终是叹了口气:“也罢,你既愿去平乱,那这婚事就日后再议。”
顾谚昭这才松了口气,额际鼻翼却是颗颗晶莹地汗珠,手心里也全是冷汗。
过了两日,素依正在睡午觉,迷迷糊糊之际只听耳边响起唉声叹气的声音,那声音不断如带声声入耳,她动了动身子那声音却戛然而止,她便翻了个身,那声音却又娓娓而来,却是秋若与云柔在说话,她睁开了眼睛,仔细地听着。
只听秋若的声音先响起,“你小点声音,别惊着素依了。”
云柔压低了声音说,“嗯,可是顾公子真的要去苗疆平乱吗?”
素依悚然一惊,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一颗心怦怦地跳着,屏息凝神间只听云柔又说:“我听乾清宫的小顺子说西南苗疆叛乱可是好一段时日了,据说皇上派了好几位大人前去,可都没有法子。”
秋若说:“我也不希望顾公子去,可是这圣旨都下来了,说是不日便要启程了。苗夷蛮子犹善使毒,我真是担心顾公子。”说完便隔着窗子瞧了瞧榻上安睡的素依的身影,心中微微叹了口气,这事若叫素依知道了指不定有多难过呢。
素依紧紧地攥着眼前被子上锦缎,眼泪簌簌而下,他要去苗疆平乱,他竟然要去苗疆……苍天,自古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这一去,他们便真的隔了山长海阔,烽火连天,又要何时才能相见?又更甚,今生今世再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