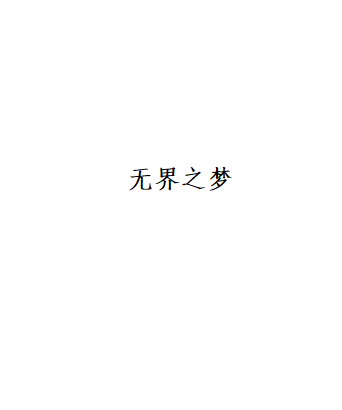怀袖问:"那他知道你喜欢他么?"
官召羽摇头:"我不知道,我想,以他的聪颖心思,应当是明白的……"
怀袖又问:"你可与他有过暗示?"
官召羽闻此问,微红了脸,低语道:"前日,我随额娘去他家府上拜望,恰巧遇见他在家,我便请教了他一首诗。"
怀袖只点头,却未问出口,她深知道官召羽的女儿心思不比月牙的爽直,她是细腻温婉的,若自己贸然问出来,官召羽不好意思说反而不好。
官召羽见怀袖并没问诗词,也猜见她的心思,感动她如此细腻体贴,便也不再扭捏,说道:"就是那首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待官召羽将这一首《长相思》深情切切地诵完,怀袖已了然她对那人却是真动了情。
那一句情思悠悠的口吻将诗句中的绵绵相思意味全泄了出来,那想山想水,含思含恨,都是人于月下楼头,重重复重重的浓密心思,茫茫然眉目间的情愫,远望驰思,念亦难休,怀揣着这颗心,连人都要化成望夫石了。
怀袖心中不禁怜惜起她来,问道:"你对此人的情愫,定不是一日两日了吧?"
官召羽微笑道:"前年,我随着阿玛和哥哥陪圣上游览圆明园,我亲眼所见他的文韬武略,因而……"官召羽说至此,又垂首红了脸。
怀袖含笑温声开解:"这并没什么,情之所以起,一往而深,乃人之常情。"
官召羽点头微笑道:"我知道你有见识,所思所想也定是与旁人不同,不会取笑于我,果然不错!只是,他……始终对我很是冷淡。"
怀袖听官召羽如此说,略想了想,温和道:"或许,他有他的不得已呢?"
官召羽听她如此说,已觉察出怀袖话里有话,双眸闪动望着怀袖。
怀袖道:"咱们虑事,多半易从自己这一面想,却甚少从对方的一面想。情思受困,咱们总问:为什么他如此待我?但,这一问其实是谬误,原应问的问题是:他为何这样对待他自己?"
官召羽从未听见过这些思想,不禁听得痴迷住,目不转睛盯着怀袖,生怕落听了一个字去。
怀袖继续道:"其实,他所做,所说,不做或者不说,总是有他的道理,总要他的缘由,即便我们看似他不近人情,或者绝对自私,但在他的思想里,那却是他的过活方式,原本是与任何人都无关的。"
官召羽若有所思点了点头,继续听怀袖讲下去。
"咱们遇见挚爱亲朋行为乖张,不禁会为之叹息他为何如此作践自己?为何这样行事待人?但却又不明了,这些原本是他一己之事,原也只需要他向自己一人交代过便罢了,咱们原是管不着的,不过跟着白担心。"
官召羽却有些听得迷糊,忍不住开口问:"那他又为何如此待我?"
怀袖直截了当回道:"每个人做决定时,都需负责任,然而咱们更多的时候,面对事物是力不从心,身不由己。所想与所为是两码子事,你需明白,'事与愿违'其实是人生之常态。"
官召羽兴奋道:"怀姐姐的意思是,他或许有其他的缘故,却并不一定是刻意针对我的?"
怀袖轻轻点头,含笑温和道:"他或许并不一定出于他的本意,只是他能力有限,不能尽善尽美,满足你的同时,也令他自己更好过。就比如你喜欢上了他,就对旁的男子不再存心,那么再遇见心仪你的男子,也便也无法回应他的情感了,不是吗?"
官召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忽然蹙眉道:"难道他也是有心仪的女子了吗?"
怀袖微笑牵住官召羽的手道:"我不过是打个比方,不是事事如此。"
官召羽闻听,转而又转忧为喜,跟着问:"那,姐姐说我该继续喜欢他吗?"
听见官召羽如此问,怀袖突然想起自己与容若,不禁微笑低语道:"将不完美的人事释然放下,向美好的愿景张看……"
"怀姐姐,我明白了。"官召羽深凝怀袖一眼,唇边噙着笑靥站起身。
走至门边,回过头,目光水莹莹地望着怀袖道:"怀姐姐,谢谢你!"说罢扭身雀跃而去。
怀袖望着官召羽消失在门边的身影,不禁低语道:"两心相悦之情,永远是女人心头的那一粒朱砂。微痛,却又无比珍视。"
语落,正欲回身,耳畔忽然传入一阵低徊的男子声音:"你便是我心头的那颗朱砂,渐渐绽成一朵血色的莲花。"
"谁?"怀袖赶忙回身四顾,屋内空无一人。
跨步行至门边向院落中看,只见细细的微风轻轻摇曳着紫香槐的枝叶,偶有几片枯叶纷纷然若蝴蝶飘落下来,哪里有人影?
怀袖不禁暗道:难道是我的幻听么?正思此事,忽又觉头一阵眩晕,赶忙用手撑住门边。
之前便要去歇息,只因官召羽来,便强撑着陪了这半日,此事已觉神思困倦。
举目四下望,却不见翦月等人由此过,只远远地瞧着茶房门前站着个人,便伸手召唤,待那人跑进,怀袖见却是成日遭人数落的扣儿。
"姑娘唤我何事?"扣儿跑到近前,向怀袖行礼。
怀袖微笑道:"此时你翦月姐姐不在这儿,你扶我回内室歇息吧。"
"好,姑娘当心着些。"扣儿边说着,便伸手挽扶住怀袖的胳膊,缓步向内室走去。
直至进了屋内,怀袖躺在床上,扣儿小心翼翼将锦被拉了盖在怀袖身上,小心翼翼问:"姑娘喝茶吗?"
怀袖微笑摆了摆手道:"你去吧。"
扣儿答应着向门口走去,走至门边回身望了一眼怀袖渐渐合上的眼眸,略站了一时才转身出去。
扣儿刚出去,便有一个人影以极快的速度旋身进入怀袖的内室,转过屏风,目光望向床上已睡去的怀袖,微微皱起眉心。
——
转过十月,天寒气已十分逼人,晨起时候,地上已经下了毛茸茸的白霜。
那只捡回来的鹩哥已经长出了长羽,平时不用拴脚链子也不乱飞,大多数时候,安静地卧在怀袖为它专设的,固定在书房轩窗下的小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