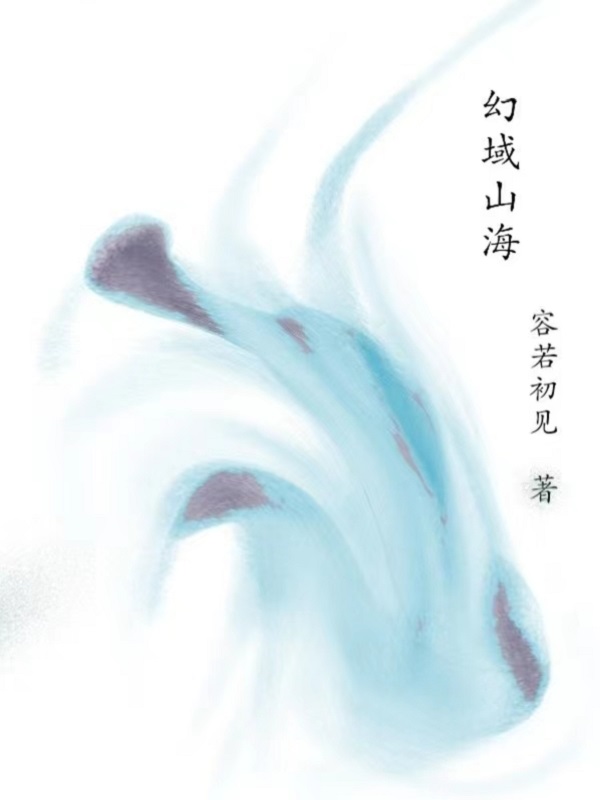“各位旅客,本次航班从美国纽约飞往英国伦敦。飞机即将起飞,请各位乘客系上安全带……”
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在机舱内荡悠着,绝大多数乘客都开始手忙脚乱的系上安全带,只有第二排右面靠窗的一名男子仍然在埋头看着手中的资料,对空中小姐的话置若罔闻。
“先生,”一名空中小姐见此情形,走上前去,俯身轻拍这名男子的肩膀,“请您把安全带系上。”
在空中小姐连续三次提醒之后,男子才将目光从手中的资料移开,抬起头迷茫地看着眼前的制服美女。
“先生,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请您系上安全带。”
眼前的男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约莫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前额平坦,双眼眯缝着,鼻子不是很高,总体来说是其貌不扬的那种,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头墨黑的平头短发,显示出这名男子的亚裔身份。
在空中小姐第三次重复了要求之后,男子这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抱歉地朝空中小姐笑了笑,系上了安全带。
不经意间,空姐瞥到了男子腿上放着的资料,最上面一张纸上印着一个三足、两耳,顶部敞有大口的奇型金属物图案,金属物上隐约还刻着花纹。图案旁边有很多方块文字,以前公司组织培训的时候稍微了解过一些,空姐知道这种文字叫汉字,她也从记忆中提取出关于那个金属物的片断,隐约记得那个金属物是一种叫做“鼎”的器皿,只有古代中国才有,能够流传到现在的已经是文物了。
长年累月在空中飞来飞去,空姐见识到的人是各式各样的,能和文物扯上关系的当然不是一般人,这名其貌不扬的男子的真实身份自然不可能同他的相貌一样平凡,空姐明白这一点,也明白自己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好奇,便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开。
男子显然还是在思考问题,一点都没注意到空姐的离去,系好安全带后,目光仍然停留在资料上,若有所思。
这名男子名叫杜宇,是中国最年轻的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尤其是在隋唐之前的研究领域,他已经隐隐有赶超前辈的趋势。两个月前,杜宇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前往纽约担任两年的中国历史客座教授。但就在前一天,远在英国同为考古专家的好友杰琳娜给自己发来一个传真,就是杜宇现在手中拿着的资料。
“霸王鼎!”
这是杜宇打电话给杰琳娜的时候,杰琳娜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在本周末,伦敦将举行一场拍卖会,压轴的就是这个中国古鼎,据说这就是当年楚霸王项羽“霸王举鼎”时的那个巨鼎,博纳姆拍卖行作为这次拍卖会的主持,非常谨慎,将全英国最出名的考古专家杰琳娜请来鉴别古鼎的真伪,但杰琳娜对中国的文物也吃不准,情急之下想起了好友杜宇,便一纸传真邀请杜宇过来帮忙。
杜宇从学生时代起就跟随老师进行考古研究,对文物有着近乎痴狂的爱好,一见传真,自然是见猎心喜,再加上杰琳娜盛情相邀,他立刻推掉手边的课,第二天就坐上了飞往伦敦的客机。
杰琳娜发过来的资料并不多,仅仅是古鼎的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和一些文字描述,单凭这几张照片,杜宇也不能确定。古人但凡铸鼎,大多在鼎身刻有铭文,但杰琳娜的照片上没有一丝铭文的痕迹,只有在一只鼎足上有个深深的手印,如果这就是当时项羽留下的,那项羽的力量为免也太可怕了,而且在传闻中,项羽举的不是鼎足,而是双手握鼎耳,两者并不符合,这估计只是卖主卖弄的噱头而已,杜宇在心中已经否定了这个鼎就是项羽举的鼎,只是杰琳娜在电话中说这个鼎已经经过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出来的确是秦汉时候的,杜宇相信这种测定是不会出错的,这也是真正引起杜宇好奇的地方,究竟是谁将这重逾千斤的古鼎从中国运到外国的,又是如何运的,这鼎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夜没睡,又想了许多,杜宇不禁有些犯困,飞机起飞后也逐渐平稳,杜宇收起资料,眯上眼睛准备在到达伦敦之前好好睡一觉。
……
睡梦中,杜宇被一阵剧烈的颠簸震醒,抬眼向窗外望去,却是一片漆黑,已经是夜间了,什么都看不见,而飞机的颠簸感却越来越剧烈了。
“各位旅客,不好意思,我们的飞行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航程,只是现在出了一点小问题。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机长是具有五千个小时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员,无论什么困境都可以安全度过的……”刚才提醒杜宇系安全带的空姐现在站在客舱前端,对旅客们大声说着安慰的话。
“刚上岗的吧……”杜宇小声嘀咕了一句,他已经看出来虽然空姐的表情很镇定,但声音的颤抖却并没有很好地掩饰住。杜宇明白这次飞行肯定是遇到大问题了。
“一半的航程……”杜宇默默想着,联想到最近报纸上连续出现了好几次的“百慕大神秘失踪事件”,心里苦笑:“难道真的这么巧?”
果然不出杜宇所料,那名空姐随后道:“为了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请大家系上安全带,将所有杂物都放入座椅后面的口袋,然后将毛巾和枕头垫在腹部,双手夹住头部,弯下腰……”末了还来一句宽慰的话,“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将各位安全送到目的地。”
“不是这么巧吧?该死的!混蛋!……”杜宇心中不断咒骂着这倒霉的航班,“号称事故率最低的飞机难道会偏偏让我遇上出事?让我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再出事也可以啊,老子还没见到那个鼎呢。”
“该死的!怎么回事!这个破铁皮怎么不听话了,吉米,你给我看着,我试试切换手动模式……”
一阵惊呼声透过机舱内的喇叭传遍了整架飞机,除了弱智和儿童之外,所有的人都能听明白这是从驾驶舱中传出来的,而在惊呼声中传达出来的惊恐也瞬间感染了所有乘客,几乎所有人的脸色在瞬间变得煞白,只有杜宇是一副愤愤中带着遗憾的表情。
恐惧在机舱内蔓延着,有许多人已经站起身来质问空姐了。就在空姐忙着解释的时候,又一阵惊呼从喇叭中传出:“吉米来帮帮我,这该死的手动居然没用,不好,速度怎么这么快!天哪!要撞上了……”
还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砰”的一声巨响,客机一头栽倒在一个海岛上,触地时那强烈的撞击给了每个人难以名状的冲击力。杜宇的耳朵嗡嗡作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轰隆”又一声巨响,爆炸了,纯净的航空机油带来的爆炸威力绝对是一级棒的,客机那庞大的身躯在瞬间就被撕成了无数块残躯,甚至还带着火焰,散落在沙滩上。
……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杜宇被身上的伤口痛醒了,用力地睁开那沉重的眼皮,第一眼看到的却是那刺眼的阳光,杜宇连忙又闭上了眼睛,也顾不得身体各处的痛楚,挣扎着翻过身来,趴在沙滩上。
歇了一会儿,杜宇勉力睁开双眼,坐起身来,然而全身烧伤般的疼痛立刻又刺激到了神经末梢,让杜宇不禁**出声。
“这是?”
杜宇抬目四望,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碧波汪洋,目光所及处,根本没有丝毫的岛屿和船只痕迹,而身后,则是那架已经断成几截,烧得乌黑的飞机残骸。除了海浪拍击沙滩的“沙沙”声,没有其他的任何声音,甚至连海鸟也见不到半只,在这青天白日下,这片沙滩寂静地有点吓人。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杜宇自言自语,当然没人会告诉他答案。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自己流落到一个荒岛上了。再看看自己,遍体鳞伤,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目前来看,自己的伤全部是皮外伤而已。
毕竟见多识广,杜宇休息了一会,站起身来,蹒跚着朝飞机残骸走去。既然自己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其他人应该也有生存下来的可能,而且还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在飞机内找点食物也是必须的,再说飞机内应该还有通讯和求救设备才是。
让杜宇失望的是,整班航班,存活下来的乘客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机务人员全体殉职。也就是说,在发现这个岛上的土著之前,这个岛上只有他一个智慧生命的存在。一个人面对这么多已经被烧焦的尸体,再胆大的也会腿肚子发软,不过杜宇是搞考古的,经常和千年、百年的古尸打交道,这些“新鲜”尸体还无法引起他的恐惧,只是让他头疼的是,作为唯一的生者,这百来具尸体入土为安的工作就得由他来做了,光是挖个大坑就够杜宇忙好几天的。
先不去理会埋人的事情,自己能活下来才是最要紧的事。杜宇居然在已经炸得半烂的储物舱内找到了不少的食物和淡水,而且还有一些药品和医用器具,甚至他还在其他旅客的行李内发现了一套野外探险装备,唯一让他失望的就是客机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已经损坏,完全无法使用。
用找到的纱布包裹了自己身上的伤口,杜宇开始发愁,照这个样子,肯定是无法和文明社会联络了,而且找到的唯一一支能用的信号枪里面还只有一发信号弹,还不知道有没有船只会经过这个荒岛。
想了半天,杜宇没理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思索,抬腕看表看时间,就是这一看让他傻了。
手表倒是没坏,还是在尽职尽守地走着,但奇怪的是,手表的时针、分针、秒针居然重合在了一起,而且以同样的速度不紧不慢地一步一走,完全分辨不出三根针移动一次是多少时间。
“这……这也太……”
杜宇没说下去,除非是表坏了,不然不可能这样,脑中刚闪过这个念头,杜宇立刻扑向那些尸体的地方,也顾不得对死者的大不敬了,直接扒了几块表下来,一看之下,更让杜宇目瞪口呆,所有的表都是一个毛病:三根指针重合在一起,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着。
“我的天哪!”
杜宇颓然,一屁股坐在沙滩上,他已经明白了,这些表自然不可能集体坏了,而是受了外界的影响。联想到以前学到的知识,杜宇猜想脚下的荒岛肯定有一种奇异的磁场,影响到了手表。再从那套野外探险装备中取出指南针一看,更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指南针滴溜溜地乱转个不停。
“这明明应该是电影中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杜宇喃喃地说着,仍然不敢相信地看着手中那滴滴乱转的指南针。
过了许久,杜宇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揪心的疼痛感再次证明了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下子麻烦了,这么紊乱的磁场,即便飞机和船只搜救也会麻烦重重。
“怎么办,怎么办……”杜宇在沙滩上来回走着,思考不出个头绪来。踱了很久,杜宇才决定总得先给自己弄个住的地方,也不找好地方了,直接在沙滩上将帐篷支起来了,将一部分淡水、食物和药品放入帐篷后,杜宇开始处理所有遇难者的身后事。
首先是将尸体从飞机残骸中搬出,然后集合到一起,接着杜宇开始挖坑。
※※※
“好了……”杜宇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坑足足挖了三天的时间,刚想直起腰放松一下,忽然一个阴影在沙滩上掠过。
杜宇一惊,连忙抬头一看,这一看让他喜出望外,居然是负责搜救工作的直升机。杜宇连忙向直升机连连招手舞动,大声呼救。但奇怪的是,直升机仿佛没有看见杜宇、甚至好像没看到这片沙滩一般,径直飞走了。留下杜宇僵直了双手站在沙滩上**。
什么意思?那群搜救队员喝醉了酒才开始工作的?别说这么大一个人没看见,这么一大片沙滩对于飞行员来说似乎也是形同虚设。眼看飞机越飞越远,杜宇才猛地想起那支信号枪,心急火燎地奔到帐篷中取出信号枪,那飞机却早就飞得没影儿了。
“该死的!”
杜宇愤愤地将信号枪往沙滩上一摔,嘴中不由得骂起娘来。
不过老天似乎还没有掐灭杜宇的希望之火,飞机消失后不到半个小时,另外一艘负责搜救工作的小型搜救船出现在沙滩前大约五百米内的海域中。杜宇这回不再迟疑了,几乎是饿虎扑食般将信号枪抓到手中,高高举起,用力地一扣扳机。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冲出枪膛,飞向半空。即便是在阳光明媚的白天,那种那种刺目的艳红仍然在天空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轨迹,就像一条单色的彩虹,竖在半空中。
那颗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在空中燃烧了足足有半分钟才逐渐下落熄灭,杜宇相信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个求救信号,也就放松下来,一屁股坐在沙滩上,心中庆幸虽然受累挖了这么大一个坑,但是总算也不必再受累将这百来具尸体掩埋了。
但讥讽的是,老天在给予杜宇生存希望之后,竟然再次将这个希望给扼杀了。那艘搜救船,也是和直升飞机一样的反应,对这个醒目的信号弹视若无睹,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地离开了这片海域,而彻底发呆了的杜宇从头到尾都在向搜救船行注目礼,直到搜救船消失在自己视线之外,杜宇也没反应过来。
由于这边海域相当广阔,对已经搜寻过一遍的海域,搜救队一般是一会再次进行搜寻的。杜宇多少也明白一些,而见到搜救飞机和搜救船对自己视若无睹,杜宇已经灰心了,明白自己几乎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了,尤其是仅有的那发信号弹消耗掉之后却没有带来应有的效果,更让杜宇泄气。
直到月上中天,杜宇才从精神恍惚的状态恢复过来,失望至极的他什么事也没做,直接钻进了帐篷睡觉,因为他明白,掩埋这百来具尸体虽然没有挖坑那么大的工程量,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没有足够的精力,也够累的。想想也真是好笑,杜宇在出事之前是有名的考古专家,专门掘古人坟墓的,现在却要挖坟埋人,这两种极具反差的做法也亏得他能做出来。
月上中天睡,日上三竿起。杜宇这一觉足足睡到日照当头才醒,既然一切都想明白了,那么睡觉也就睡得比较踏实了。由于那个大坑挖的离沙滩有一些距离,因此拖动尸体也够麻烦的,埋人的工作杜宇花了一天半才完成,长期脱离体力劳动的杜宇被这几天极其庞大的工作量累得不成人形,不过总算把尸体掩埋完毕,没有死人的困扰,杜宇的心里总算踏实了点,不然这怪异的小岛再加上乱葬岗一般的气氛,杜宇再怎么胆大,长期下来,即使不精神失常也会心慌不已。
看着堆得高高的坟包,即使是阳光明媚,杜宇仍然感觉是一阵恶寒,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虽然让杜宇不再相信鬼神之说,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敬鬼畏神仍然深深影响了杜宇。本着尊重死者的传统习俗,杜宇在坟包前撮起了三堆土,代替檀香,然后跪在坟堆前,杜宇重重的磕了三个头。
“各位兄弟姐妹,老少爷们,我杜宇与你们同乘一架飞机,各位不幸罹难,唯我杜宇独存于世,此是我杜宇之幸,相信也是借各位洪福。小弟本当随各位而去,怎奈俗世之间尚有尘缘未了,各位先行一步,五十年后,杜宇必至奈何桥畔向各位请罪。”
说罢,杜宇又磕了三个头,想想还是不妥,凌空虚拜道:“兄弟姐妹此去经年,小弟不能相送,为表歉意,若能脱困,各位此去酆都,在那黄泉路上一路盘费自由小弟支付,切勿担心。日后每逢寒食清明、中元盂兰,各位在地府的花费皆由小弟全力承担,还请各位安心离去,千万不要与那黑白无常横生争执,一切自有小弟安排。”
又是凌空虚拜三下,杜宇又磕了三个头,心中才安稳了些,虽然这些行为与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格格不入,但能让自己心安那就好了。
处理完一切,杜宇不敢在待在这个坟包附近,第二天又花了足足有一整天的时间将自己的“家”搬到了海滩的另一侧,离这个坟包远远的。
从这天开始,杜宇的荒岛求生才只是真正拉开了帏幕。本来以为埋了这一堆尸体,事情就算告一段落的杜宇,现在却突然发现这个岛上没有一丝动物生存的痕迹,除了那些奇形怪状的植物,有的是高可参天的巨木,有的是矮小如青苔般贴在地上的微型小树,还有长得脸盆大的叶子却拥有全身毛刺的草本植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让杜宇不由得感叹这世界的神奇,这些植物都是杜宇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惜杜宇不是植物学家,不然的话,看到这么多从未在人类资料中出现过的植物物种,非得让他兴奋的发疯不可。
这些奇怪的植物既让杜宇好奇,但也让杜宇害怕,因为他明白,很多东西都是碰不得的,就像花蘑菇有毒一样,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些植物,岛上又没有动物,也就是说,除非杜宇能壮着胆子吃下这些植物,不然的话,等到飞机上残留的食品一吃完,杜宇就只能独自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而且是最痛苦的死法——饿死。
这很无奈,但没到最后一刻,杜宇还是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只好暗中约束自己省着点吃剩下的食物,以图能够凭借这些食物支撑到救援人员的到来——现在的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的那种沮丧,也全然忘了岛上的种种奇怪现象,只是凭着一种发自心底的乐观坚持认为自己一定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