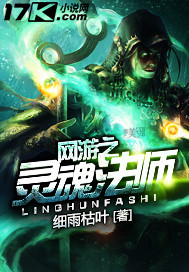段霖晖的话一下子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他这一问,竟然连袁允南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李峪树倒是想再反驳两句,可是也想不出什么妙招,再加上段霖晖从来软硬不吃,言辞锋利。许多官员弹劾过他,都被他一篇一篇驳斥回来,朝廷之中基本都有一个印象,当大理寺卿要和你吵架的时候,必须先回家读两天的书,再回来慢慢吵。
杨正清一向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明,在水利和河道整治这方面他早就看的不爽了,知道这里面装神弄鬼的东西很多,可是以前的时候有萧城毅在那边层层的压着,他想折腾出什么都不可能,如今先是豫昭王大力整治水利,年末户部又扣下了工部的账单,他就知道时机到了,所以,一向中立的他这个时候也站在了大理寺卿一边:“要说这全国河道水利的整治,有些支出确实不合理,这其中一定存在徇私贪墨、消极怠工的情况,工部超支严重,户部不批也是有道理的。”
李峪树十分不满:“当初,工部签发的单子都给户部看过,户部也是知道的,好好的到了年末给我们工部来一棒子,还美曰其名说是我们工部这边寻思贪墨、消极怠工,这不是摆明了给我们难堪么?杨大人,你这么说可有什么证据么?”
现在的杨正清经过生死轮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性情冲撞的刚烈冲动之人了,如今的他已经贵为吏部尚书,身为六部之首,早已能够镇定地对待他人的质问,所以他平静道:“工部的账单我们都看到了,可是看到了并不代表这账单就合理。工部的支出若是合理的话,上个月也不会有十几道河道衙门上缴户部下拨的钱款,再说这工程进展,平北将军已经去巡视河道了,其中境况如何明年自有分解。李大人现在在这细枝末节上追着本官不放实在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
这边李峪树被杨正清攻击,那边袁允南又碍着段霖晖没法帮忙,李峪树左思右想,干脆一屁股跪倒在地,哭诉了起来:“太后娘娘,臣也苦啊,当初朝廷下令大修河道,导致一时间工部的账单接连不断,臣已经拦下了很多无用的工程和开支,可是无奈下层官员都拿着国策为幌子,上面萧城毅又给工部施压要年年都要拿出成效来,臣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臣也难做啊。”
“今年河道的支出是五百万两,臣已经尽力削减了,不然太后娘娘可以查一查往年的例子,都要高达七百万两呐。工部的各个官员可都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做的,可是现在可倒好,就因为超出了预期,户部就压着工部所有的账单不妨。太后娘娘,我们朝廷的这些官员今年拿不到俸禄没什么关系,可是这让下面那些河道工怎么办?他们可是等着吃饭过年啊。”
李峪树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到动情处只恨不得哭嚎两声,他料定齐黛莹身为国母,自然心系天下百姓,与其一个劲的和吏部尚书还有大理寺卿较劲,还不如说服太后娘娘。果然李峪树的话让齐黛莹有所触动了,这时通政司使仇光也道:“太后娘娘,这河道之中有些油水我们都是知道的,可是这些都是那些贪官佞臣所为,再者就如杨大人所说,平北将军韩西月已经前去巡查河道,目的就是要查清情况。再苦不能苦百姓,依臣看,工部的单子可以签,剩下的可以等韩将军追回。”
仇光和李峪树两个人一个晓之以情,一个动之以理,几乎都要将齐黛莹说动了,可齐黛莹知道在民政方面,她根本不熟,所以还是虚心地询问了一下左右丞相的意见,许恒与沈鸿彬商量了一下,还是认为河道的单子可以签一部分,超出预算过多的还要在详省才行。
齐黛莹点头道:“好,就按照左右相说的办,那么工部还有哪些单子没有签?”
段霖晖心中一沉,水利河道尚能说去,一旦后面有了牵扯,户部可是要不利了,刑部尚书毕燃正好站在了李峪树的身边,他低头看了一下,禀报道:“剩下未批的就是洛阳龙阙山的皇陵还有宫中主殿的修筑。工部年初上报的预算是二百万两,年终结算却是四百七十万两,超出了二百七十万两。”
“皇陵和主殿的修筑也没有批啊,也是因为超支过多啊。”隐约的,段霖晖感觉到太后的声音似乎冷上了两分。
“太后娘娘!这事,我们工部也冤枉的很啊!”不知为何,听到毕燃提及了这皇陵和宫殿的事情,李峪树就像体内一下子注满了力量一样,声音大了许多,底气也足了很多:“洛阳龙阙山皇陵本就在修缮之中,去年先帝与淑懿太后突然先后而亡,皇陵亟需休整,再加上江南和黄河出了栽,运输道路被堵,不得不增加支出。再加上今年是元光初年,新皇登基,按着祖制,新皇主殿应该重新休整一番,这些事情,工部都是给太后娘娘呈报过得。现在可好,户部压住了这两个单子,来年皇陵那边动不了工,宫中主殿又修了一半!”李峪树回头,高声逼问霍荣:“霍尚书,我且问你,若是这些不知处,淑懿太后和先帝怎么移棺龙阙山皇陵,你现在压着账单,意思是要让淑懿太后和先帝无处所归么?还是说要让新皇无处所居么?!”
一直默然无语的礼部尚书曾宇雷,曾经在朝堂上当众向豫昭王发难的人忽然站了出来,恶狠狠地对霍荣道:“霍尚书,我算是发现了,你今天是无论如何都要和工部过不去了,其余的超支你不管,唯独工部的单子你不停的挑麻烦,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你的最终目的就是皇家头上的这笔账啊。”他朝着霍荣,话语里就像藏着钢刀:“霍尚书,想来你是怕压下了皇陵和宫殿的账单,皇上会发怒,所以干脆将工部的单子一并都压下来,到时候就没人能分清你心中所想了,是不是!”
众人一惊,说也没料到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一番惊人的言论,霍荣也是感觉身后猛地刮来一阵凉风,要是往狠里说去,这可是不敬的大罪,要灭族的!若非刚刚段霖晖悄悄地对自己说了几句话,只怕这个时候,他早已不知该如何应对,好歹有了一些准备,霍荣冷哼一声,当即也摔了手掌的账单,愤慨道:“我只说工部今年的亏空很大,其余我可是一个字都没有说,曾大人想要治我的罪,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霍荣!不要无理!”沈鸿彬当即呵斥二人:“曾尚书,工部的账单有大的出入,户部自然可以提出疑问。我们都是朝廷官员,都是为着皇上为着天下尽责,本着自己的职责做事,何罪之有?再则霍荣,工部对你的做法有疑问,你一一回答就是了,没人想要给你加罪,太后娘娘也说要给你治罪,你休要再无理!”
段霖晖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抬眉看了一眼坐在左方的左相沈鸿彬,心中对沈鸿彬的敬佩油然而生,看来不止是自己,连左相都发现了这其中隐藏的杀机了。其实今天虽说是左右丞相朝开的会议,可是身为皇族的北淮王与豫昭王都不曾出席,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金帘之后的太后齐黛莹。要说太后,实在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她明明有着垂帘听政的权力,可是却偏偏放下,身居后宫,将前朝之事全部托付给前朝重臣,在各种大事需要她拍板的情况下也绝不含糊,明辨是非当机立断,确实算得上是一位贤后。
可是正因为太后是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子,手中又无重权,很容易就会让人忽略一件事情,那就是——她也是一个年轻丧父,唯有一个孩子的孤独女子,她的心思也是十分细腻敏感的。
先帝壮年而去,唯独留下她和一个孤子,在先帝才去没多久,又经历了一场大难,若非豫昭王横空出书出手相助,只怕这皇位现在都不一定轮得到她的儿子。所以,不要看太后现在这样明白是非,只要一触及她的底线,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段霖晖很清楚,太后的底线就是她和她儿子的权威。
户部扣下的工部修筑皇陵修缮宫殿的款项,已经让齐黛莹心中略有不满,再加上李峪树和曾宇雷两个人一阵挑拨,可想而知齐黛莹心中该是个什么光景,她必定想着:好你个户部尚书,欺负先帝去的早,我们孤儿寡母孤苦无依,竟然连太后和先帝的陵寝还有新皇的宫殿都不好好修,简直太过分!
一旦齐黛莹心中有了这个想法,霍荣可算是完了,还好,左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适时地帮霍荣解了围,明着批评霍荣,暗中确实在帮助他大不敬这个罪名,而且比起自己,左相的话要有力的多。